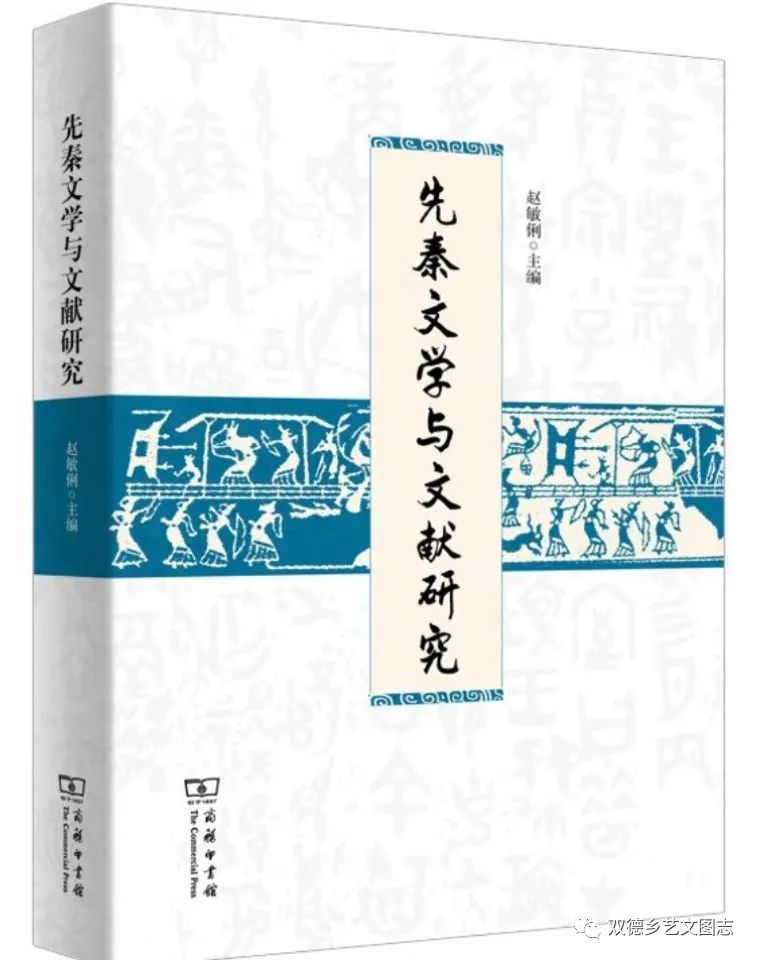
赵敏俐 主编 《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
商务印书馆,2020
最近生活节奏很乱,赵敏俐主编的《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终于读完。是一本基于2015年首师大发起的“先秦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2017年编成,直到2020年才出版。小蔡推荐给我的时候说,里面讨论的一些问题也是这几年我常谈的。电子版找不到,托朋友从东北师大借的,参考本,一周就得还。一夜之间,封控来了,也省得还了。
李山的课在B站听过,文章还是头一次读。集子里所收他的《三篇的写作时代》,很有分量。尽管逻辑上不无漏洞,但他对研究对象深入的程度,非常令人敬佩。写的是翻案文章,要证明《尧典》《高陶谟》《禹贡》三篇不像疑古派认为的那么晚,不当在春秋、战国时代,而是写定于西周中后期。
他先提出西周作品并不都似周初“八诰”般的屈诘古奥,西周近三百年,语言必经变化,尤其发生在中期的社会变革,此前已有白川静、杰西嘉·罗森、唐兰等人从各方面观察,得出相近的结论。因此不能以语言的不够古奥就判定其为东周以降所作。继而从历史语言学、修辞学、思想史等不同角度,通过与铜器铭文和《诗经》具体篇章的比对,详密论证了夏书三篇写于西周的可能,理据充分且微妙细腻。相比之下,疑古派判定夏书晚出,证据却少得可怜,以至被李山笑为“瞎子断匾”。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愿意相信这些证据严重不足的论断?
这也许就是学术思想及其方法的意识形态化。一种新的思想或方法一旦为人们普遍接受,那接下来它在任何方面的发挥,哪怕是十分随意的发挥,都易于被人们遵从。疑古及其方法就是如此,它在20世纪得以确立之后,很快就不限于一股学术思潮,而成为一种潜在的伦理或道德意识。在下意识里,疑古才是科学、进步和光荣的;而信古则是蒙昧、落后和可耻的。所以在操作程序上,疑古如顺流而下,信古如逆水行舟。后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也未必敌得过前者。意识形态是一种时代征候,既是突破性的力量,也是某种牢笼。
过常宝《论先秦“辞”的演变及特征》,作了很好的梳理和分析。由《周礼·大祝》,可知辞大体包含了宗教和世俗两个维度。前者即“六祝之辞”,用于鬼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后者为“六辞”,用于上下亲疏,“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辞的宗教维度也许要早于它世俗的维度,“至少在西周中后期,这个字就主要被用以指神圣职事中的言语行为了。”“‘辞’是太祝沟通鬼神的专业性、神秘性、规范性的语言。”“最早指的是宗教仪式中的语言,尤其是宗教仪式中程式化、规范化的语言。”程式和规范,使得言辞与日常交际用语逐步区别开来,从而显示其操控力和权威感。
辞的宗教和世俗这两个维度,既有区别,又一体连贯。祝用于鬼神,是向上的辞。向下的辞用于人事,是所谓诰命,过氏称之为“教诫”。向下的教诫,通常也要在鬼神祖宗面前进行,所以也通于鬼神。辞的使用则都离不开仪式,即礼仪的程序,所以可说辞是语言的礼仪化的结果。过氏指出春秋时“‘有辞’只是礼仪周详的代称,符合礼仪程序或礼仪精神的语言即为‘辞顺’。”辞的权威既得之于神灵,又让渡于政治。随着西周神权的衰落和政权的抬头,辞也从宗教走向世俗。卜辞为青铜铭文所取代,大体可显示这一趋势,《尚书》则更是布政之辞的结集了。
辞的进一步下行,至春秋时代,则进入君子“立言”的层面。立言带有更强的世俗感,与辞的宗教性抑或政治权威性,进一步拉开距离。也就是说,有价值的言辞不必来自宗教与政治权威,也可以是道德个体开出来的经典话语。如过氏所说,三不朽之立言,“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大夫阶层继祝史之后,成为这个时代新的文化创新的主导者。”“‘辞’则从宗教语境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手段。”“君子之辞的世俗化发展,使得辞的宗教性渐渐失去,辞也就不复存在了。”而成为世俗性的文。
因为辞的历史根源在宗教,所以在观念上,辞必以虔敬信孚为内质,这也是对礼和仪的要求。所以,辞虽然表现为语言形式的特殊性,但其要义,却首先在宗教性的内质上。因为这古老的宗教失落得太久了,不能为我们所感知,所以,我们首先把握到的只是辞的形式而已,包括整饬、用韵、程式化,后来都为文所承受。但任何形式,其本身就有意义并产生力量,没有形式,辞和文都不复存在。形式并不是次于内容的存在。辞蜕变为文的过程,大致就是宗教而政治而审美的过程,形式始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保有其力量。

西周时期 印纹硬陶罐 浙江博物馆藏
曹建国《“赋诗断章”新论》,就这个老生常谈的命题,提出几点不同的认识,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强调 “赋诗”为春秋时的新现象。所谓新,在于作为常礼的传统的公卿献诗,献诵的主体是工师乐人,故以音乐为主,语义则被乐章遮蔽,作为文本的诗并不受关注。而春秋的断章赋诗则转向了诗,即文本信息的使用,乐反而退居次位,甚至通常并不具备和乐的条件(徐正英也说鲁僖公二十三年开始的诸侯聘问赋诗之风,导致了诗与乐的分家。同书219页),赋诗主体亦随之由工师转向诸侯卿大夫。正因这是一种新变,所以有些贵族,如卫之宁武子、齐之庆封、宋之华定,尚未能适应此一情况,以至不能答赋。尤其襄公二十七年鲁叔孙豹为来聘的齐庆封赋《相鼠》,庆封竟懵然“不知”。过去我读这段,非常不解。按曹氏的说法:“相信如此直白且尖锐的内容,如果是直言诗文,就算是庆封再糊涂,也不至于不知是讽刺自己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庆封听到的不是文辞,而是乐章。而且赋诗是发生在宴饮之时,赋诗者不当是叔孙穆子本人,而当是乐工。”如此,则情理可通。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果说发生在文公四年的宁武子被赋《湛露》《彤弓》,而不能答赋,是因“‘赋诗断章’出现之始,交流尚未形成共识。”那么,襄公二十七年的庆封被赋《相鼠》而不知,已上距离宁武子七十七年;昭公十二年宋华定被赋《蓼萧》而不能答,更上距宁武子九十三年,早已不再是风气之始。何况在庆封“不知”的次年,卢蒲葵即提出“赋诗断章”之说,可见此风气早已弥漫开来。而早于宁武子三十七年,在闵公二年时,卫之许穆夫人已能赋《载驰》。因此,说赋诗有工诵奏乐与卿大夫的口诵之区别则可,说“交流尚未形成共识”则不可。
周时的乐、舞、诗,和礼一样,是贵族子弟都要修习的,乐舞并非专属工师之事,这通过文献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作为乐语的诗,同样受到重视,一开始就是乐教的题中应有之意,《周礼·春官·大司乐》所谓“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应当不是后起的现象。所以,能否通晓交际中对方所诵之诗并妥善地答赋,是卿大夫个人的修习程度的问题,存在个体差别,在所难免,而非风气之初渐的问题。如众所周知的重耳与秦穆公之会,在僖公二十三年,早于宁武子事十四年。重耳到了秦国,将见穆公,原本打算带子犯去,子犯推辞说要让赵衰跟着去,理由是“吾不如衰之文也”。在宴会上,果然遇到往复赋诗的活动,在赵衰的佐助下,重耳很好地通过几番赋诗,完成了与穆公的沟通,使之决定出兵助其返国。此事至少可说明两点,一是赋诗活动此时早已成为风气,所以子犯事先就有预料,故推荐赵衰赴宴。二是虽然卿大夫所受教育大体无别,但赋诗能力确有高下之分,子犯和重耳都远不如赵衰。即便到了春秋后期,孔门弟子普遍接受诗教,也有在文或言语能力方面的突出与平庸之不同,所以孔子提示学生注意学诗的“专对”之用,否则,“虽多,亦奚以为?”学是都学的,运用的能力却相去甚远。
反过来说,即便“乐语”方面得到了不断的重视,以至于孔子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可是类似工师演奏的本事,也仍然不能丢掉,“乐亡而礼从之”,所以儒家要特别坚守它,诉诸训练与实践。因此,不仅孔子生前“讲颂弦歌不绝”,“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即便到了秦末,高祖围鲁时,仍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的景象。当然,儒家的努力并不能阻挡乐普遍衰落的现实,而诗又何尝不然?在口头上,战国行人辞令的兴起,致使赋诗没了用武之地,而退缩回文本。乐与诗,大体是个共进退的情形。
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的《的形成》,是思考浓度很高的一篇文章,随处可见对习见文献的幽曲而富有意致的解读。尽管题目看起来非常疏廓而老套,作者触及的很多问题却富有新意,看法或思考方向的新颖别致,也多非国内学者所能及。更为难得的是,他对诗的礼仪功能、诗乐之关系的理解,以及用传世文献与出土铭文的不同层次的比对,也非常在行。如强调汉代的注诗,不是从诗中“提取”历史语境,而是把历史语境“注入”诗中,巧妙地点出了汉儒释诗的真相。“历史化”是战国以来的一股风潮,不知是否与王室史官的出奔以及诸侯史乘的外溢有关。“六经皆史”是不断建构的结果,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神话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化的处理,确有道理。历史化的不断持续,记忆与虚构的混杂和往复推动,就形成“层累”的现象。
柯氏提示颂诗中可能存在的“模块”,很容易让人想起雷德侯的《万物》。尽管“模块”说显得过于机械,实际上在“三百篇”中也并不普遍。但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颂诗在使用时乃由多首构成一个更大的演奏单元的现象,尤其是《大武舞》的老问题,如今又在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反过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颂诗篇幅都非常短小。诗是从属于乐舞的,而舞的表演,尤要变换段落乃至场次,一以配合叙事,有如西方戏剧之数“幕”;一以变换舞容,打破沉闷,持续攫获观者的注意力。王国维很早就指出颂乐舒缓,这也很可能是颂诗不长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或许可以说《周颂》不是独立撰写的文本,而是取自一个公共诗库的素材(shared poetic repertoire)的变体。这一公共诗库更多仅限于《颂》本身(后世宫廷颂诗偶尔也从该诗库中借用诗行),还受到仪式表达形式上和语义上的束缚。”这样的判断却不符合实际。柯马丁甚至认为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国风》中,提出早期的诗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原本”,“每首诗的诗题都指向一个有一定范围的语料库,它在不同情况下能以不同方式被实现。”
然而,语料库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我相信《周颂》中的相当一部分就应该是“独立撰写的文本”,而当这些文本成为典则之后,才会出现局部的所谓“借用”现象。所借用者多为“套语”,作为素材的“诗库”还谈不上。套语的使用类似后世的“引用”的行为,此现象《易》中也常见,而不必作为“素材库”来理解。同时不能忘记,它们首先是作为乐舞的单元而非文本单元被组合或引用的。柯马丁类似的分析最终还用于《江汉》一诗,认为它由不同段落和文体拼凑的痕迹很明显,尤其是其中册命的部分。可是全诗记述召虎南征之事,是统一的。《江汉》属于李辉所谓西周后期新兴的“公卿赞歌”的典型,是把册命之辞化为诗句的一个典型,而非孤例(同书,295)。柯氏的用意在于强调《诗》是编辑而非创作的产物,这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指出《江汉》和类似有合成痕迹的《楚茨》不见于任何其它先秦文献的征引,其实并不奇怪,恰好可用于印证此类赞歌的私人的属性。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和《耆夜》中的《蟋蟀》,近来引起了学者们关于孔子删诗之可能的思考。但我总觉得,《诗》的异文情况是非常可能的,每种本子从内容到数量上会存在着各种差别;可是它自身应当是确定的。就像《周易》与《连山》《归藏》那样,各本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同本的文本则较为固定。只有这样,使用起来才更方便。而表演者要在演奏现场从一个原料库中临时抽取,随机组合,听起来殊无道理。尤其像内容连贯完整者如《将仲子》《氓》之类,很难想象是拼凑而成,而这类文本在风诗中的比例很大。至于柯马丁指出三百篇“保存了口头的精英共同语(élitekoiné)”的问题,实际上已由缪钺做过论说,缪氏收在《冰茧庵丛稿》中的《周代之“雅言”》对周代共同语的论说非常精湛,可惜很少见人谈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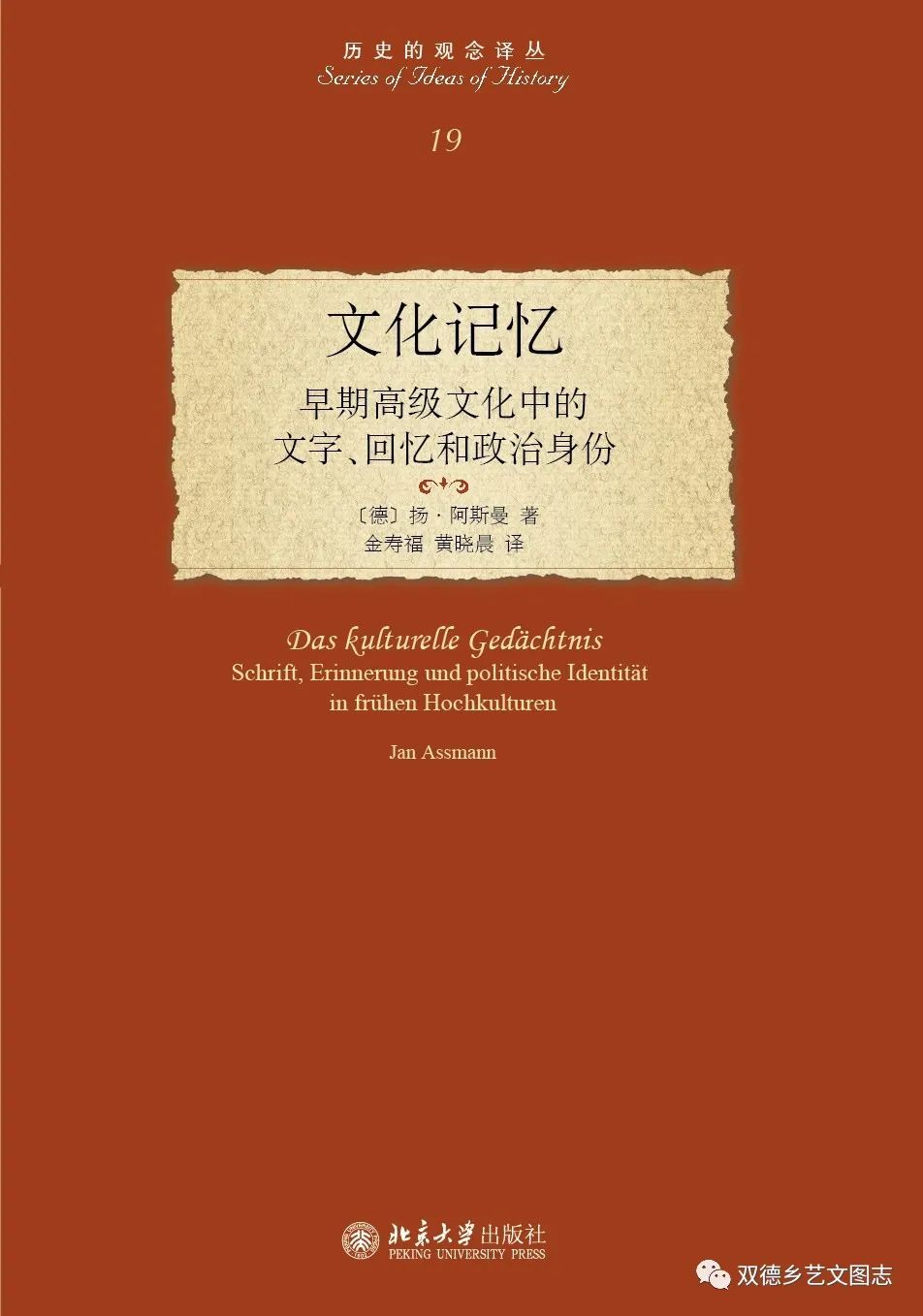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 黄晓晨 译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文中提到了几种令我很感兴趣的著作,虽然读不了西文,还是要记此以备查考:一是柯氏自己的《古代中国的文本、作者和表演:文学传统的起源和早期发展》(Texts,Authors,and Performance in Ancient China: The Origins and Early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据说是即将完成的新著。二是王靖献(杨牧)的《从仪式到寓言:七论早期中国诗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三是德人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Munich:C.H. Beck, 1992(此书已有中译本)。四是美国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作者问题和文化认同:文学流通模式》(Authorship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0。
姚苏杰的《重章结构的形态与类型》,是篇牛文,作者当有理科背景。运用了模型统计的方法,发现了三百篇重章结构的一系列问题。他的统计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引出更多的认识。他还作有古典文学及青铜铭文的篇章结构研究。这些至少反映了早期文本制作和使用的“仪式-程式”特征。姜晓东《周代歌诗演唱艺术与作品的文体形式》通过《耆夜》《益稷》《卿云歌》想象三百篇的歌诗在应和对答中可能包含的不同抒情主体,由此论及诗篇的章句划分问题。他将《卷耳》解作周人的“祖道”之祭,也令人耳目一新。许志刚《成书辨析》指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关于《礼记》传本的情况的介绍,全袭自《隋书·经籍志》的谬说,令人瞠目。台湾清华大学朱晓海《论》强调《楚辞》与屈原乃一体之两面,只有屈原所作及代屈原言的作品,才能称作楚辞。这个说法也值得重视。
2022、11、28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