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FUDANJOURNAL(SocialSciences)No.3201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夷坚志》中的“乡民”描写及其文化阐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南昌大学中文系,南昌330031)[摘要]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市民视角上,而基本忽视了对乡民故事的考察。南宋洪迈的文言小说集《夷坚志》中乡民人物类型众多,故事题材丰富,可谓中国古代小说乡民描写之集大成者。具体分析这些有关乡民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基数最大的这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我国民问社会的教化观、信仰观和道德伦理观。[关键词]《夷坚志》“乡民”描写文化阐释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市民”这一群体,如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宋元话本中的市民生活、“三言二拍”和明清拟话本里的市民意识等等,而对“乡民”这一群体则基本忽略。经笔者查阅1915--2012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关于市民文学的研究文章共计3264篇,而有关乡民的文章却一篇都无。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基数最大的是农业人口,“市民”并不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主力人群。
同时,中国古代小说中也并不都是反映“市民”的作品,其中不乏对“乡民”的描写。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在关注“市民”的同时,不妨将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乡民”,转向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基数最大的这一群体。南宋时期洪迈的文言小说集《夷坚志》,是一部较多反映乡民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作品。据笔者统计,在《夷坚志》全书207卷2737则故事中,涉及乡民的有225则,约占全书十分之一。本的民众;他们或为从事耕作的传统意义的农民,或为乡村(镇)中的富者和商人,以及活跃于乡村(镇)间的三教九流。研究《夷坚志》中的“乡民”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及其文化意蕴,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学画卷中完全不同于市民文学的色彩斑斓的另一面。《夷坚志》中塑造的乡民形象很多,按照社会角色或经济地位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是以耕作为生的农民。《夷坚志》中对这类角色往往没有过多的语言描述,与其称其为角色,不如说是符号更为合适。如《观音医臂》中观音治好村媪久病不愈的手臂的故事(甲志卷十),《观音偈》中一患腿疾的农夫通过诵念观音偈而痊愈的故事(甲志卷一),以及《三河村人》中同邑村民梦魇成真的故事(甲志卷一)。这类农民一般都没有姓名,**以“村妪”、“农夫”、“村民”之类统称。
[收稿日期]2012—10—12[作者简介]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本文为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本文所引作品,均出自中华书局1981年版《夷坚志》。为行文方便,不再胪列出处。74万方数据作者在讲述时,也多以“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以及“同邑有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等简单笔墨带过,主要则放在与之有关的一些离奇情节的叙述上。如《观音医臂》、《观音偈》主要突出观音、观音偈治好村妪和农夫的神力,反映了乡村观音信仰的普遍;《三河村人》主要渲染村民梦魇成真的奇遇,反映了乡民的胆小和愚昧。可以说,他们只是故事名义上的主人公,我们很难在其中看到他们作为小说人物的能动性行为和富于个性的面目,其作用倒更像是讲述故事时所必需的道具;作者也未赋予他们更多的形象意义,他们既不是被讴歌赞美的人物,也不是被讽刺挖苦的对象,仅具有一定的叙事和结构上的意义。但他们作为乡民中的主要群体,其角色意义在小说史上还是值得关注的。第二类是乡村中的富者,其职业身份和致富原因常常并不具体交代,只以“富室”、“富家翁”、“员外”等相称。
与我们的印象不同,这类人往往不是“为富不仁”者,而多是正面形象,受到褒奖,得到善报。如《蒋员外》中的主人公经常帮助乡人渡过难关,如有不孝子卖祖宗田产,他会随其价买人,然后无偿赠还。正因为其“轻财重义”,所以泛舟出海遭遇风浪时仿佛有神人相助,免于溺死(甲志卷七)。同样,青田乡的富室在水灾来临时,第一时间记挂的并不是运送家产,而是乡人安危,其船“往来十余返”,使得乡民“脱沉溺之祸”,最后在一片汪洋之中,“富翁”居所“什器箱笛,按堵无恙,惟书策衣衾稍沾湿而已”,善人终有善报(支戊卷六)。还有富室张二十四郎,也是因为“能施德于乡间里中”,“一乡遍受其惠”,因而感动了同村盗贼及外村同伙,使其免遭盗贼的劫掠(补卷二十四)。以上是既富且仁者,其中也有为富不仁者,如《毛烈阴狱》中叙“沪州合江县赵市村民毛烈,以不义起富。他人有善田宅,辄百计谋之,必得乃已”,最终因专干“诈得人田”而被阴司追索性命(甲志卷十九)。这类为富不仁者往往没有好下场。第三类是身处乡村的小商贩。此类人物数量较多,他们并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不以农耕为业,而是靠经营一些小本生意维持生活。如以贩猪为业的《陈承信母》中的陈承信,“以鬻民;“以弋猎为生”的《休宁猎户》中的张五;“以煮蟹自给”的《沈十九》和《张氏煮蟹》中的乡民;“以屠牛为业”的《何百九》和《董白额》中的村民;还有以开旅店谋生的《浦城道店蝇》中的村民,等等。
此外,这类小商贩还从事鬻粥、卖蝉、杀蛙、鬻海狮、鬻螺蚌鱼鳖等各种名目的小本生意。富有意味的是,从事这些生意的乡村小商贩大多由于职业杀生,其下场往往悲惨,不仅祸及自身,甚至殃及全家。第四类是乡村中的三教九流。乡村中往往有一些“异人”,他们身怀法术,如《余荣古》中余荣古会“五雷法”,能治愈耕牛的病疫,也能使“如狂如痴”的病人“平安如常”(支乙卷三);周狗师的“剌泉之法”,能“以纸钱十数束,猪头鸡鸭之供,乘昏夜诣湫洞有水源处,而用大竹插纸钱入水”,则“不移日,雨必降”(支乙卷三);《张妖巫》中的巫者张生,善为妖术“打筋斗”,“能与人致祸”,或病或死,人人“莫不畏惮”(支丁卷四);《方大年星禽》中的村落术士方大年,“精于禽课”,“卜应如响”,在他卦银,银又为金”(甲志卷十六)。他们有的还能预知未来,如《黄五官人》中道人清楚地预见黄五考试登第(支乙卷二);《玉山陈和尚》中陈生遇见道人后,“心神顿清,自是遂能言未来事”,可以准确地预见雨期,“日某日某时,不差晷刻”(三志辛卷六);《曾三失子》中农民曾三问卜于术者胡九龄,胡认为兆象不佳,“必有人口灾殃并妖异不详之应”,果然曾三儿子不知所终(三志辛卷十);《杳氏村祖》中更有“翁媪二人,兀然如土木”,“不知几百岁”,被杳村人供为村祖,应该也有过人的本领(乙-t。
-。。1-)。此类身怀异术者还有着侠义心肠,能够代人受过,如《叶道行法》中叶法广,认为朱某一家平时奉香火甚谨,愿意“以身代死”,后来“朱室平复如初,法广遂死”(三志辛卷七)。这些人本领各异,善恶有别,但大多和巫、巫术有着某种联系,在小说中常被称为“村巫”或“乡巫”,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乡村地区巫术的盛行及其势力的根深蒂固。75万方数据以上是对《夷坚志》中乡民形象的大致区分,需说明的是,这也许并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如 “富人”并不是一种职业定位,和其他三类不完全一样,本文也没有划出“穷人”一类。但《夷坚志》 是小说而不是著作,我们只能按照它实际写到的乡民形象进行大致的区分。 除了人物形象的划分之外,《夷坚志》中有关乡民的故事类型也很有特色。一般情况下,故事 类型的不同是基于人物类型划分的结果,但我们发现,在《夷坚志》的乡民故事中,同样的人物类型 可以出现在不同的故事类型中,而同样的故事类型中也有不同的人物类型,所以有必要再对其中乡 民的故事类型进行梳理,使我们对其中的乡民描写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和上述人物类型一样,故事类型的划分也只能是一种大致的题材分类,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遇怪类型,这是书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正如作者在《夷坚丙志序》中所提到的,“始予萃 《夷坚》一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也”,可见,“鸠异崇怪”是整部小说创作 的主旨,这也决定了它必然是故事的主要类型。其中有关乡民者当然更是如此,所谓少见多怪,乡 村社会的迷信、落后和闭塞,加之荒村野店的自然环境,自然是孕育和诞生遇怪故事的肥沃土壤。 在《夷坚志》的相关描写中,作为“怪”的动物种类远比城市为多,野生动物有龙、虎、蛇、狐、龟 等,家禽动物有猪、犬、牛等,大多与农耕社会关系密切。 龙与虎。如《复塘龙珠》中描写的在乡村出现二龙相斗的奇观:“豫章武宁县复塘村,乾道己丑 岁七月二十一 Et,白昼雷雨大作。数牧童放牛垅上,见西北方电光中二龙斗,良久,东南震霆数声 起,逐退之”(丁志卷十九)。其实世上并无“龙”,这只是夏天雷雨时云气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景观 而已,因乡村天地开阔,所以能偶然见到,而城市受视野所限,无缘得见。特定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人 与动物特殊的共生关系,如《鹳坑虎》中呈现出乡民与老虎之间和睦相处,农妇亲切地称之为“班 哥”(甲志卷十四),仿佛在称呼自家的孩子,这与一直以来“虎为灵物,不妄伤人”的传说有关,更体现 了乡民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
乡民小说中的精怪以蛇为最多,这与农村多山多树、人烟稀少有关。“长仙”在乡民口耳相传 过程中,大概只有“黄仙”(黄鼠狼)可与之匹敌。如《京西田中蛇》中胡德因为杀蛇而使村妇人痛 哭,买下蛇头来埋葬,这是因为乡民害怕蛇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丁志卷四)。在《易村妇人》中, 由于蛇瘟而使得“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殆半”,令人恐惧(支景卷二)。至于蛇化为人形,《夷坚 志》中记载更多,如《蛇妖》一篇开首称“蛇最能为妖,化形魅人,传记多载,亦有真形亲与妇女交会 者”;接下来一连记载了四个有关村妇被迫与蛇妖“野合”的故事,其中蛇往往化为男性,面容可怖, 或“昂首张口”,或“举首怒目,呀口吐气,蓬勃如烟”,或“咽间有声呜其傍”,而村妇被奸淫后往往 大病一场,甚至妊娠,遭受巨大的痛苦(Y 志卷--t)。其他如《余干民妻》等篇也有类似描写。 “蛇禁忌”源于对蛇的恐惧,正如西方民俗学家柯克士所说,对“蛇的崇敬,为恐惧所养育 着”。上述有关蛇的故事印证了这一点。只是在书中,蛇与市民、蛇与乡民两者呈现出不太相同 的关系。在上述蛇与乡民两者的故事中,蛇多为男性,专以胁迫淫辱乡村妇女为能事,面目可憎;而 在《夷坚志》有关蛇与市民的故事中,蛇则多为女性,且美丽温柔,多人情,少妖气。
如《衡州司户 妻》中蛇妻“盛年有姿色。与同官家往来,和柔待下,皆得其欢心”,但因“舌表两歧”,难掩蛇迹,被 做官的丈夫察觉后,泣语夫日:“与君缘分止此,行当永诀。”果然“明日而病,顷刻而沉笃”(支癸卷 ill钱炎书生》、《历阳丽人》等,其中的蛇女皆为美女,或“雅善讴歌,娱悦性灵”(补卷二十二),或“商摧古今,咏嘲风月,虽文人才士所不逮”(三志辛卷五),有貌有才,本与丈夫(身份为书生和县尉 子)和睦恩爱,却被多事者请来法师施以符术,或逃或死,男女被生生拆散,其故事母题大多与四大 柯克士著,郑振铎译:《民俗学浅说》,见《郑振铎全集》第2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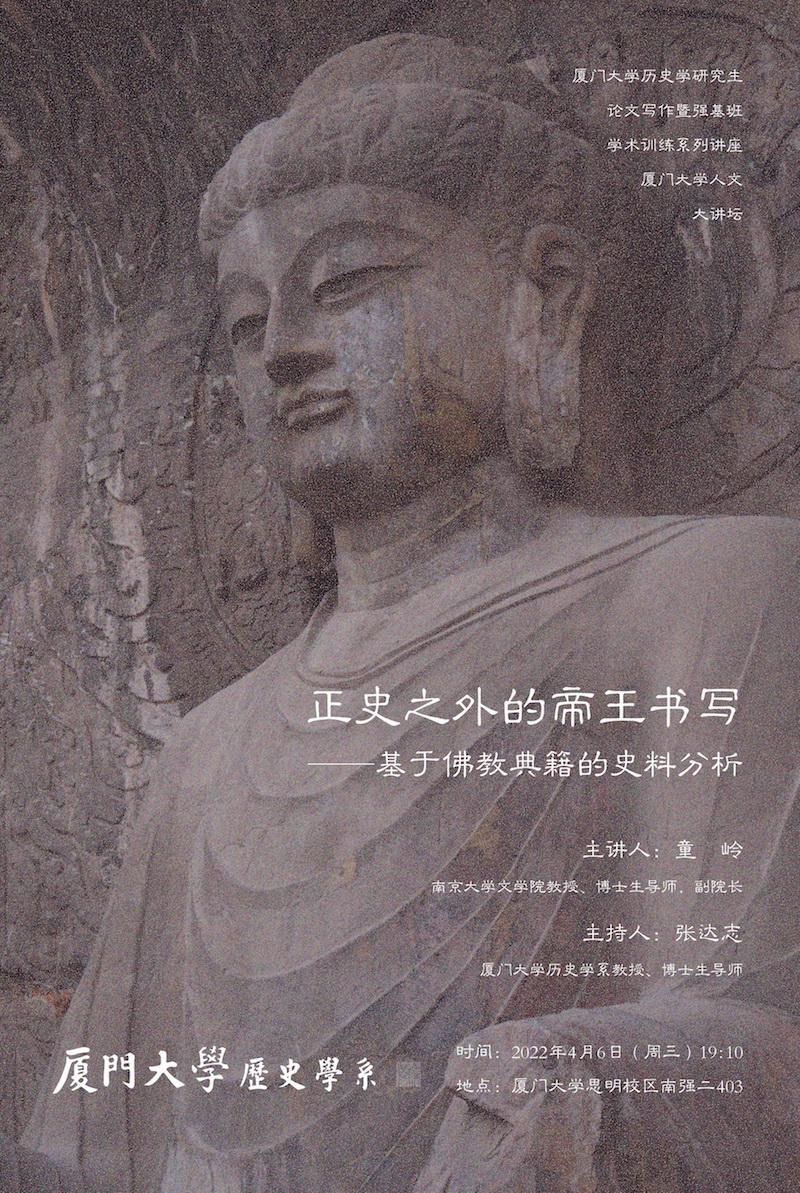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