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张燕/撰稿 童岭/审订
2022年4月6日晚,“厦门大学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写作暨强基班学术训练”系列讲座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庄汉水楼403举行,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教授受邀以《正史之外的帝王书写——基于佛教典籍的史料分析》为题展开演讲。本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张达志教授主持,来自历史系的陈博翼老师、七十多名强基班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共同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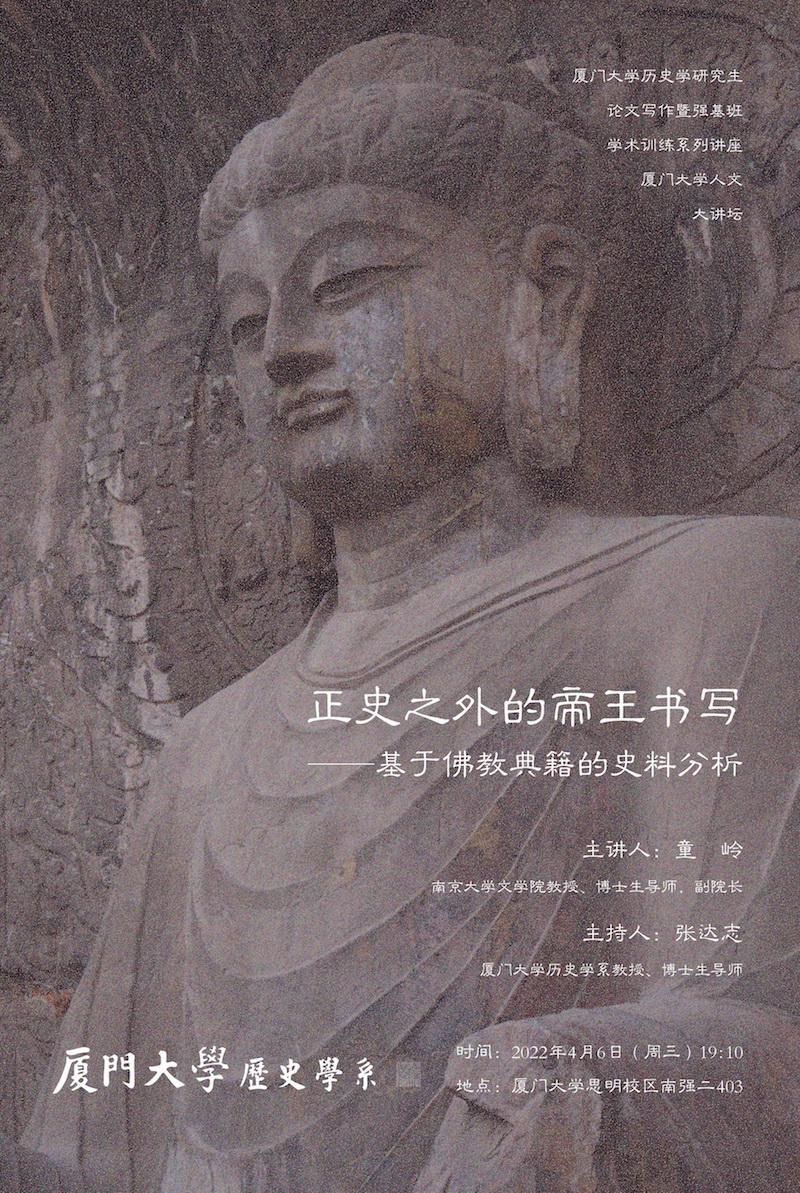
引言
讲座伊始,童岭教授从今年清明节南京鸡鸣寺举办的线上祭祀先人的“梁皇宝忏法会”说起。《梁皇忏》又作《梁武帝忏》《梁皇宝忏》,是梁武帝为超度其夫人郗氏所制之慈悲道场忏法,该忏文直至现代仍在祭祀中被使用,展现了不同于正史记载中的梁武帝形象。本次演讲共分成六部分,关注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汉传佛教的鼎盛时期。

《梁皇忏》
一、皇帝如来:五胡至北魏中国佛教之特质
童岭教授首先强调五胡十六国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重要一环,而建都南京的汉人正统政权晋、宋与之南北相对,这是一个中心失衡的分裂时代;继而阐述北方的“国家佛教”与南方佛教发展路线之不同。
其一,北方“国家佛教”。五胡十六国至北魏,拥有能够预言胡族国家命运、战争胜负等能力的高僧成为华北各族君王的镇国之师,尤以北魏时代最为突出。为阐释“国家佛教”的内涵,童教授列举了两个典型案例:一者,某次佛图澄为石虎预言失败,导致石虎暴怒并欲加害僧徒,故佛图澄以佛教的“前世今生”之说开解石虎;二者,北魏“皇帝即如来”的佛教观念:如云冈昙曜五窟中,五尊如来佛像完全模拟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学界通行的说法)。此外,北魏第一代僧官法果尊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为“当今如来”,明确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卷一一四)。由此明确沙门应礼拜帝王,从而调和佛教出世精神与儒教君臣理念的矛盾。
其二,南方“沙门不敬王者论”。在东晋、南朝,因为贵族势力的强大与皇权的相对衰弱,高僧主张保持佛法的独立性,慧远即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高僧传》卷六)。江南佛教的发展脉络虽然不同于北方,但成书于梁代的《高僧传》专门立有《神异篇》,这却是“高僧拥有预言能力”之思想在南北方中国都有风行的印证。
童岭教授以高度鲜卑化的汉人——高欢、高洋父子为例继续探讨北方的“国家佛教”。首先,童教授简要介绍高氏一族的发展历程,展现其鲜卑化程度之深。继而以多个案例描绘北齐佛教之兴盛及“国家佛教”的发展:其一,僧尼人数众多,据《魏书》卷一一四载:“(北齐)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二,高欢在晋阳与邺城之间的太行山支脉上修建响堂山佛教石窟,其第九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是国内石窟中最大的一幅,而中心方柱顶部据闻是“高欢陵穴”。其三,高欢通过观音信仰的传播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以树立其权威。如他在位时期编撰《佛说高王观世音经》,分序、正宗、流通三部分,其子高洋将其定为“国经”。

北齐响堂山第九窟:高欢陵穴(童岭 摄)
随后,童教授着重向大家展示正史与佛教史中对高洋形象的不同描述:在正史中,他是集勇武者、荒淫者于一身的奇特人物;但在佛教史中,他却又是一位虔诚的礼佛者。高洋在天保九年(558)建造了大庄严寺,还两度行幸甘露寺,准备在此寺中“禅居深观”。高洋视高僧法上为“佛”,便曾模仿燃灯授记的场面,匍匐于地,请法上大师践踏走过。童教授特别推荐了孙英刚《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中古燃灯佛授记的政治意涵》(《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一文,该文认为高洋通过这样的仪式,塑造自己佛教转轮王的身份,从信仰和政治的双重维度加强统治的神圣性。
最后,童教授对前两部分作如下总结:在中国五胡北朝时期形成的王法一元——“国家佛教”可谓影响极广、极深,尤其在传播到朝鲜半岛与奈良时代的日本后,他们将中国中古时代的“国家佛教”发展到新高度。
三、流星王朝:隋代佛教史的再定位
首先,童岭教授阐述历史书写的内涵:中古时代,每位史学家(包括佛教史学家)都会从各自的知识背景与社会经历所形塑的思想内核来进行史学书写,因此对一件史料的史学阐释存在着不同层级的弹性。特别是拥有完全独立时间观、世界观的佛教史学,用高僧道宣之语讲,虽然是“至道无言”,但“非言何以范世”。
接着,童教授呼吁若欲定位隋代佛教史,则须关注周隋禅让之前的北周武帝灭佛事件,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五胡”,甚至声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广弘明集》卷一〇)但随着他的去世,其废灭佛道的措施也被逐一取消。镰田茂雄敏锐在《中国佛教通史》中指出,北周毁佛才正是孕育中国佛教的母体大地。
而后,童教授认为,隋文帝杨坚在诸多宗教制度层面,一改北周武帝宇文邕的佛道弹压政策,汉传佛教在中土绽放出华丽的花朵并结出丰硕的果实。虽然“开皇”这一年号本身具有道教意义,但这并不代表杨坚反对佛教,相反,这正是三教融合的一种表征。此外,在此时期,被称为“中国佛教史学之父”的高僧道宣著有《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等“佛教历史”的三大著作。境野黄洋很早就指出,这些著作蕴含“史学性质的趣味”(《支那佛教史の研究》,共立社,1930年)。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便多次提到,对于生活在北朝后期过度到隋,或再入唐的僧人群体来说,最大的一次灭法记忆就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废佛事件。道宣在言及北周灭法时,常常也跟叙到隋文帝的复兴之举,这种对比非常有突兀感。童教授通过对比此段叙事中的“帝王书写”,发现道宣秉持着贬北周武帝而扬隋文帝的一贯书写理路。
四、开皇神光:隋文帝在佛教史上的形象
童岭教授首先列举多则史料,论证佛教史中隋文帝杨坚的形象。首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载:“开皇十五年秋夜,神光自基上绕,露盘赫若冶焰,一旬内四如之。”此句照应本部分标题中的“开皇神光”四字,描绘出隋文帝在佛教史中的正面形象。又如《续高僧传》卷一九中称隋文帝夺位登基为“丞相龙飞”,是极正面的书写,甚至饱含赞美之意。杨坚的小名叫做“那罗延”,梵语为nārāyana,是金刚力士之义。
费子智(C.P.Fitzgerald)也说,隋王朝的奠基者杨坚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精英教育的人,也不打算取悦官僚阶层。但是对于重兴佛法,他却亟亟以为己任。据《资治通鉴》卷一七五载,隋代“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可见隋文帝的国教政策在三教融合的另一面是以佛教为主,儒道为辅。隋文帝崇尚佛法的最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诏令普天下修建舍利塔,正史中对此记载较少,反而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不惜笔墨记载了此份重要诏令。佐佐木功成在《仁寿舍利塔考》中对此评价道:“仁寿舍利塔的建立,是承接周武法难之后,中国佛教在全国复兴的动机。”奉纳舍利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灵塔供养,体现了隋文帝以王权来弘法的决心。

南京栖霞寺隋仁寿舍利塔(童岭 摄)
与佛教史中杨坚的正面形象正相反,由于正史比较同情前朝的靖难者,故传统史书、说部文献对杨坚的评价并不高。为说明此问题,童教授列举尉迟迥叛乱事件。杨坚即位不久,相州总管尉迟迥等人打着勤王口号起兵作乱,但很快便被隋廷扑灭。传统史书中对尉迟迥颇多同情之语、赞美之词,如《资治通鉴》卷一七四中形容尉迟迥在得知杨坚上位后,号召“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然后举义军进攻关中。这种同情尉迟迥的默认逻辑,一直到现在的漫画如许先哲《镖人》都有体现。
反观佛教史则以决然不同的视角褒美隋文帝,贬低尉迟迥,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记载了隋高祖处置尉迟迥一众的详细过程,并有“贼止蔚廻,余并被驱”的负面书写。相较于正史所载,道宣笔下可谓无声的批判。
最后,童教授指出,从佛教史的角度出发,尉迟迥的抵抗活动不具有正义性。佛教史学与正统国史系统的记载,在这一事件的错位与重合之处,不得不说是提供给后世研究者回溯隋初史实的一段珍贵对比文献。
五、大业沸腾:隋炀帝时代的佛教与政治史
童岭教授认为,隋文帝与隋炀帝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前后贯穿的传承关系。但相对于隋文帝注重外在形态(修建舍利塔等)的大力崇佛,隋炀帝更加精于在学理上弘扬佛法。他登基后,把其晋王时代的江都四道场“复制”到东都四道场。隋炀帝虽然绝不是北周武帝那样的灭佛天子,但他诸多不合人心的举措导致“天下沸腾”,佛教徒认为佛法在这沸腾世界中也岌岌可危。
正史系统与佛教史对隋炀帝的书写亦大为不同,童教授列举杨玄感叛变事件对此加以说明。《隋书·杨玄感传》对于杨玄感反隋失败可谓充满“同情”,卷首谓其“体貌雄伟,美须髯。”《资治通鉴》亦“同情”杨玄感,批判隋炀帝杀戮过多。反观佛教史中对杨玄感颇多贬低之语,“枭感起逆”、“枭感作逆”之词不绝于书。
最后,童教授由此延伸至唐代初年历任统治者对于佛法的态度问题。唐高祖和唐太宗对于佛教并未表现出崇信的态度,相反,他们父子都有一定程度的抑佛政策。如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并进入洛阳城后“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洛阳壮丽的佛寺和绚烂的宫殿,一起被凯旋进城的李世民基本摧毁殆尽。又如武德九年四月,唐高祖接受太史令傅奕废除佛法的建议,下诏沙汰僧尼。而唐太宗虽以超高规格迎接玄奘回国,但本质上对玄奘带回的六百多部佛典不感兴趣,而是对记载西域沿途情报的十二卷《大唐西域记》兴趣盎然。
六、则天武后:世界帝国与佛教中心
童岭教授指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武则天为了完成唐周革命而利用佛教,并非真心崇佛。对此,童教授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观点陷入了“庸俗政治学”和“阴谋论”的陷阱之中,理由如下:首先,从心理史学的角度来看,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隋朝皇室、曾任隋纳言杨达的女儿,杨氏继承弘农家族的传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受其母亲影响,武则天很可能并非利用佛教,而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佛教。其次,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康居的高僧法藏,在为《华严经》作《传记》时,将武则天塑造成世界的佛教君主。童教授继而又列举具体事例论证其观点:第一,武则天在分娩之前,请求玄奘传授在家戒。武则天之子出生后(未来的唐中宗),玄奘成为其皈依法师,为其取名“佛光王”。第二,武则天准许在翻译佛经时不避讳。在财力与政策支持之下,从弘道元年(683)开始,大量重要汉译经典涌现。
而后,童教授援引加拿大陈金华先生的观点:“在宗教方面,武则天总的来讲是以佛教为主,但是她所开创的佛教与政治的互动模式,特别是佛教在其整个帝国中的作用,都属空前。不仅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甚至于在整个世界佛教史上也是空前的。”
接着,童教授简要阐述武则天崇佛的具体举措,尤以佛教建筑的兴造为主,突显中土作为佛教世界新中心的地位。其一,建构五台山与文殊信仰。通过把五台山改造成文殊的道场,彰显中土作为世界帝国新中心的地位,可以说是佛教对世界新秩序的塑造。其二,垂拱四年(688),在紫微城内修建天堂,即礼佛堂,内置大佛。其三,同年,修建万象神宫,即明堂。其四,长寿三年(694),建造具有佛教中心意味的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在营造过程中,来自高句丽的泉献诚和来自波斯的阿罗撼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则天天堂的大柱础(梁爽 摄)
结语
讲座的最后,童岭教授总结道:“历史的真相具有史实与阐释(讲述)的双重性,对于错综复杂的中古史来说尤其如此。史实与阐释相比,固然史实终于阐释,但一个史实在被阐释(讲述)之前,仅仅具有文献学价值,不会产生广泛的影响。阐释的方式、力量决定了史实的再现程度。中国中古制度史如此,中古佛教史亦存在类似的传承理路。”
随后,张达志教授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体悟和思考,并感谢童岭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将来应组织更多的交流会,以促进厦大的资源整合,推动学科积极向上发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