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周一渤
文/洪烛
2008年的八大胡同地区

倚门卖笑(倚门卖笑的意思)
八大胡同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把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之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小戏班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诸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有2.5万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夜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这些地方共有娼妓二万五千人。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民国时期八大胡同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不太清楚。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的……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18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好像这也是有传统的。更早的时候,宋徽宗就尝过去民间做嫖客的滋味。他迷恋东京名妓李师师,偷偷挖了一条地道通往妓院。不仅跟“追星”的词人周邦彦“撞车”了,还中过梁山好汉宋江的“埋伏”。
赛金花
明末出了个陈圆圆,晚清出了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赛金花旧居
1936年,刘半农领着研究生商鸿逵访问人老珠黄的赛金花,由赛口述、商执笔,写了本《赛金花本事》。此为比当代的畅销书《绝对隐私》要早得多的“口述实录”。“大学教授要为妓女写书,轰动了整个社会,书出版后销售一空。”(叶祖孚语)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百顺胡同
陕西巷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800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800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40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小凤仙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小凤仙旧居的门槛
有一部老电影叫《蔡锷与小凤仙》,就是表现这位红尘女子跟北伐名将的知音之情。蔡锷是王心刚演的,小凤仙是张瑜演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45家,妓女328人;二等妓院(茶室)有60家,妓女528人;三等妓院(下处190家,妓女。1895人;四等妓院(小下处)34家,妓女301人。以上共计妓院329家,妓女3052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幸好新中国成立后,妓女们也得到了解放。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妓院。“八大胡同”可以休矣!
聚宝茶室门楣
聚宝茶室内景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9号,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荣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45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一听这名字就很媚俗),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5间房,楼上也是5间房,每间房约9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7间房,每间房只有6平方米,后来改成5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6平方米的空间,虽小,里面却浸染着一部血泪史。当然,故事早已失传了,面目模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进进出出的都是旧时代的大款吧?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49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4间房,楼上共16间,楼下也是16间,每间房均10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像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我尝试用现成的古诗句串联一番: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惜只批驳了站在台面上的商女,没来得及讽刺幕后的嫖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嫖客比商女更鲜廉寡耻——那是在花钱买“亡国”啊。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27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4间,楼下4间,两面共16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10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楼宇间的妓女们,为投其所好,即使不会跳埃及的肚皮舞,也得将南美的大腿舞学上几手。嘣嚓嚓,嘣嚓嚓。推金山,倒玉柱。
临春楼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大隐隐于市嘛)。“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此语我是听诗人邵燕祥说的。我想,芥子园,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吧?想这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而邵燕祥,50年代中期,曾和袁鹰结伴去韩家潭小学跟少先队员们见面。是否辅导作文?“那时候还不知道李渔在这条街上住过。只知道韩家潭是所谓‘八大胡同’之一,不免有些感慨;当时看校舍破旧阴暗,猜想或许正是旧日青楼,又不便问,心中如堵。近年有时去铁树斜街(原名李铁拐斜街,颇富民俗色彩,不知为什么一定要改名,是怕误解为嘲弄残废人吗),房管所在那儿;左近属于‘八大胡同’的石头胡同、陕西巷,四十多年前已尽扫勾栏秽气,不过民居没太变样;韩家潭胡同较大,宽敞些,但也绝无芥子园的痕迹了。”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像我前文中提及的叶祖孚、邵燕祥诸君,要么是“微服私访”,要么是不期而遇,都没有大张旗鼓的意思。我本人,也不大敢打着“文化考察”的幌子,去八大胡同探古溯源。甚至写这篇文章,都不得不斟词酌句,生怕错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
至今没踏访过八大胡同旧地,加上不想招惹是非,只得借助前人的文字,想像并评述一番这昔日青楼地带的风风雨雨。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众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正气凛然,可作示范。该序言虽署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听说执笔者正是叶祖孚先生,文风老辣!
我工作过的单位,曾租借泡子河一带某宅院办公。这幢老房子格局较奇怪,四面皆两层小楼,中有天井。房间数量多,但各自的面积小,颇封闭。作为互不干扰的单人办公室倒正合适。于是同事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虽然年久失修,但室内及走廊所铺实木地板绝对是好材料,依旧棱角分明,只不过踩起来咯吱响而已。后来听街坊说,此处日伪期间曾为妓院,各间暗室里皆搁有贴地的榻榻米。有女同胞顿时花容失色,上班时全敞开着门。我想她们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这老宅里有没有孽债,有没有冤魂?说不定曾有铁蹄下的歌女(或慰安妇)在此被逼迫而死呢。天井里本有一口枯井的。我在井边跟领导下过棋。从此尽量绕道而行。
后来,单位搬迁了,离开那幢宅院,那条胡同。大家全由衷地舒了一口长气。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与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民间的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我见过许多幅。她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势、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我看了特别不舒服。那是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的,为了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十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上面这张妓院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对其中的那两位表情尴尬的女性,我很怜悯,有什么办法呢,身若飘篷的弱女子,只能随波逐流地忍受命运的摆布;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
著名妓女合影
我关心的是:在画面之内以及之外,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真够窝囊的,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更顾不上照料皇城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国夫人的诗句(当时她所在的王国的军队,全部向入侵者缴械投降了),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这张八国联军逛窑子的照片,是侵略者亲手拍摄的。他们以此纪念自己的双重征服(或全方位的征服)?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作为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
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
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
他们通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莫非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虽经历了几千年兴盛衰亡的大循环,却一向被公认为是“乐观”的民族?
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屡屡受伤,很容易受伤。却很少真正地“伤心”。因为他们掌握了遗忘的技巧。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要活下去,就得朝前看。你说这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也罢,你说这是民族性格中坚韧的一面也罢。
毕竟,而今的中国人,已彻底改变了“亡国奴”的身份,并且“洗脑”般地摆脱了耻辱的记忆。
可我想,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
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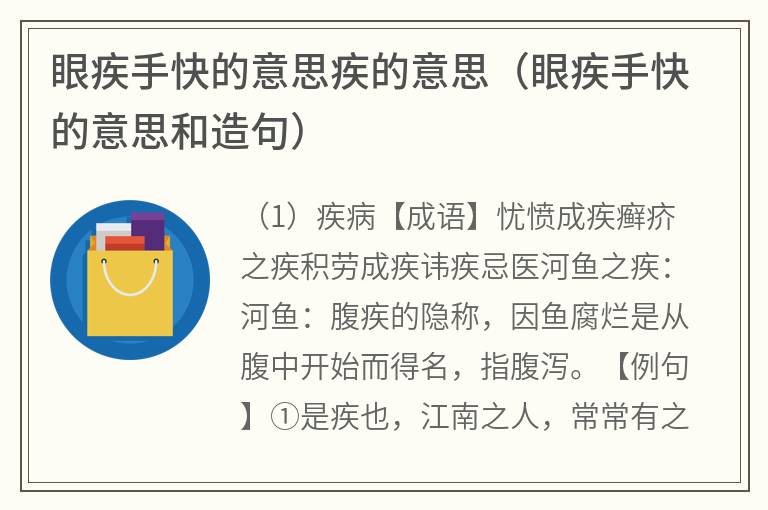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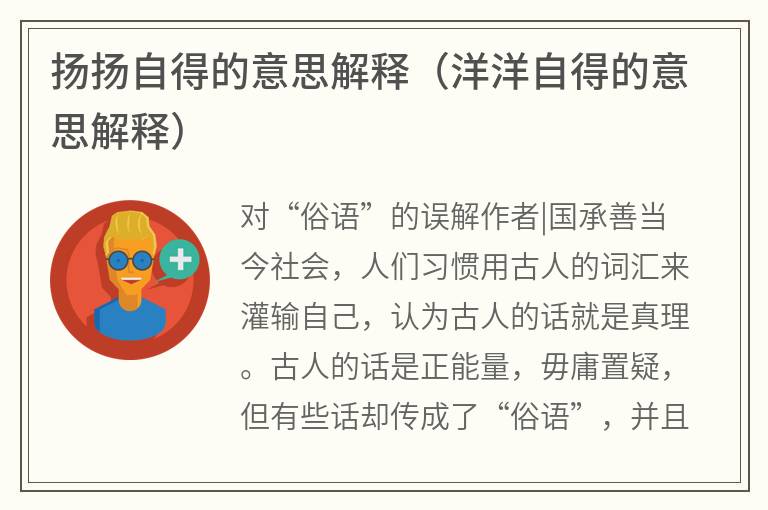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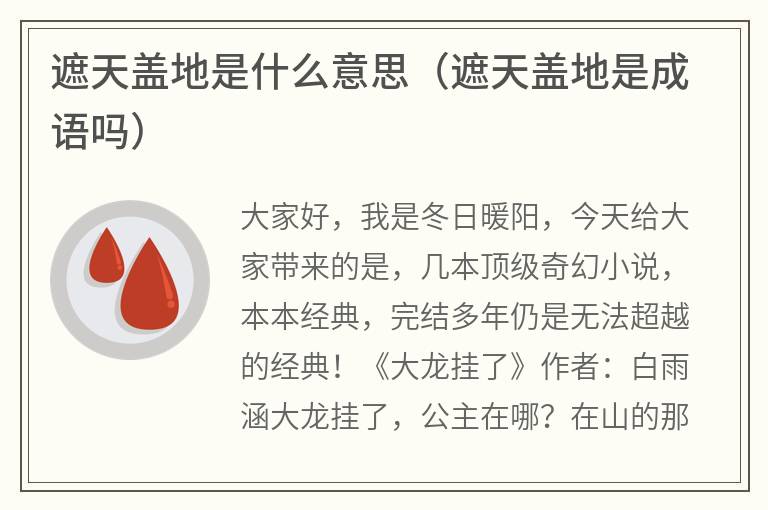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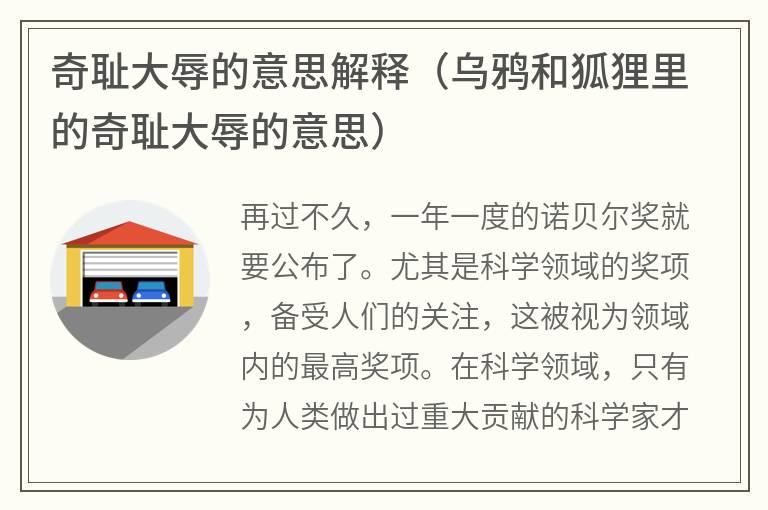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