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坐在观鱼处琢磨《沧浪亭记》的这段版本异文的时候,一位老先生领着一群参加夏令营的小学生来到这里,饶有兴致地为他们讲解这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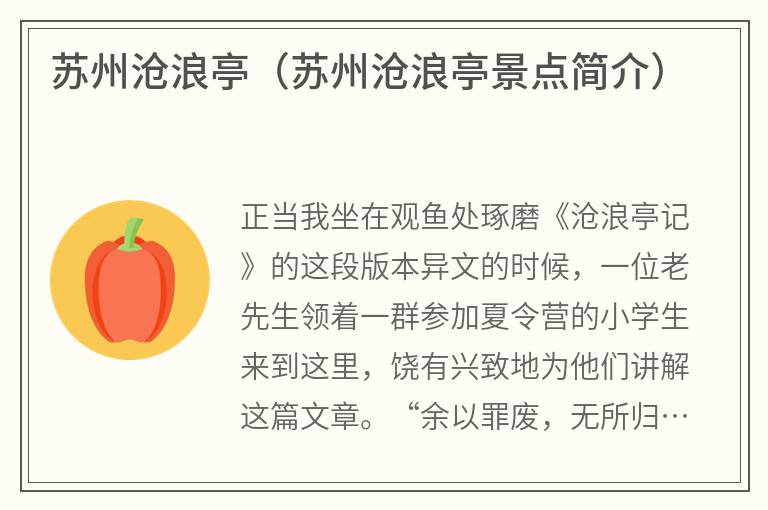
苏州沧浪亭(苏州沧浪亭景点简介)
“余以罪废,无所归……”
“这就是说呢,苏舜卿被罢了官,没有地方可去了……”
“无所归”——当老先生照常例把开篇一句释作无处可去的时候,我隐隐觉得,这个世所公认的解释好像并不稳当:苏舜钦怎么会没有地方可去呢?
“进奏院狱”发生之后,苏舜钦虽然被朝廷革职,宣布永不叙用,但没有任何文献数据显示他曾遭到编管,换句话说苏舜钦的人身自由其实是不受限制的。
想想后来的苏轼,每逢仕途蹉跌之际,总要感叹“万里家在岷峨”,辞官还乡、归老蜀地的念头终始不忘。而苏舜钦本是开封人士,却偏要离乡别井,远涉江湖,旅居于吴中。他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家乡待着呢?这可是苏轼朝思暮想而终不可得的事儿呀!
事实上,苏舜钦迁居苏州的动机不光是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就在事发的当时,苏舜钦的亲友们也看不懂他的决定。比如苏舜钦的内兄弟韩维就曾去信苏州,责备苏舜钦说:
兄弟在京,不以义相就,以尽友悌之道,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
——《答韩持国书》
把手足至亲统统撇下,一个人像条丧家狗似的跑到苏州去,这些烦恼统统都是你苏舜钦自找的!——可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难道是因为北宋京城的消费水平出了名的高,罢官之后,失了经济来源,苏舜钦在开封便待不下去了吗?
我们恐怕还不能轻率地做出这个论断。因为去往苏州之后,苏舜钦在城内的皋桥和苏家巷置了两处宅子,可他嫌这些地方“土居偏狭,不能出气”(《沧浪亭记》),于是又花了四万钱买下沧浪亭以为别业。
苏舜钦在写给韩维的书信中曾亲口承认“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违,而伏腊稍充足,居室稍宽,又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答韩持国书》),吃穿用度都还宽余,“穷困潦倒”四个字无论如何是贴不到苏舜钦身上的。
那苏舜钦为什么来苏州?后来的南宋诗人陆游曾在《家世旧闻》中记述了祖父陆佃和神宗皇帝的一次谈话,其中提到过苏舜钦涉案的“进奏院狱”。陆佃说:
“昔苏舜钦监进奏院,以卖故纸钱置酒召客,坐自盗赃除名。当时言者固以为真犯赃矣,今孰不称其冤?”
——《家世旧闻》
苏舜钦当年犯下的这桩案子本质上是一桩经济案件。起因是逢到进奏院祀神的日子,苏舜钦循着旧例,将所拆奏封的废纸卖了,换来酒钱与同僚诗友招伎饮宴。结果遭到了严厉的参劾,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被“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苏舜钦《与欧阳公书》)。
今天的人们普遍相信,这桩经济案件的背后涉及朝中复杂的党争和政治迫害。苏舜钦是含冤被谤,做了党争的替死鬼。所谓监守自盗云云,只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的内情乃是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政客王拱辰之流为了阻挠新政措施的推行,打击主持新政的宰相杜衍和范仲淹等人,找准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开刀,诬陷他有经济问题,借机好向杜衍身上泼脏水。
可陆佃的话显示,对这件案子的风评,当时与后世大不一样。后来人往往为苏舜钦鸣冤叫屈,可同时之人却多数相信苏舜钦的确是涉嫌经济犯罪的。关于这一点,苏舜钦周围诸多亲友的态度都可以作证。
案发之后,苏舜钦的好朋友蔡襄始终一言不发。耿介刚烈的欧阳修也借故托辞,以自己不在言职为由,刻意避免与本案有所瓜葛。甚至就连岳丈杜衍都不肯站出来为苏舜钦说一句话,以至于苏舜钦在写给欧阳修的书信中抱怨岳父“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与欧阳公书》)。
这些当朝君子、衮衮诸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缄默不言,绝非偶然。
虽说王拱辰等人在“进奏院狱”中参劾苏舜钦,不排除有藉此打击改革派的意图,但苏舜钦的所作所为也绝不是白璧无瑕。是他自己行为不检,授人以柄,而朝廷最终的处罚决定(即“除名勒停”)虽是除死罪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但它毕竟没有超出大宋律法的量刑范围——监守自盗,照刑律是可以论死的。
设使苏舜钦是因为尽忠王事,因公被谤,欧阳修等人自然要站出来为他仗义执言。可现在他犯下的是监守自盗这等最为士大夫所不齿的罪行,似此私德有亏,让有心求情的人还怎么开口说话?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苏舜钦在开封的确是待不下去了。一方面,杜衍等人的沉默让苏舜钦强烈地感受到了亲友的“背叛”;另一方面,那些为他所邀,参与进奏院召伎饮宴的同僚诗友还有十多位受到牵连而遭贬谪。
这样两下夹击,苏舜钦恐怕颇有点儿“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窘迫。为了摆脱困境,他只好离开京城,远避吴中。但即便如此,监守自盗的罪名,苏舜钦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下来的,那样一来,他将彻底身败名裂。
为了挽回自己的清誉,苏舜钦只好一再给亲友们去信鸣冤,辩称自己是因为朝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而遭到了无辜的迫害:
始者,御史府与杜少师、范南阳有语言之隙,其势相轧,内不自平,遂煽造诡说,上惑天听。
——《上集贤文相书》
声称自己做了党争的牺牲品和殉道士,甚至筑亭苏州,勒名“沧浪”,隐然以遭受迫害,含冤放逐的屈原自比,苏舜钦的这些公关言论正是后世人们认定“进奏院狱”为冤案的源头。可是我们一旦轻信了这种经过人为改动的历史叙述,也就再没法探知苏舜钦远游吴中的真实动机了。
“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无论苏舜钦引导世人风评的努力是否成功,接下来的这个问题都是他必须要严肃对待,认真思考的:虽然在我们今天的印象里,苏舜钦是一个诗、文兼擅的大作家,但活过半生的他其实并没有想过靠着书立说,因言不朽。
他的志趣与抱负一直都是出将入相而非著作等身。可是朝廷在“进奏院狱”后给他的处罚是除名勒停,这意味着苏舜钦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垂于不朽的通道已经被彻底堵死。如果到这个时候,他还抱定从前的理想而不肯撒手,那最后的结局恐怕就只好效法屈原,沉江自尽了。
“余以罪废,无所归”——这个“归”并不仅仅是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更是要在废毁往业之后寻觅新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
而最终的结果呢,至少在这篇《沧浪亭记》当中,苏舜钦宣称他成功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从固执于仕途的泥淖中拔了出来,甚至还颇带着几分优越感地怜悯起过往那些至死不悟的才哲君子来——苏舜钦含糊其辞的反面典型中说不定还包括了自投汨罗的屈原呢——立功之想已成前尘往事,而另一个德行高妙的抱道君子却在《沧浪亭记》当中重生,恐怕这,才是苏舜钦敢于宣称“自用是以为胜焉”的真正原因吧。
—THEEND—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原创&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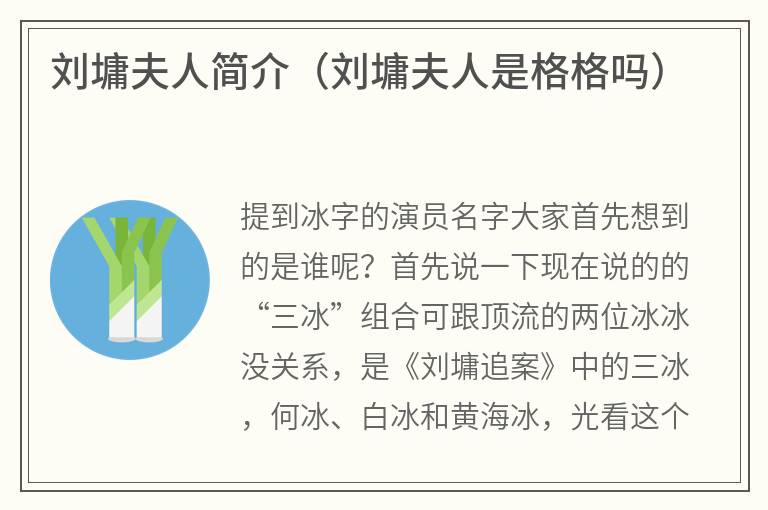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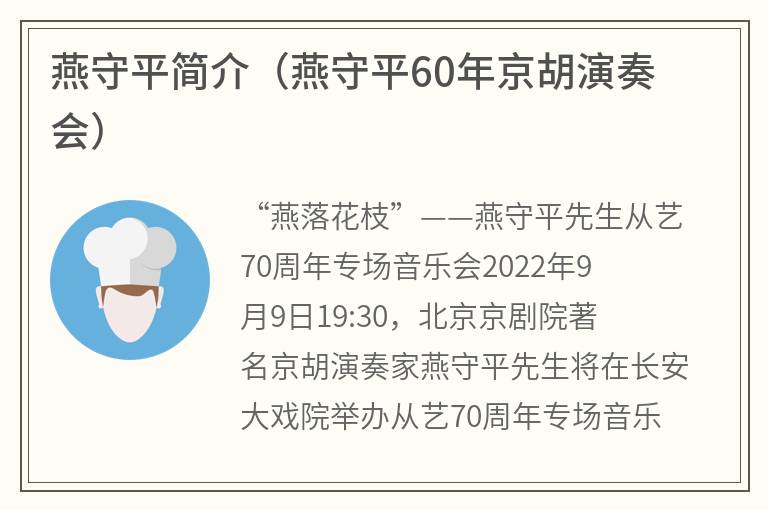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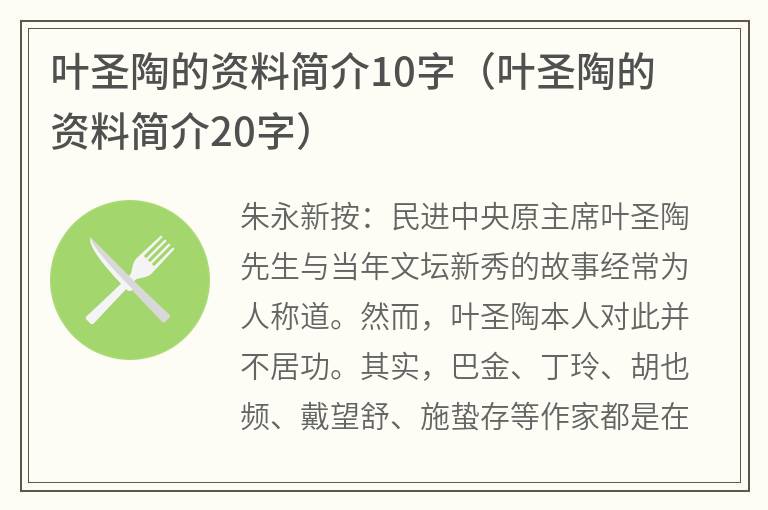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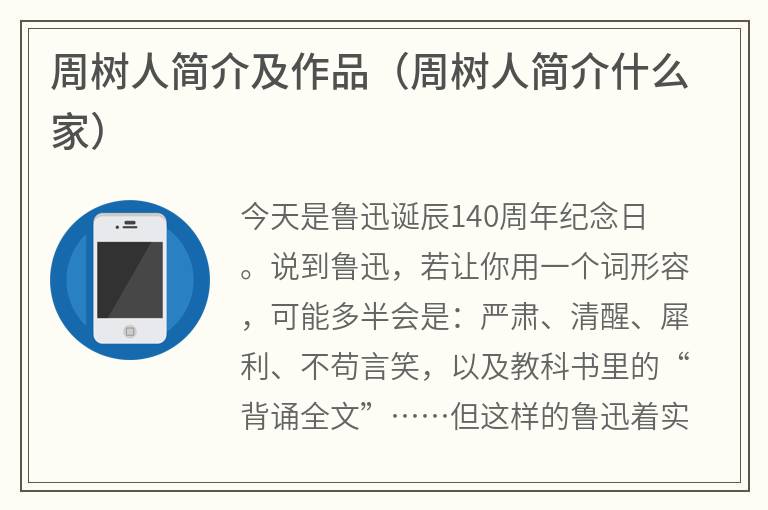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