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革命,清室覆亡起,如何叙述和理解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就成为一个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场域,清史记忆亦随之呈现出各异的形态。王钟翰先生曾谓:“民初以来,清史研究就是历史学科出现的新趋向。这与其说是受历朝都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之影响,毋宁说是辛亥革命以来排满思潮在学术上的反映,以及清朝统治的‘僵尸’依然存在并有外国侵略势力企图借尸还魂这一严重对学术界产生的一种刺激。”此段文字虽短,但道出了民国初年清史为各方所瞩目的几点缘由:其一是辛亥革命前后排满革命思潮而引起的明清易代之际历史的复活;其二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引起革命党一方试图通过揭清之失而进一步瓦解清代复辟的可能性;其三是清遗民一方试图通过修史以报故国,寄托黍离之悲。另外,日本人对清史的关注和为其侵略中国服务的学术文化活动亦刺激了学人关注清史。
民国时期北京政府主导修撰刊行而最终被国民政府查禁的《清史稿》,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由官方所主导的传统纪传体“正史”,其修撰过程即后来的命运所关涉的问题极多。因为政治文化的转型,传统“正史”的命运亦如同许多传统时代的许多经典一样逐渐被边缘化,梁启超在晚清曾说:“于今泰西同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其立论的目标在于将中国旧史进行彻底地改造,在这个改造中,“创造性转化”与“消耗性转化”皆不可避免。罗志田曾将这一时期概括为“经典淡出的时代”,并指出:“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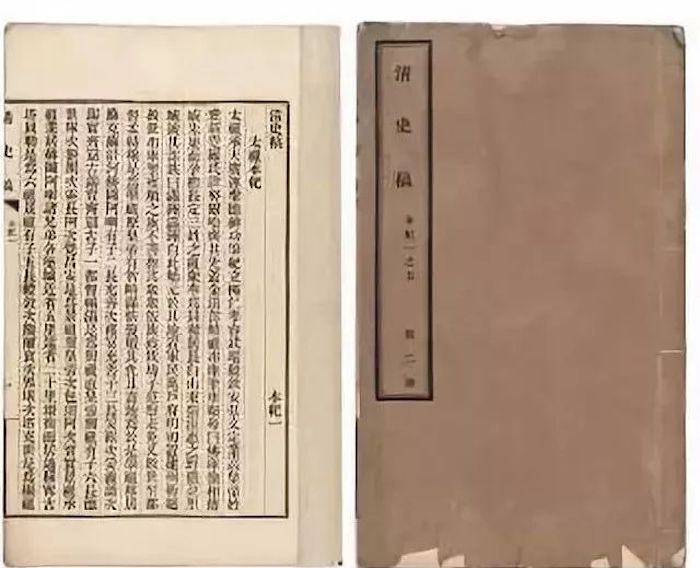
清史稿
民国初年有关清代历史的其他文本如稗官野史、掌故笔记、演义小说、戏曲与电影(稍晚出现)剧本、历史教科书等等也纷纷出涌现,一时间“人人喜谈清代掌故”。清代历史记忆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态势。
稍稍检视当时报章之上刊登的书籍与戏曲广告,即可看出当时确实出现了一股“清史热”。当时报章上各类广告文字侧重有所不同,有些广告词意在强调其作品近于历史本相,譬如1913年9月《申报》上小说《清史演义》的广告便谓:“是书系青浦陆士谔先生手笔,笔墨犀利,论断精确,叙事详明,将有清十二朝武功文德、国政朝章以及宫闱秘闻、朝野奇事悉载靡遗,诚小说界空前之杰构”,一年之后的1914年11月,此则《清史演义》的广告仍然在《申报》上持续刊登,似乎销路颇好,其文曰:“本书初、二、三集出版仅只一载,销数已达万部。日本文豪日下峰太郎要求译为日文,经著作人陆士谔君允许,现已译等《台湾日日新闻》,风行彼邦,自行新小说以来,价值之巨,得未曾有。”广告中还借日本人之口而自抬身价,其真实性虽值得探究,但能在前后一年有余的时间中持续刊登广告,似乎说明销售此书收益不少,能支付一笔不菲的广告费用。
而在此前后,《申报》甚至在同一天在同一版面便登出两条有关清代历史小说笔记的广告:其一为《清季野史》,略谓:“此书分初、二、三编,内容三十余种,悉出一时名人手笔,于清季掌故搜辑极广,其中如纪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庚子之乱等作皆极可贵,又庆王外传、清代割地谈等或译自欧文或参考西籍而成。尤为难得,作清史参考书可读,作小说读亦无不可。”强调此丛书兼具小说的趣味与史事的精确性;另一条则宣传的是一套“满清稗史”:“订正再版满清稗史(内容十八种)《满清兴亡史》、《满清外史》、《贪官污吏传》、《奴才小史》、《中国革命日记》、《各省独立史别裁》、《当代名人事略》、《十杰记实》、《南北春秋》、《戊壬录》、《新燕语》、《变异录》、《三江笔记》、《所文录》、《湘汉百事》、《清末实录》、《暗杀史》、《清华集》。本书出版以来,荷蒙各界欢迎,出版现已售罄,复经著者将内容详加校订,再版印行,仍附铜版图画,装订十八册。”从上述书名看,其中内容大多未必可信,然标题耸动,炫人耳目,可能在民间社会行之颇广。尽管内中所言“初版售罄”云云,可能是出版商自夸之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书籍虽多系辗转抄撮并加以想象附会而成,但受众反比严正之作可能更广,故其中的内容和态度亦参与形塑了人们心目中的清代历史记忆。

陆士谔
书籍尚需识文断字者方能阅读,在当日底层社会仍有许多不识之无者,故书籍流传的广度尚相对有限。而戏曲等艺术,因其借助形象、声音为媒介,则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亦往往能欣赏,故在很多时候比小说流布范围更广,戏曲之中的故事,往往妇孺皆知,又能通过口耳相传,故传统中国社会之中,民间的历史知识与历史意识,有许多是来自历史题材的戏曲之中。清代覆亡之后,以清史为题材的戏曲亦很快便被推上舞台,当日报章上亦为之大作广告。如一则为《满清三百年始末记》戏曲宣传的广告便称:
演新戏无非把往事新朝重提起,现身舞台,俾观者鉴古知今,得资阅历。如演社会戏,则悲欢离合、赏善罚恶;如演历史戏,则有兴亡废立,旌忠惩奸,启发人之智识,警惕人之观感。本社开幕以来,一载于兹,所演之戏,均从有益于社会着想,备蒙观客称许,而乾隆下江南一剧,极为各界欢迎。然是剧于满清历史,仅如凤毛麟角。故本社搜集清室三百年之往事,或内府秘纪,或故老传言,自顺治称帝始至宣统退位终,其中兴废存亡、忠正贪邪、淫盗奸宄,色色俱备,尤以顺治得位之易、康熙秉政之明、雍正换子之奇、乾隆游佚之侈、宣统失政之速,天道循环,颇堪寻味。至若演员之高尚,布景之完全,早以有口皆碑,毋庸自诩,准于初七晚开演。有新剧癖者,曷来一观此绝无仅有之历史好戏,胜读一部清史也。
观其广告词中所言,戏中所谓历史事实多系荒诞不经之传说,譬如“雍正换子”、“乾隆游佚”之失等等,恐怕史实的成分少,而传说附会的成分多,但这并不妨碍民众喜闻乐见,而此戏在当时似乎也演得热火朝天。《申报》上第二天的广告继续刊登《满清三百年始末记》的广告,登出当晚演出的具体内容是“顺治帝入关称尊,吴三桂恋色卖国”并配合演出内容撰写口语化的广告词,用上海当地的吴方言戏仿观众的口吻,令人读后忍俊不禁:
哈哈,今朝好天气,到啥场化去白相呢?想着哉,三洋泾桥民兴社,今夜做头二本满清满清始末记,我到要去看看,顺治进中原格事体接连看完仔,赛过一部清朝史记哉,让我打电话去定好位子,铃铃铃,三千一百三十号,喂,啥人?阿是民兴社?是格。今晚三百年满清始末记那哼做法格?就从清太宗称尊,兴兵攻打中国演起,当时李闯做乱,做了皇帝,霸占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三桂重色忘国,借兵攻打李闯,及至歼除闯贼,得回陈圆圆,就轻轻把大明江山送掉,请顺治帝登基。剧中有鞑子做皇帝、皇叔偷皇嫂,并有浙江上虞县的故事,孀妇做皇妃,奇奇怪怪,大有可观,新添特别布景:行营宝帐、金殿皇宫、大炮坚城、华堂曲室、夜月狂风、御园梦景,形形色色,无不应有尽有的。
这段方言口语,直把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写得如同江南吴地的家长里短一般。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自然会因为其中的亲切感而喜闻乐见,但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就恐怕不那么接受其中颇不雅驯的言辞。更不用说其中所谓“鞑子皇帝”、“皇叔偷皇嫂”等用语,会让看到这类文字心念故国旧君的清遗民十分不满,在自己的文字中怒斥之。
清季曾在国史馆任职多年,在当时颇以史学之才、学、识三长自负的恽毓鼎,辛亥革命之后遁迹都门,以清遗民自居,便对当时从出的清代稗官野史多有不满。他在民国初年曾在读了新出的《清代野记》之后评论:“近世南人,不满意于清室帝后,已成一种流行性,此从古未有之变态。盖一代之亡,学士大夫作为笔记,追述先朝故事,多寓忠爱之忱,独近世不然,故余于此类纪载,不乐寓目,以其本源先不正也。”事实上,他并非“不乐寓目”,而是相当喜欢看民初出现的谈清史的作品,只不过看了之后多加以批评,有时颇为赞赏,因为作品立场与其相近,有时便显得迂阔。1912年9月,恽毓鼎记载:“饭后鹤群来,剧谈新作《清演义》,已十余回,大意发扬武功,以作国民之气。与《三国演义》相近,而故朝掌故,借以流传。小说家言,其风行之力反过正史也。鹤群甚踌躇于孝庄文皇后宫闱之事。此事故老言之凿凿,而下笔为难,唯有于无字处书之,使读者慧心领取耳(《红楼梦》可法也)。”此处体现恽毓鼎与友人回护清廷的用心,以至于故老相传的宫闱秘闻使得他们“下笔为难”,最终却决定使用小说家的笔法,“于无字处书之”,而非详细考订而辨别此事原委,亦可体现出恽毓鼎的史学观念。1914年8月,恽毓鼎从农会(借书处在农会亦有意思)借得《清外史》读后则评论说:“今日粗阅一过,其事之偏僻实不必论,且以义例言之,凡后代人为前朝修史,所修者某朝,即以某朝为主人翁,如梁、陈、齐、周四史,皆出唐人手,而客主各不同,称其君曰天子,曰上,曰朝廷;称他国曰入寇,曰陷。内其国而外他国,义例当然也。故不以所修之朝为胜朝,而以所修之前一朝为胜朝。又如清朝人作一书叙明朝事情,必称之曰太祖、成祖、庄烈帝,决不段段加明字,曰明太祖、明成祖、明庄烈帝,且直斥曰元璋、棣、由榔(笔者按:崇祯帝名朱由检,此处恽毓鼎记忆有误)也。今观《清外史》于列圣庙号上皆标一清字,甚至直呼帝名,而满朝、满帝、清廷等字满纸,可议处必丑诋不遗余力,而善处则一字不书,其不公平如此!若使此种人执笔而修清史,则是非倒置不堪问矣。呜呼!史事岂可轻畀耶!”

恽毓鼎像
1916年孟森针对当时清代野史从出的的现象曾说:
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谈故事者乐数清代事实。又以清世文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甚于焚书坑儒之祸,弛禁以后,其反动之力遂成无数不经污蔑之谈。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不欲随波逐流,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辨正,偶举一事,不惮罗列旧说,稍稍详其原委,非敢务博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耳。
孟森秉持的严正的史家立场,对于荒诞不经以污蔑清代为能的传说,自然不能容忍,他自陈持此态度乃是史学家的自我认同使然:“其为保护清室之意少,而为维持史学之意多。故虽不信官书,亦不听世俗之传说,尤不敢盲从(辛亥)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种族之私,而冀耸流俗好奇之听。”他认为官书与私人记载皆有所偏颇,故“清史一科,固以纠正清代官书之讳饰,但亦非以摘发清世所讳为本意”。但稗官野史中宫闱传说的流布,亦体现出当时清代历史记忆的多元与混杂,秦燕春曾指出民国中期:“清代之史(特别是明末清初之史)在经过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带有‘有色眼镜’的反复戏说之后,其泥沙俱下、珠玉杂陈的局面相当严重,可以说将其回归历史本来面目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某种意义上而言,清史记忆所呈现的正是不同人物、不同群体对于当下以及未来中国的不同看法。历史记忆本与当下得处境息息相关,故亦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产生出前所未有或者早为人遗忘的一些面向。关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区别,法国史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曾说:
记忆和历史远不是同义语,我们应注意到,一切都让它们处于对立状态。记忆是鲜活的,总有现实的群体来承载记忆,正因为如此,它始终处于演变之中,服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则,对自身连续不断的变形没有意识,容易受到各种利用和操纵,时而长期蛰伏。时而瞬间复活。历史一直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可疑的、不完整的重构。记忆总是当下的现象,是与永恒的现在之间的真实联系;历史则是对过去的再现。记忆具有奇妙的情感色彩,它只与那些能强化它的细节相容;记忆的营养源是朦胧、混杂、笼统、游移、个别或象征性的回忆,它容易受各种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动,它要求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记忆把回忆(souvenir)放置在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它驱赶下来,它总是让一切都回归平凡。默不作声的记忆来自跟它紧密相连的群体,或者按哈布瓦赫的说法,有多少个群体就有多少种记忆;从本质上说,记忆既不断繁衍又不断删减,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相反,历史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这就使得它具有某种普世理想。记忆根植于具象之中,如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历史关注的只有时间之流、事物的演变及相互关系。记忆是绝对和纯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
上述引文揭橥了记忆的流动与多歧,且从属于不同群体,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虽然概括自法国的历史经验,但揆诸中国历史,亦若合符节。具体到清代历史记忆而言,一方面,清代覆灭之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被新的共和体制所取代,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虽然辛亥革命在后来的叙述中常被认为“不彻底”。事实上,辛亥革命的影响甚为深远,绝非仅及于政治制度层面,近来的研究逐渐揭橥辛亥革命在社会心理、文化等层面所引起的巨变。辛亥革命类似于吹及各个层面的一阵飓风,所过之处,事物的形状皆因之形变,原有的秩序与位置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孟森
有论者指出的:“共和取代帝制的转变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那次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其相关的转变在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近代四川学者刘咸炘曾经论述史学的功能在于“察势观风”进而“知人论世”,这一取向在当时并未引起多数人的注意,而近年来始开始被重视。历史现象本有“实事”与“虚风”的不同层面,辛亥革命之后清史记忆,本近于“虚风”一面,然并非不重要,且其影响常常在潜移默化之中决定历史中的人物的行事方式。王汎森曾以风为喻,指出历史的进程:“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像毛细管作用般,在最微细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民国初年,时人在论述思想史、学术史乃至词选等议题时,常常冠以“近三百年”的前缀,实际上“近三百年”就是清朝统治时期,论者故意不用“清朝”或“清代”,背后多少含有“去清朝化”的心态,体现出作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立场。此种隐微之处的表现,便可谓历史上的“虚风”,虽是细节,但足以提示许多“实事”所未必能说明的问题。诚如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所言:“人是处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任何“物质性”的行为背后,实际上也遵循着由人所提供的“意义”路径。1925年章太炎在给弟子吴承仕的信中曾论及清遗民敌视民国的态度,有些并不一定有许多动作,但“泄杳之风,由来已久⋯背诞之言,时时形于文字。”这可能就是“风”的一种体现,许多象征性符号并不需要太多动作,而使用者与心目中的接收方就自然心领神会,然而究其实际,又没有太多的实“迹”。故章太炎对当局“法吏不问”清遗民的活动,十分恼火,故“于黄陂再起时,曾劝其捕治溥仪,以完复辟之罪。”章太炎的主张似乎是以心理而非行为来给溥仪及其周围的清遗民定罪,近于“捕风”,虽然看似不近情理,然若用之于探索时人的心迹,则很可能比有形的活动更能接近真相。又,许多清遗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投效于伪满洲国的行为,在受现代民族主义影响下得人看来,无疑是“汉奸”叛国的行为,然在当事人的内心,则可能有以“民国乃敌国也”,心存依托伪满洲国为清室复辟的想法,尽管在此口号背后,仍不免有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之处。
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原,定鼎两百余年,超越前代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如辽、金、元等,其历史本身与汉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有着不尽相同的一些特征。王钟翰曾说:“清代官制,虽云‘大半沿前明数百年旧制’,然细究之,两代官制多名同实异”,“名同实异”一语实能把握明清易代的变化所在,但论者往往不察,认为清代与前代中原王朝无异。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最早使用“征服王朝”一词,将辽、金、元、清,皆归入其中。事实上,清代制度与文化既有继承自前代汉人王朝及游牧民族所建政权之处,又自有损益,形成新的格局。这些特征自辛亥革命前后便引起时人的注意,而当时倡导排满的革命党人通过重新发掘明清鼎革之际的文献,以自西方假手日本传入的民族主义为思想资源,从这些发掘出的旧文献中读出新意,复活明清之际被清廷刻意压抑的历史记忆,用以宣传满汉之别和革命的必要。朱希祖1931年在为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作序时写道:“余自二十五年前游学日本,初留意于晚明史籍,其时二三师友,亦尝弘奖斯风。余杭章先生首先传刻张煌言《苍水集》、张斐《莽苍园文余》⋯⋯其时东京、上海,声气相应;顺德邓氏,乃大肆搜辑,野史遗闻,遐迩荟集。断简零篇,邮之以学报,鸿文巨册,汇之以丛编⋯⋯盖读此等书者,皆有故国河山之感,故能不数年间,光复旧物,弘我新猷。回顾顺、康、雍、乾诸朝,出其暴戾雄鸷之力,以从事于摧毁禁毁者,方知其非无故也。”

朱希祖
翻阅时人的日记、信札以及事后的回忆文字,会发现成长于清末的反清革命者,率多受到过这批复出的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记录的影响,有些人甚至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得了与清代官方不同的历史记忆,而这种早年的记忆,影响甚为深远。
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的记载,他回忆幼年时在无锡荡口镇的小学里,他从自己的体操老师哪里得知了“我们的皇帝是外国人”的信息,相当震惊,开始有了朦胧的反清意识。他随后又在老师的启发下,认识到中国历史一治一乱,而西方则是“兴了便不再衰,治了便不再乱”的规律,从此立志要研究中国历史,探寻中西历史之间的异同。而蒋复璁后来则回忆清季杭州的小学堂中,学生对清廷有所不满,便在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上作些涂改:“当时历史课本之中,关于清代的历史还称国朝,也会空格或抬头,但是我们同学不约而同地都把‘国’字改去,好一点的改称‘本朝’,有的竟改为‘清朝’,小学生都如此,更大的学生更不必说了。”
民国成立,排满革命虽已无标的,但孙中山在清帝退位之后,即在南京祭明孝陵,此举极具象征意味,将自身倡导的革命与朱元璋及明代历史记忆联系起来,构建一个汉人民族革命的连贯谱系,此一革命谱系在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仍然发挥着作用,在国民党一方的官方历史叙述中,清代始终是压迫汉人的一个异族反动政权。刘小萌教授曾经说:“在清朝灭亡以后,中华民国(笔者按:此处应主要指国民党一方)的史学叙事基本是对满族统治完全否定,代表作就是萧一山三大本的煌煌巨著《清代通史》,他把清代纳入近代史,讲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就是民族革命”。然袁世凯代孙中山出任大总统之后,北洋政府中多前清旧人,袁世凯设立清史馆,网罗学者文士修清史内清廷而外民国,引起革命党一方的不满,自修史起始阶段,便多有不同的议论,甚至讥评,种种报道频现报章,修史在民国初年纷扰的政局中,虽为不急之务,然而引起的关注似并不少,此现象亦间接说明“修史”这一行为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传统虽然呈断裂之态势,然其与现代实际上又藕断丝连。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