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多年前,就历史剧创作中“史”与“剧”的关系问题,我在《剧本》月刊(1995.8月号)发表了《摭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一文。文章开宗明义提出“戏剧本体”涵容“历史”,历史真实最终必定消融、沉潜于戏剧本体中而经由艺术真实体现出来;并辅以四个子题加以阐述,其分别为“驰骋想象,把结论性的历史真实转化为‘过程性’的艺术真实”、“探幽烛微,把外显性的历史真实转化为内在性的艺术真实”、“传奇传神,把事件性的历史真实转化为情节性的艺术真实”、“活灵活现,把抽象性的历史真实转化为形象性的艺术真实”。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更难得的是得到了许多实践工作者的认同。十多年过去了,时代生活乃至进程中的戏剧状态都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而关于历史剧中“真实”问题的讨论却迄未止息。当年“摭谈”,是拾取别人的话题来借题发挥;今日“再谈”,是想补充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我把近年来的思考主要归纳为下面三点。
一、历史剧创作要确立“戏剧本体”的地位
席勒在比较小说等叙述类艺术与戏剧的特征时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一切叙述的体裁使眼前的事情成为往事,一切戏剧的体裁又使往事成为现在的事情”。这句话可谓不期而然却又恰切地道出了戏剧的“本体”性质,更道出了历史剧的“当下”性质,即戏剧总是某种行动着的“当下”的展开与呈现。尽管戏剧有着一整套复杂的艺术系统,但无论是作为“类”的戏剧艺术,还是单个的戏剧剧目,其本性都是在两个小时左右的舞台艺术时空中凝结为一种“本体”状态亦即李泽厚先生所言的“最终实在”。而历史剧的“往事”,何以能“成为现在的事情”和“眼前发生的事情”,盖因戏剧的本体性质使然!也正是戏剧的这种“当下”性,使观众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使观众乐在其中地观赏“眼前发生”的历史“往事”,也使观众的审美接受表现为即时审美、当堂反馈、潜移默化、长期受用等特点。
我们通常说中国老百姓,过去大多是从历史剧目或“老戏”中获得一些历史知识的。但这种获得不是自觉地刻意求之。观众走进剧场,是“看戏”、“听戏”,是要获得一些“形式美”的满足,是怀着一种(审美)期待去为即将呈现在眼前的剧情和人物,洒一掬同情之泪或为之解颐开怀……因而,唐文标先生在分析了中国古剧中的道德因素后认定“道德剧”就是“娱乐剧”。“娱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悲剧或喜剧所带来的不同的审美。因此,无论是历史知识,还是道德教化,最终还得附着在戏剧本体之中,蕴含于戏剧予观众带来的当下的审美之中。
同样,无论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如何定义,如“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是探究确定年代的事件”、“历史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尽管说法不一,各有侧重,但这些有关“历史”的思考元素以及历史的“本事”、“往事”,都可以“为我所用”而真实地归化于戏剧本体之中。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历史”与历史剧确实存在着一种“异质同构”的联系。历史是“人”的历史,无论是以帝王精英及其“大事件”为主导的所谓“大历史”,还是以小人物、日常生活、边缘事件为主导的所谓“小历史”,都是人的实践活动推演出的事件、事变、事态,进而创造出的“事实”历史(亦即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也正是古往今来真实存在过的无数个体生命以及他们的灵性、才情、机心乃至权术等等,演绎了历史的波澜壮阔甚或波谲云诡。而戏剧,恰恰是为历史的人,提供了“真实”活动的“现时”舞台。“命运的必然性――时间的逻辑,这是一件最具有深刻的内在确定性事实,这一事实充塞在整个神话式的宗教和艺术思想中,构成了全部历史的本质和核心。”历史学家所说“命运的必然性”(或是偶然中的必然)、“时间的逻辑”,也都是历史剧所借以建构戏剧本体的客观法则,在这里,历史与历史剧形成同构关系;同样,不管“历史”的定义如何繁复多样,但却逃不出“实际上的过去”与“历史学上的过去”这两种基本形态。前者具有客观实在性,是本然的历史;后者虽力求客观真实,但因个人的关切渗入其间而难免打上主观的印记,因为,历史学家的“历史”总表现为对“往昔的叙述和借此得出建构叙述的研究方法”这一点上。艺术家也和史学家一样借此建构自己的表现方法,也和历史学家一样关注故事。但不同的是,史学家是“讲”故事而述以往,历史剧是“演”故事于当下;“历史”只陈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剧则基于历史的本质(命运的必然性、时间的逻辑)富于想象力地陈述已然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的目的在于追求史事(包括意义)的真实性,而历史剧在假定性的前提下则尽可能地追求历史形象的真实性以及假定的真实性;“历史”事实上重点关注着“大历史”,而历史剧总是能将“大、小历史”冶于一炉来加以呈现;“历史”,更多瞩目于“事件”及其成因、背景,历史剧则既青睐于“事件”,更充满着对事件背后的“历史心灵”的叩问和剖现,典型的例子如《屈原》中的“雷电颂”以及戏曲历史剧中一些习见的核心唱段。
从以上简要的分析比较中,不难看出,“历史”与“戏剧”在“人”的问题上,在“命运的必然性”和“时间的逻辑”上同构而契合。但“戏剧中人”比“历史的人”更丰富、更复杂、更生动,也更直观;不论历史剧与历史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又使二者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本体”形态。而在以“历史”为表现或反映对象的历史剧中,“戏剧本体”无疑将“历史本体”包容其间,也正是在这里,“戏剧本体”高于了“历史本体”。
我们高兴地看到,李泽厚先生在其近著《历史本体论》中对“历史本体”作出了这样的界说:“所谓‘历史本体’,并不是某种抽象物体,不是理式、观念、绝对精神、意识形态等等,它只是每个‘活生生’的人(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但这‘活生生’的个体的人总是出生、生活、生存在一定时空条件人的群体之中,总是‘活在世上’,‘与他人同在’。由此涉及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我活着’,‘我意识我活着’。整个‘历史本体论’就归宿在这里。”这一界定,无疑为“戏剧本体”打开自己的“天地境界”或曰审美境界,提供了来自“历史本体”的有力声援!然而,李先生对“历史本体”直切本质的真实把握,在当下的历史研究中尚属一种理想状态。而他所呼唤的“历史本体”得以归宿的“天地境界”,及境界中的“命运偶然性、个体特异性、人的有限性、过失性和对它们的超越”,恰恰能在历史剧之“戏剧本体”中得以真实体现和“充分绽出”!由此,我们在确定了历史剧之“戏剧本体”地位后,就可以切入历史剧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了。
二、“历史真实”应服膺于“艺术真实”的建构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长期纠葛与博弈,被有的论者认定为“循环论证”,若确定二者是对等关系,则此论不无道理。但如前所述,历史剧中的“戏剧本体”对“历史本体”是一种吸纳式的包容关系而非对等关系( 在“剧”中的不对等)。“剧”较之“史”,“剧”是涵盖并重构“历史”的主体。同理,历史真实只有经由艺术真实的整体形态体现出来。历史的真实,只是为艺术真实的建构提供“真实”的可供剪裁、提炼的创造依据。这两种“真实”,位阶不同,因而不存在所谓“循环论证”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把历史剧中的历史真实混同于艺术真实或把历史真实视为高于艺术真实的事却时有发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竟被有的史家挑出了近百处有悖“史实”的“错误”。历史体裁的创作者们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一顶有违历史真实或“反历史”的帽子,令人莫可适从。目前历史学界的确有一种将历史“细碎化”、“碎片化”的倾向,如考证出“李白先后结了四次婚”、“孔子的身高2、21米。与姚明几乎一般高”等等。如按照这些所谓的“历史真实”去要求并对照历史剧的创作,则扮演孔子的人非姚明莫属了,而扮演《法门众生相》中的太监刘瑾则断断不能由“花脸”行当来演了!殊不知,作为已被观众接纳的艺术形象,观众并不会去关心或追究人物的身高多少、声音是否“娘娘腔”这样一些琐碎的外在“真实”,这即使作为一种“历史常识”,在一种艺术氛围中,观众也是无意或无兴趣去接受的。相反,观众会从中不自觉地感受到一种更本质的真实,如孔子的“仁”、刘谨的“奸”及其绽出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田汉先生在创作《关汉卿》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历史资料,依据的只是关氏的十几部作品及其他零散材料。但由于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深度把握、对历史本质的深刻领悟以及对历史人物的深切关怀,并据此来营构自己的艺术真实,从而尽可能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即便如此,也有人指出《关汉卿》一剧的失“真“之处,指责其在元代人物身上使用了“吸烟”细节,而烟草“是明万历年间才从海外传入我国的”。对此,我觉得仍要从全剧的整体面貌来作判断――“吸烟”细节前置的人物对白是“不知哪一年能过上太平日子啊!真有点累不起了,在这里抽一袋烟再走吧……”作者要反映的历史真实,并不在于“吸烟”或那一年代是否已有了“烟草”,而在于反映底层民众面对天灾人祸生出的对太平年景的祈盼!一句“真有点累不起来了”,既是对所处时代的不堪重负,也是具体情境中人物的疲乏之态,于是“吸烟”抑或是“喝茶”什么的,便成为“无奈中透一口气”的真实写照,是人物情态“对象化”了的真实!在这里,观众显然不会或不屑于关注“烟草是何时传入”这样碎片的真实,而是经由作者建构的艺术真实来感受一种历史氛围的整体真实。当然,一般情况下不必违背“历史常识”,但若是为了更高的艺术真实,完全可以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失事求似”,失细枝末叶之“事”,求形神兼备之“似”,来达致表现历史本质的艺术真实,成功者如《关汉卿》这样的不朽名篇是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戏剧之外的作品例子来加以佐证。前苏联画家苏里科夫的名画《近卫兵临刑的早晨》,如果按历史事件(行刑)发生的真实地点,是黑沼地而非红场,画家对这一“历史真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他甘冒被史家指责的风险,把行刑地点移到了红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更有张力地反映俄国社会尖锐而紧张的时刻,两种不可调和力量的冲突。“红场上的‘布景’帮助画家更深刻地揭示出人民与国家的执政者在彼得大帝时代复杂的形势下的矛盾。画家离开了具体的事实……然而,他不仅没有离开艺术的真实,而且形象地表现了历史事件的确切含义。”这是真正的历史理性在艺术中的真实体现!在这里,艺术的真实,蕴含并更有力度地表现了历史的本质真实。但若拿某些人的历史“望远镜”来看,则明显违背了历史事实而失“真”;若换一架科学的“显微镜”来看,则不过是无数“真实”的色斑而已。的确,一些非艺术的“深入观察”与较“真”,正在葬送审美的感觉,正在消解艺术真实赖以生存的审美品格。而“牛顿的彩虹和诗人的彩虹”完全是两种不同观察方法的产物。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我们不能被有违艺术规律的东西,以其条条框框来“剪断天使的双翼”、“征服所有的神秘”、“拆散了彩虹”!
此外,在历史剧的“真实”问题上,在历史体裁的创作中,通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诘难,如“在古人身上赋予了现代人的思想、行为、语言”而违背了历史真实。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管仲是齐国名相,在“朕即天下”(管仲所处时代帝王尚未用“朕”之称谓,在此只是借代使用)的封建王权统治下,他却把“君”与“国”分得很清,不肯“殉君”是因要“报国”,忠“国”而不忠“君”,这是古代人的思想?我看比现代人还“现代”!“行为”是人的行为,作为“类”的人完全可以推己及人包括推及古人,并在特定情境中“行为”之;“语言”现代与否,中国古典戏曲的丑角艺术,早已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剧情的需要,“丑”行跳进跳出,说出很“现代”甚至时尚的语言,恐也无可厚非。其产生的“间离效果”,反而能让观众从其切中本质的“代言”中获得和真实感。张庚先生在《古为今用――历史剧的灵魂》一文中,曾比较了取自同一历史题材的《三关摆宴》和《四郎探母》,两个剧目,写作年代不同,作者的思想倾向也不同,前者表现了国破家亡时的悲情大义;后者则弥漫着甘于被奴役的卑琐之情。这两种应时而作的写法,并没有视为“反历史”。我反倒认为,因其不同的艺术真实的表达,倒是更本质地传递出原题材所蕴含的历史丰富性以及不同写作年代的历史真实。我想,这或许是这两个剧目至今仍在搬演的一个内在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历史剧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既有联系,又有质的区别。历史真实是一种确定的真实,即确有其人、实有其事,而艺术真实是一种模糊状态的真实,即“失事求似”、“离形得似”,是难以直接类比、需要意会通观的真实;历史真实是一种已然的真实,艺术真实则是一种可能状态的真实,是以有限的艺术时空创造无限可能性的天地人生境界的真实;历史真实是一种力求客观的真实,艺术真实则是具有主观规定性的真实,即更接近人本身的经验性真实,并以此照亮处于历史“幽暗之地”的心灵的真实;历史真实也常常表现为单一的真实,如评价某剧中某一点是否真实,而艺术真实则是一种浑成状态的真实,是吸收各种养分特别是历史的滋养而整体生发出的真实。因此,历史剧中的艺术真实是一种自体性的真实,它以一种开放的动势,咀含、吸纳确定的已然的客观的历史真实,并以此审美地把握历史本体来构筑自己的真实世界。
三、通达艺术真实的审美途径
如前所述,历史真实是一种客观、已然的存在;而在历史剧的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艺术真实,较之前者是一种事后的存在,它要依赖艺术家的主体创造来加以构建和浑成;而这种主体创造,既离不开对象化的历史真实,更离不开有效的审美途径,否则就真的会失“真”,或只见历史之真而无艺术之真,或两种真实皆失。我以为,要审美地构筑历史剧的艺术真实,主要依赖于以下几种相辅相成的构造方式:
1.努力营造真实的历史戏剧情境
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中早已引入了“情境”理论,如历史生态学中的“情境”方法,考古学中的“评论的情境”等,意在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或器物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历史剧的“戏剧情境”则比其更丰富、更直观、更具冲突性,意在创造出“真实的(历史生活)幻觉”。较之前者的“配景”(连缀、合并、搭配),戏剧的情境设定,可以说是一种“造境”艺术。一方面,要造设真实的外部环境,以氤氲出真实的历史气息和特定的历史氛围;另一方面,又要造设真实的人际环境,即人物关系、人与人的冲突、心灵与心灵的撞碰包括心灵本身的分裂与矛盾,进而形成展示人物性格、命运、情感的生气灌注的艺术时空。在这一时空中,“戏剧艺术是普遍或局部的、永恒或暂时的约定俗成的东西的整体……给观众一种关于真实的幻觉”。因此,好的历史剧的戏剧情境的营造,能将历史生活创化、完形为艺术真实的整体性呈现。
由于历史本身就处在一种矛盾运动状态,戏剧的“情境”刚好能据此引入一种“破坏性”的冲突因素,而使历史情境转化为真正的戏剧性“情境”。京剧《膏药章》如用纯粹的历史真实来要求,则很难站得住脚。但由于营造出了充满“真实幻觉”的喜剧情境,如破败的龙旗,倾斜的构件、森严的石狮等“不协调”的外部环境,据此传达出晚清将亡大厦将倾的真实的历史信息;并通过“破坏性”因素的引入――革命党要巧借膏药章来刺杀官府大臣。原本胆小怕事、安贫乐道、优哉游哉且自鸣得意的小人物膏药章就此卷入到一场“革命”风潮中。没杀人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杀人凶手。即至绑赴刑场,膏药章因害怕而瘫软,被人用箩筐抬着且歌且舞、且嗟且叹等一系列喜剧性场面的出现,乃至在感叹时运不济中唱出了“如今的物价随风涨”等间离性的无稽之叹……这一些并没让观众感到“不真实”,反而让人们在规定情境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处于历史剧变期的小人物的悲怆、无奈和被揉搓的个人命运。
同样,京剧《廉史于成龙》的主人公为官十几年居然没能回一次家与妻子及家人团聚,仅就此而言,即使吻合历史实情,仍有不合情理、“高大全”之嫌。但由于很好地设定了戏剧情境――切近的民生疾苦、撞入眼帘的冤假错案、官员的强横腐败以及个人的囊中羞涩等一些“破坏性”因素的纷至沓来,才使这一人物真正“真实”起来、真实地“高大”起来,而观众更多的是体味到其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和悲悯之情才予以价值认同的。
以上两剧,一谐一正,但皆因营造了真实而具体的规定情境,从而能化部分的“不合理”为整体的“可信”,是“可信的不合理”(亚里士多德语)。我想,这就是“情境”的力量,也是艺术真实的力量!
2.倾力酿造真切的历史人生情感
情感的真实,是观众接纳艺术真实的重要表征。人之常情,古今相通。一部《四下河南》或是《秦香莲》,观众为何屡看不厌?盖因有情感的投射、情感的积淀、情感的互动,从而推人及己唤起了自身深切的人生体验。观众总是同情弱者、同情美好、同情正义而投以终极情感的关切!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道德的抽象继承”,在历史剧中则要化为“情感的即时传递”,因为观众在看戏时,更多的是在“人同此情”的情感反应中去咀嚼道德意味的,更多的是在人物情感是否真实上作出价值判断。我们常常看到,台上呼天抢地,台下无动于衷。这首先得归结为情感的不真实,“强哭者,虽悲不哀”也。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剧《赵氏孤儿》在对历史人生情感的真切把握上,显出自身的独到之处。全剧超越了机械的道德“二元对立”模式,写程婴的“忠义”,并不简单忽略掉他的人生“情感”,或把这一“情感”理念化、抽象化,而是铺足垫稳,写足了他为“救孤”而换嫡子时强烈的情感矛盾和内心冲突,写出了数百婴儿将因此受戮的紧张情势。而这些,丝毫无损于程婴的“忠义”,反而让这“忠义”,在痛苦、两难中更显真实、更切近人本身、更富人间气息!同理,在“孤儿”得知真相而欲仗剑弑“父”时,面对这个养育了自己十六年并呵护有加的“父亲”竟又是杀死自己亲生父亲的仇人,他现出了片刻的不忍与犹疑……艺术家捕捉到的这种情感状态,是源自深切的人生体验,使之在复杂中透出单纯、在个别中体现普遍,而更加切合人物此时此地的真实情感。设若没有这些笔触,人物都将会变成抽象的“道德”工具或“复仇”工具,沦为黑格尔所诟病的“抽象旨趣的人格化”产物,这也是艺术真实的本质规定性所忌惮的。
同样,越剧《西施归月》在对历史人生情感的体验与掘发上也作了有意味的探索。勾践“卧薪尝胆”,送西施入吴而最终灭吴,西施竟怀孕归来,深爱着西施并盼其归来成婚的范蠡得知此情而陷入不堪重负的情感危机中,痛苦、愤懑、退缩、怜悯、遣责、自责、担忧,种种真实的情感以及人性的弱点,在这一特定情势中一一展露;勾践视西施为复国的英雄又耻于承认而不能见容之;而西施为复国,体现出伟大的牺牲精神,为孩子,又体现出真切的母爱和母性的尊严……经由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和深切的审美体验,酿造并催化出情感的复杂性、丰富性、真实性,以及情感的“分裂与矛盾”,原本是戏剧艺术最能令人动容之处,然而,有批评者却将剧中的西施、勾践、范蠡分别误读为“”、“色狼”、“戴绿帽子”的小人。我想这既非作者原意也不符合实际的呈现状态。作者是希望在一种动态过程中来剖现历史人生所富有的真切情感,并融入自己对历史人生的普遍旨趣的情感化思考。而这恰恰是吻合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那儿,“历史”并非时空范畴中的社会历史,而是把事物当作“过程”而非“实体”来理解的辩证思维方法。而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的掌握”方式,也同样是把事物(如“卧薪尝胆”)当作一种历史人生的情感“过程”来加以动态地展开的,而不是借此来描写“抽象”观念而成为被马克思所批评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唯此,才能真正体现历史人生的真切情感以及“经心灵观照过的真实”。
3.着力塑造真实的历史人物性格
历史剧艺术直接关涉的就是“历史的人”及其所挟带的人类的普遍旨趣,并将其化为“有生命的实际存在”。沈从文先生先事文学,后“被迫”治史,正因为他的双重身份,使他认识到,历史研究不止于文物、文献,还要有形象。因此,当他面对那些“坛坛罐罐”发出的“历史信息”时,似乎感到了“人的体温”,看到的是活跃的人间生命!这些文物“不仅连接着生死,也融洽了人生”。这当是一个一身二任的有良知的学者的大智慧大悲慨!我在前所述及的那篇谈历史剧的文章中,也曾提及沈从文先生,也谈到过“首先要理解和同情你笔下的历史人物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这一观点,无独有偶,早就有史家声言要对历史人物充满“同情的了解”并以此作为历史主义的治史方法之一,史家如此,况艺术乎!
我们在评剧《帘卷西风》(改编自孙德民同名话剧)的创作中,没有简单地接受对慈禧这一人物“盖棺论定”的历史评价,而是紧扣一个27岁的有着特殊身份的年轻女性来进行“这一个”的性格塑造。既写出了她的精明强干和强悍的一面,又注意到她忍辱负重的一面;既写出了她渴望宠幸的小女子心态,又写出了她的冷峻肃杀;既写出了她的野心,又写出她身处险恶环境中的“平常心”;既写出了她在得逞后的踌躇满志,又写出了她的内心虚弱与后怕,并据此性格预示出一个原本正常的女人,注定要将自己终身放逐在政治漩涡中而没有归路的的命运走向。剧中有一个慈禧为取悦于慈安太后竟割下臂肉作药引的情节,若究其历史真实,恐难令人置信,但在其身处险境而又图谋战胜“臣”的特定时刻,此举,将其野心、机心、无奈之心、委屈之心,一并毕现而闪射出“有体温”的性格锋芒。
昆剧《公孙子都》取材于较为平面的《伐子都》,但由于对历史人物充满了“同情的了解”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切体验和审美观照,而使公孙子都这一人物性格大放异彩。全剧充满了人物的心灵挣扎、灵魂拷问、身体扭曲等富于张力的戏剧场面,子都刚愎、自恋、陕隘而不乏英雄气的性格质素,使其最终成为席勒所说的“自我惩罚”的悲剧英雄。由此表达出了一种历史人生的普遍情状,即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的良知,面对自己选择或被迫接受的命运,面对时间的严酷淘洗……这是历史的本质真实在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因此,子都的性格塑造抵达到历史心灵的幽暗之地,并使其宛若重生,从而给人以“体温”般的艺术真实。
综上所述,我们在历史剧的创作中,只要真正确立了戏剧的本体地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长期的纠结与龃龉,就会因其位阶不同而得以消解;艺术真实是依据着并涵盖了历史真实的一种更浑整、更澄明、更直观的自成体系的真实,是一种基于历史、高于历史、又显在于历史的真实,也是观众真正得以接受到的真实。观众会从此“真实”中,感受到历史律动的真实质地,但那是经由艺术真实生成出的一种历史质感!而要真正建构出令“历史”服膺也令观众信服的艺术真实,只有通过情境的营造、情感的酿造、性格的塑造等一系列的审美创造活动,才能达致“天地境界”并于此境界的“当下”情态中,掘发并照亮被历史烟尘遮蔽了的无数灵性生命的人性的真实、形象的真实乃至历史本质的真实!
参考文献:
[1] 席勒著,张玉书译.《论悲剧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98页
[2] 参见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第2页
[3] 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6页
[4]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第13页
[5] 参见陈香:《孔子2.21米比肩姚明?学者称警惕治史“狗仔化”》,《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14日
[6] 鲍列夫著,乔修业、常谢枫译.《美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第251页
[7] 济慈.《莱米亚》,转引自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84页
[8] 参见张庚.《古为今用--历史剧的灵魂》,载《张庚文录》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第392页
[9] 参见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楼书社,2005,第147页
[10] 参见萨塞.《戏剧美学初探》,载周靖波主编《西方剧论选》下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第422页
[11] 参见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1页
(作者为湖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国家一级编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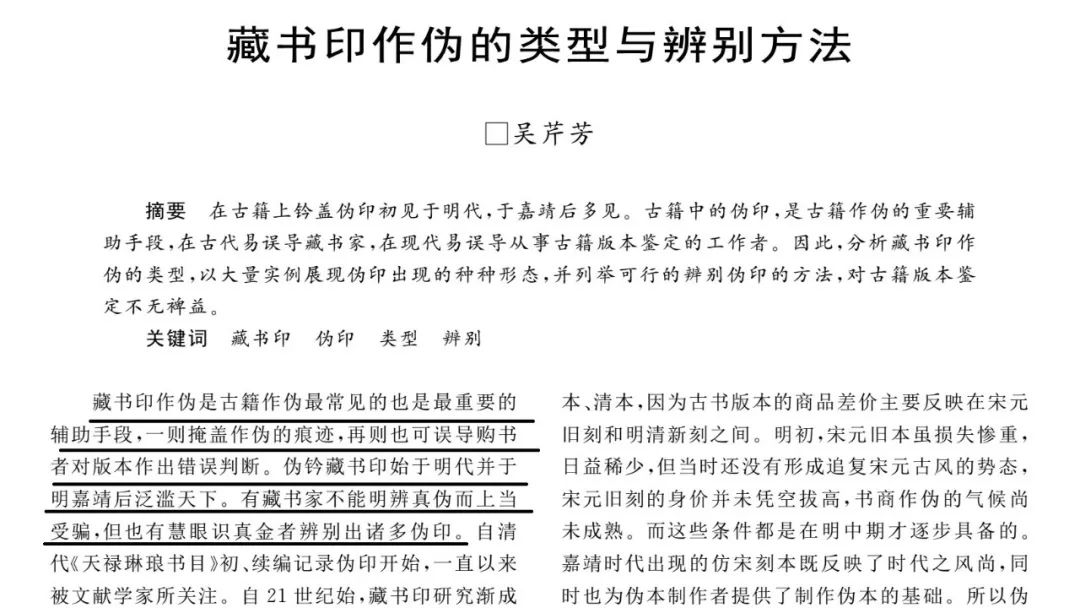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