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三史”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广泛使用的一个史学概念。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甚至在当代话语中,“三史”一直被赋予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厘清“三史”概念的源流,不仅有利于我们纵向把握“三史”的发展轨迹及其背后史学意识的嬗变,而且有助于我们横向理解“三史”内涵的多重性。
截至目前,有关“三史”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取径:一是以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者,以读史札记的形式着力探析早期“三史”的具体内涵及其转变,为我们认识“三史”提供了诸多先导性认知;
二是以高明士为代表的现代学者,依托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详细考察唐代“三史”转变及“三史科”的设立,开辟了“三史”在制度史层面研究的新路径;三是部分学人关注到《史通》中的“三史”问题,聚焦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的“三史”表达,拓展了“三史”研究的面相。
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三史”问题扫清了诸多疑滞,使我们对“三史”的发展演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魏晋南北朝,“三史”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文人学士往往以“三史”来标榜学识和矜耀史才,“三史”逐渐成为彰显学识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三史”不断进入文化视阈的顶端,开始成为史学典籍的代称,呈现鲜明的经典化特征。
除了《三国志》的记载外,以“三史”描绘士人知识渊博与学问精深的现象在魏晋以后的历史文献中层出迭见。如《晋书》记载傅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即以“三史”说明傅玄著述广博。
同书《刘乔传》附载刘乔之孙刘耽“少有行检,以义尚流称,为宗族所推。博学,明习《诗》、《礼》、三史”,这里将“三史”与《诗》《礼》并列,乃欲说明刘耽学问之精深渊博。东晋袁宏《后汉纪》引介许劭,称其“少读书,雅好三史”,即以“三史”表明许劭为学之兴趣所在。
又《魏书·阚骃传》载,“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同样是借“三史”来彰显阚骃之博闻强记。《隋书·文学传》云,陈朝潘徽“尤精三史。善属文,能持论”,亦言其人学识之专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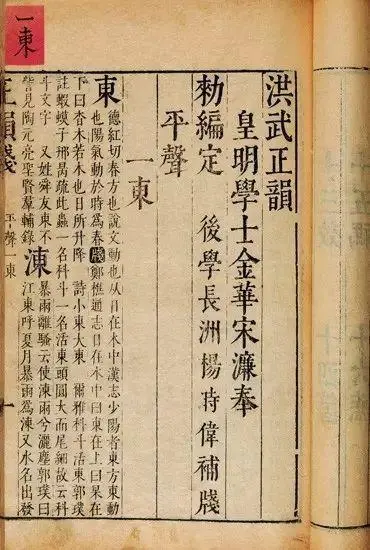
不难看出,在这些或隐或显的表述中,“三史”已经成为彰显士人博学与专精的重要指标。
“三史”的独特意义不仅反映在对历史人物的刻画中,同样也被广泛应用于现实的文化生活中。《北堂书钞》“继迹迁固”条曾引《华峤集序》云:“峤作《后汉书》百卷,张华等称其有良史之才,足以继迹迁固。
张华等人对华峤《后汉书》评价颇高,认为其书可以踵绪班马,享有“与三史并流”的殊荣。从中不难看出,此语虽然意在肯定华峤的史学成就,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三史”在当时历史知识图谱中具有的崇高地位。
西晋葛洪在《抱朴子·遐览》篇中也透露出“三史”在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其文云:“鄙人面墙,拘系儒教,独知有五经三史百氏之言,及浮华之诗赋,无益之短文,尽思守此,既有年矣。”

葛洪在此主要批驳鄙俗之人在知识学习上的局限,但在其表述中,“三史”与作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的“五经”合言,俨然成为史部典籍的代名词。对此,逯耀东的观察可谓敏锐:“魏晋时代所称的‘三史’,并不固定指某三种书……而是泛指一般史学著作而言。”
这一现象与魏晋以后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特别是在“五经”(或“六经”)成为经学代名词后,史学领域同样需要一个文化符号与之并行。那么,此前倍受推崇的“三史”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降及南北朝时期,受文学“骈俪化”风潮的影响,“三史”在实际表达中又往往与其他数量名词(特别是“五经”或“六经”)上下对举,形成文句上的对偶。在这种语法用例下,“三史”的经典化色彩日趋浓厚。
刘宋时,郭季产所撰《集异记》曾载张华恢诡逸事一则。其文云:“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积年能为幻化,及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

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华无不应声屈滞。”在这里,作者为了突显张华学识渊博,极言其人对“三史”“百家”等知识的熟络。所谓“百家”乃指诸子百家之学,而“三史”则是史部文献的代称。
相似的语词用例,也见于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其外族忠孝,比屋连甍,信义勇于干戈,诗书甘于酒醴。或有渔猎三史,纷纶五经,都讲开黉,诗生负帙。”
徐陵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出使东魏,同年,因侯景之乱而淹留北土。在此期间,为解思乡之情,徐陵修书至南朝宗室,畅想晚年安享天伦之时可以“渔猎三史,纷纶五经”。
此处的“三史”与“五经”互文成义,其内涵并非具体指称某三种史书,而是抽象地表示史部典籍。这种内涵指向在北齐阳松玠之《谈薮》中亦有体现。“三史”的经典化表达在南北朝时期蔚然成风,甚至在墓志中亦多见其例。

如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魏李达妻张氏墓志》在描述墓主生平时称道:“优柔三史,缱绻六经。摛文藻焰,妙善蛇形。”墓志以“三史”与“六经”对举,形容张氏经史素养之高妙。这样的用法与前述传世文献别无二致。
又如北齐天宝三年(553年)《独孤忻墓志》称赞墓主学识:“学通八素,博该三史。”此处“八素”乃“八索”之讹写,中古墓志颇为常见。作者将“三史”与上古经典“八索”对言,以此彰显墓主对古今典籍的博览。
这种表达背后同样显示“三史”浓厚的经典化色彩。“三史”一词在魏晋以后普遍流行,以至于士人学者往往引述“三史”以称赞他人学识。在此过程中,“三史”的文化地位日益尊崇,逐渐成为与“五经”(或“六经”)相对应的史部典籍的代名词。
当然,“三史”这一经典化过程并非向壁虚造。对于早期“三史”而言,其内涵在享有具体实指的同时,也暗含着对史书的总称。毕竟,在汉末三国时人的历史认知中,《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籍大体可以反映此前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对于时人而言,“三史”既可以指称三部具体史籍,也可以泛指史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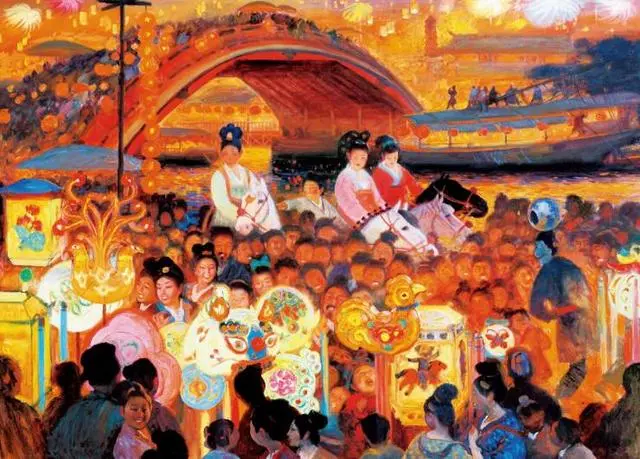
在“三史”趋于经典化的过程中,其具体实指也在无形中经历着复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三史”的经典化进程相始终,并深刻影响着此后“三史”概念的再次形塑。如上文所述,“三史”原本指代《史记》《汉书》《东观汉记》。
然而,自汉末以降,世人对“三史”各自价值的评判并不均衡。大体上,《汉书》为世所重,讲习此书者甚众;《史记》稍逊于《汉书》,但也广为传习。因此,当时除以“三史”昭示个人学养外,合称“《史》《汉》”“迁固”“班马”以凸显才学的现象,亦不乏其例除却史实失真与文辞拙劣,《东观汉记》在文本形态上的缺陷也是它难孚众望的原因之一。
正如学者所言,《东观汉记》不同于《史记》《汉书》“以一个整体的形态面世”,它在编修阶段就已经部分地传播与阅读。这种流传方式在当时为该书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从长久来看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弊端———《东观汉记》一书始终处于未能定型的散乱状态,甚至在东汉灭亡之后都“没有一个人对全书从头到尾进行整理和加工”。

结语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反映东汉历史的史籍,《东观汉记》本应究一代之兴衰、穷东都之始末,但是,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该书断限只是“起光武记注至灵帝”,与东汉国祚终于献帝的史实不符,无法承担载录东汉全部历史的使命。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