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讲《史记》,很新鲜。
他讲《史记》有三大特点:第一,既讲本纪、世家、列传,也讲表和书;第二,不只讲故事,也追溯历史故事背后的文本;第三,讲述《史记》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人的解读。也就是说,通过陈正宏的讲述,你读到的,不只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有两千年来中外读书人共同解读的《史记》。
在他的新书《血缘:〈史记〉的世家》中,陈正宏详细梳理了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通过一个个家族的故事,你会看到,支撑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还有基于共同文化基因向善的情感与道德。”
【司马迁写《史记》,建立的是一个有机体】
上观新闻:说起《史记》,人人都不陌生。《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高校历史学、文学专业的入门书。“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史记》并不好读,《史记》应该怎么读?
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委会委员):应该怎么读《史记》?简单来说,按照兴趣来读。
《史记》是按照五体的顺序来编写的,但如果你读《史记》一上来就去读《五帝本纪》,那你肯定就不想读了,因为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太远了,很多东西你也弄不清楚。
最好要从你已经知道的一些历史开始读,比如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都读过廉颇和蔺相如,本来就知道“将相和”这段故事,那么你从这里开始读就会容易读进去。其实这个故事在《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占的篇幅是非常小的,你看《廉颇蔺相如列传》全篇,尤其是这两个人的后半生,是更有意思的,如果你再去了解这两个人所处时代的背景,那整个三晋时代的历史走向也就呼之欲出了。
接着,可以再看看《史记》中的世家,那毕竟跟大多数中国人的家乡有关。山东人可以看看《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两湖人看看《楚世家》,浙江人看看《越王勾践世家》。一步一步地,你觉得自己的文言文基础大概能过关,对一些重要的篇章也有兴趣,那么你再去读《史记》里一些艰难的东西。
上观新闻:每个人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和自己相关的部分吗?
陈正宏:任何的历史文本,当然都无法跟现实中个人的具体经历相对应。历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什么会永远不变”。但是,虽然历史时刻在变化,却又在某些节点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你会从《史记》中看到很多和现在的联系。
上观新闻:《史记》记历代帝王的“本纪”写了十二篇,记历史大事的“表”写了十篇,记各种典章制度的“书”写了八篇,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的“世家”写了三十篇,记重要人物或族群的“列传”写了七十篇,这些篇数都成整数,代表了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陈正宏:这个问题在历代有多种解释。按照我的理解,司马迁写《史记》,架构精密,建立的是一个贯通古今的有机体。十二本纪的十二,源自十二支;十表的十,应该是十干。十二支和十干共同构成了一个永不结束的时间轮回。八书的八,应该是四面八方的八方,也就是一个延展的空间。至于三十世家,司马迁在《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以“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为解,说明为什么选三十这个数字,意指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环绕北极星,地上有三十根车辐支撑车轮正中的车毂,这就像现在的自行车车轮里有钢丝围绕支撑着车轴一样。所以,三十世家是把天地勾连了起来。到最后的七十列传,七十就是所谓的众生了。这是因为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当中,七十这个数字就像我们现在的三五七九当中的九一样,表示多,比如对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习惯的称呼是七十子之徒,秦代的博士有七十个名额等。
司马迁是天文历法学家,他的数学肯定很好,他自己说用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写了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没有这样精密的架构是不可能做到的。
【“世家”一体,有不可取消的独特意味】
上观新闻:然而,《史记》之后,班固编撰《汉书》时,本纪、传、书(改名叫志)、表都在,世家却没了,而且后世2000年史书几乎再不见“世家”,这是为什么?
陈正宏:这个应该是跟司马迁、班固两人对“世家”在历史中的意义认识不同有关。所谓“世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世代做官尤其是做大官的人家。《史记》把“世家”作为一种文章类别的名称来用,写的是历史上各重要诸侯大姓的家族史。但作为一种变通,司马迁也为历史地位处于本纪和列传之间,但并非诸侯大姓的人物留下了合适的空间,比如面貌很特别的《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
大家都知道,《孔子世家》写的主要是儒家祖师爷孔夫子的言行,不过因为后面附了简短的孔子后代世系,勉强还可以算世家;而《陈涉世家》描绘的,是秦汉之交农民暴动的人物陈胜和他的死党揭竿而起的故事,陈胜就根本没有世系可记,司马迁还是放进了世家。
因为存在这样面貌特别而复杂的情况,《史记》的“世家”一体,很让后来的评论家困惑。对于《史记》体例不纯的批评,也由此而生。到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世家这一体因为存在难以归类的麻烦,所以就索性被取消了。之后的正史里面,因此也很难再见到家族史一类的分体了。
上观新闻:所以,您特意以世家为主题写作,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史记》的新视角。
陈正宏:在我看来,《史记》的世家,实在有一种不可取消的独特意味在。
中国传统的观念,向来以家族、族属为重;而早期的诸侯大姓,又直接联结着大小不等的邦国和城池。正是靠着世家这一特殊的体裁,上下数千年间,血缘与地缘的复杂勾连,中华民族千回百转的融合之路,才能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任何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都会淘汰一批旧世家,诞生一批新世家。
上观新闻:世家那么多,司马迁为什么单单只挑选了这几十家写进《史记》的世家一体里?
陈正宏: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是非常重视家族血统的人,但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历史延续到西汉时期,族姓的繁多让再厉害的史家也很为难,必须要有取舍。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把世家各篇的叙录写得明显比其他四体各篇的叙录详细,还特地用了“嘉”字句,来表彰其中大部分世家的特异之处,比如“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嘉其能拒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等。而他所“嘉”的,几乎全是世家大姓中的有德者及其德行,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以历史学家的特有方式,向众人昭示,支撑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除了人的生物特性,还有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向善的情感与道德。
上观新闻:延伸说来,司马迁作《史记》,怎么选材,如何取舍?
陈正宏:司马迁说过三句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分别出自《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从这三句自述,可知司马迁的具体做法,主要是广泛收罗史料,做精密的排比和有限的整理工作,加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最终才写出这部气势恢宏的历史巨著。
《史记》的不凡之处在于如实记录了人是如何活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与后世的官修史书不同,司马迁笔下的人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也有一些边缘人物,像《封禅书》中蒙蔽汉武帝的方士,《晋世家》里自相残杀的兄弟,还有《刺客列传》里的刺客,他们是复杂的,都在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改变了历史或者想要改变历史。司马迁通过书写一个个生动的个体,用昨天的历史,来揭示永久的人性。
此外,他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自比,也明确地显示,他编纂《史记》,不可能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或者主要以作家的身份来创作的。
【别人眼中的故纸堆,却是珍贵的大数据】
上观新闻:您觉得司马迁不是以作家的身份来创作《史记》,那他是什么身份?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
陈正宏:司马迁的身份,以他成年后进入仕途的不同阶段来说,主要是三个:郎中、太史令和中书令。其中第一个身份郎中,是汉武帝的低级侍卫,是武官。第二个身份太史令,相当于现代的天文台台长兼档案馆馆长,是科学家、文献学家或者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对司马迁个人而言,《史记》是从这个阶段正式开始编纂的。最后一个中书令,是汉武帝的机要秘书长,《史记》也是司马迁在这个职位上完成的,因此这时的太史公,可以算是高级官员加史学家了。
司马迁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他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系统地加以梳理,并“翻译”成汉代人理解的文字。这个工作量非常大,他出色地完成了。

上观新闻:这和您的工作有些像,文献整理。
陈正宏:确实是,别人眼中的故纸堆,却是我眼中珍贵的大数据。
文献整理为一切文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曾做过一个比喻,假如我们在菜市场里,文献学就是负责买菜的。虽然不管烧菜,但买菜并不轻松,首先要知道整个菜场的布局,哪个摊头是卖菜的,哪个摊头是卖肉的,而且对同部位的肉,不同摊位的你还要会做比较。买好了之后,我们还会把菜洗好、分好,准备着给厨师使用。
有人觉得我讲《史记》比较新鲜,就因为我是学文献学的,我主要不是来跟你讲《史记》里有什么故事,而是讨论《史记》的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司马迁可能是利用了什么原始文献编写出来的,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上观新闻:的确,我们现在很多人谈到《史记》就觉得是在讲故事。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研究界,都有人在反复讨论《史记》的虚构问题,总觉得书中的人能这么生动地说话,有这么丰富曲折的情节,一定是文学不是历史。
陈正宏:细节描写不是文学的专利。历史如果没有细节,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如果把历史或者史书单纯地理解为数据、制度或者个人履历,觉得人的个性、心态、感情都不是历史学应该关注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生动就一定是虚构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在新闻里会看到某些事情之奇葩,某人发言之生猛,连小说家大概都想象不出来。而透过现实去反观历史,尤其是回顾《史记》这样的经典文本,会发现许多人、许多事都像是“古已有之”。所以用是否有细节乃至细节是否生动,来判断某个文本是文学文本还是历史文本,显然是不合适的。
上观新闻:梁启超曾经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法,他说《史记》在当时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史书,当然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
陈正宏:对。这意味着用传统古籍分类法中最流行的四部分类法来说,《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史记》的这种由子书而至史书的综合性特征,在著者司马迁那里,显现出的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他对人本身有非常深切的体认和感慨。他觉得,书写历史,如果我对于人性的东西不能揭示得很清楚,那么历史好像就没有被打开。比较《汉书》跟《史记》,做比较纯粹的历史研究的人似乎更喜欢《汉书》,因为数据准确,写论文引用比较放心;但是作为经典来阅读的时候,大部分人更爱的,恐怕还是《史记》,因为读司马迁的文字,就好像他在你面前,跟你聊天似的,而就是这样,才造就了这样一部经典的著作。
【判断作品是不是经典,和国别、民族都没关系】
上观新闻:您反复提到了人性,《史记》的伟大之处是不是探究了人与命运的关系?
陈正宏:《史记》处处有人性,司马迁非常懂人性,也看到了人的复杂性。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是把对个人行迹的叙说,和某个人在历史中起到的客观作用,这两者分得清清楚楚的。
比如太后吕雉,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由于她拥有强大权势和极其狠毒的手段,所以被后人熟知。这熟知的根源,就在于《史记》里那篇《吕太后本纪》,有吕后在刘邦死后残忍地对待其他女性的记载。但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里,却给予吕氏以正面的评价:“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翻译过来就是说,虽然吕太后在掌权的期间前前后后鼓捣出了不少动静,但是这些动静都仅仅限于皇宫之中,而且并没有损耗国之根本。对老百姓而言,严苛刑法很少用到,罪犯因此也很少,大家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又比如宋襄公,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典故,莫过于在宋楚泓之战中以彰显仁义为名提倡“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也就是王师不能攻击没有做好准备的对手,坐视战机流逝,等楚军列阵完毕后才发起进攻,最终落了个大败。宋襄公因此也成为中国军事史上被后来人取笑的对象。但是,司马迁却没有取笑宋襄公,非但没有取笑,他还在《宋微子世家》最后的“史太公曰”里,借“君子”之言,高度赞扬了“宋襄之有礼让也”。因为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切以战争逻辑为最高处事原则,而战争逻辑,是司马迁十分反感的。
在那么早的时代,司马迁著述能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一分为二地看历史中的人物,是很伟大的。
上观新闻:司马迁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如今跻身中国文化的超级IP,阅读《史记》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陈正宏:现在兴起了经典热、国学热,让我感到喜忧参半。喜的方面,是有年轻一代的来喜欢传统的经典总归是好事。不像以前,年轻人大多在西方历史文学领域打转,知道外国人的名字比中国人的名字都多。忧的是,我们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有人提出只读中国传统经典,不看别的。
我觉得,你不能偏于一方,经典是全人类共同的,同样的时代有柏拉图也有孔子,你都应该关注。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经典,和国别、民族都没有关系。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国学”这个词,这个词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尤其是中国国力比较衰弱的时候,它是为了对付西学的。而在现代学科语境中,中学、西学已经无法截然分开了。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们怎么读《史记》,为什么要读《史记》。我想《史记》之所以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认真地读一读,不单是因为它有名,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中有对中国早期历史的比较真确的追述,而这追述之中,又有对人性的深刻而独到的洞见。无关古今,也无关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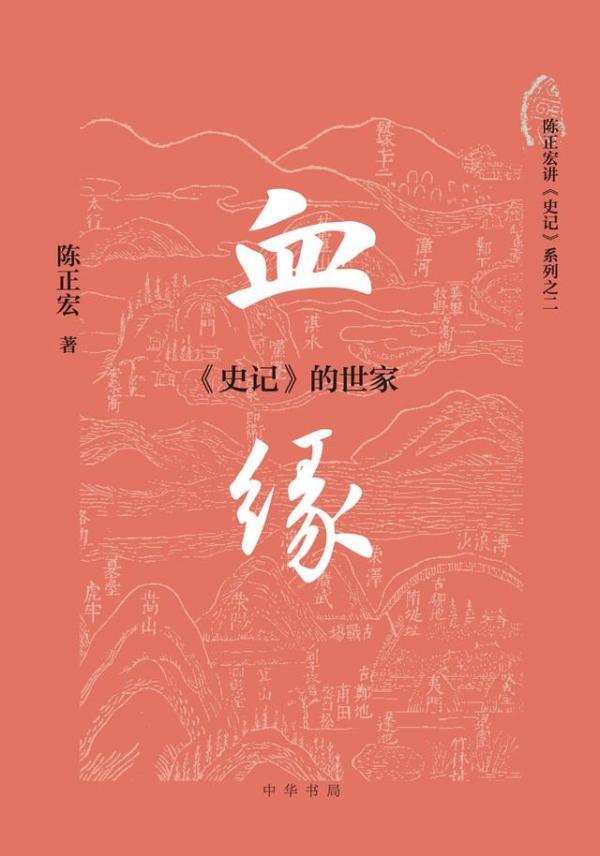
《血缘——《史记》的世家》陈正宏 著中华书局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