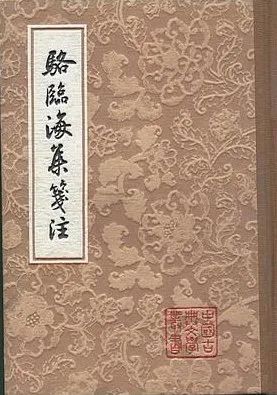
本文转自“跨界经纬”公众号,原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三辑)2008年10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骆宾王从军西域事,唐人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及两《唐书》骆宾王传只字未提。清人陈熙晋在为骆宾王诗文作笺注时首揭此事,谓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入寇,罢安西四镇,以薛仁贵为逻娑大总管。骆宾王在奉礼郎和东台详正学士任上,适以事见谪,从军西域。会仁贵兵败大非川,宾王久戍未归,作《荡子从军赋》以见意。此说一出,影响甚大,直至本世纪初,治骆宾王生平和初唐文史的学者多沿袭之。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后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郭平梁认为,骆宾王于仪凤四年(679,是年六月改元调露)作为波斯军的掌书记随裴行俭至西域平阿史那都支之乱,先到西州,然后假托训猎,东出柳中、蒲昌,北越天山,经蒲类至庭州,复转到天山南麓西进,至温宿城,越拔达岭,至碎叶城;裴行俭东返后,他仍在西域逗留了一段时间。王增斌则明确否定陈熙晋说,认为骆宾王根本没有参加过咸亨元年(670)薛仁贵、郭待封征讨吐蕃的队伍,骆宾王一生两次西行出塞:一在显庆四年(659)罢(或离)奉礼郎之职,随裴行俭从军西州,作《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一在调露元年(679)出狱后,随裴行俭西征突厥,作《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诗。薛宗正则认为,骆宾王从军边塞乃在仪凤三年(678),裴行俭于是年深秋发师长安,次岁夏抵西州,迂道莆类,奇袭阿史那都支于轮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对手。骆宾王乃裴行俭军中书记,随军到达碎叶。及裴行俭班师,一部分幕僚亦随之东返,骆宾王留下未行,继续佐幕于王方翼。大约到了开耀元年(681)王方翼调徙金山都护,移治庭州,骆宾王乘势辞归。我们通过对骆宾王创作与交游的详细考察,尤其是在充分检讨和利用近二十年来唐代西北军事史研究成果后,发现上述诸说与骆宾王一生行事、诗文创作和初唐西域军事行动均有一些抵牾之处。本文认为,骆宾王集中诸多从军西北的边塞诗作,既非如陈熙晋等人所说是咸亨元年秋随薛仁贵军西击吐蕃时作,亦非如王增斌等人所说是显庆四年和调露元年两次随裴行俭至西州时作,而是骆宾王于咸亨元年夏四月离奉礼郎任跟随阿史那忠出征西域、安抚西蕃诸部落时所作。
01
王增斌认为,骆宾王分别于显庆四年、调露元年两次随裴行俭从军西域。但这两个时间,与骆宾王集中诸多边塞诗作、生平交游都有不合之处。
《新唐书》卷三《高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述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以送波斯王子泥洹师为名讨西突厥事,均谓于调露元年(679)六月出征。而裴行俭离京时,骆宾王尚幽絷在狱,根本不可能随军西征。
学界大多认为,骆宾王于仪凤三年(678)秋后因在侍御史任上“频贡章疏讽谏”,得罪武后,被诬下狱。据新旧《唐书•高宗纪》,知高宗仪凤四年(679)六月辛亥(初三日),于东都颁诏大赦,并改元调露元年。按理说,骆宾王应该在六月大赦出狱,但不知是当时从皇帝下诏大赦到具体执行需要一段时间,还是有人从中作梗,总之骆宾王一直到秋后还在狱中。《在狱咏蝉并序》和《萤火赋并序》皆为骆宾王调露元年秋在狱中所作。《在狱咏蝉序》云“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表明他已听闻高宗颁布改元、自己将被大赦的消息;而“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则似对自己不可能马上出狱心存忧惧。又,《萤火赋序》云:“余猥以明时,久遭幽絷。见一叶之已落,知四运之将终。凄然客之为心乎,悲哉秋之为气也。'‘此文亦当作于入狱第二年的秋季。假若为仪凤三年(678)秋刚刚下狱时作,不当云“久遭幽絷”。骆宾王《宪台岀繁寒夜有怀》一诗,有学者系之于仪凤三年冬骆宾王刚下狱时所作,但我们认为,此诗当如骆祥发所云,为调露元年冬骆宾王刚出狱时作。因为诗题中的“出絷”不应理解为入狱。《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云:“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其鞫案禁系,则委之大理。贞观末,御史中丞李干佑以囚自大理来往,滋其奸故,又案事入法,多为大理所反,乃奏于台中置东西二狱,以自系劾。开元中,大夫崔隐甫复奏罢之。''知唐自贞观末至开元中,弹劾、鞠案、幽禁均不需岀御史台,御史台中自有东西二狱。故“出絷"应作出狱讲。据此诗意可知,到“殷忧岁序阑"的调露元年冬,骆宾王方得出狱。而《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云:"(调露元年,679)九月壬午,吏部侍郎裴行俭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匍以归。”可见,自调露元年六月裴行俭奉诏离京征讨西突厥,至同年九月班师回朝这一段时间,骆宾王一直都在狱中,完全没有可能参加此次军事行动。郭平梁、王增斌谓骆宾王于调露元年六月岀狱后即随裴行俭西征突厥,大误。薛宗正谓骆宾王仪凤三年秋即已从军西域,且在西域长达三年之久,至开耀元年(681)方归,则没有考虑到骆宾王在侍御史任上曾被诬下狱事,更与史实不符。
因为考虑到裴行俭此次军事行动只有三个多月,而骆宾王的一些边塞诗给人一种在边塞很长时间的感觉,所以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除调露元年随裴行俭西征突厥外,还在显庆四年(659)罢去奉礼郎之官,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而岀塞西域。我们认为,王增斌这个推断同样也难以成立。
骆宾王从军西域时,李峤曾作有《送骆奉礼从军》诗。对于李峤的生卒年,学界观点近来已趋于一致,大都认为李峤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或二十年(646)。如果骆宾王确于显庆四年从军西域的话,那么李峤为其饯行并作诗相赠时只有十四五岁,不太符合情理。另外,王增斌认为骆宾王集中《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均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从军西州时。细绎《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诗意,我们发现此两诗中所述节令、路线和军中情绪,与王增斌所说骆宾王调露元年所作《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诗并无二致,王增斌将它们别作两次入塞之作,理据不足。而且《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一诗也不可能作于显庆四年。因为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郎中为大夫。所以“辛常伯"之称谓不应出现在龙朔二年二月前,王增斌谓《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都作于显庆四年随裴行俭赴西州长史任时,与骆宾王当时交游情况、朝廷职官制度都扦格难通。
02
我们认为,骆宾王一生只有一次从军西域的经历,从军时间最有可能是陈熙晋所推定的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只不过陈熙晋说亦有一些舛误。
王增斌在《骆宾王从军西域时间考——兼探骆宾王生平》文中之所以要另立新说,完全否定陈熙晋所持的骆宾王咸亨元年随薛仁贵西击吐蕃说,其论据有三:一是时间上不合,薛军出发是在初夏,骆诗显示战事之发生是在秋季;二是地域上不合,咸亨元年的唐蕃战争发生在大非川、乌海一带,而骆西行边陲诗中所及地名与之全然无涉;三是战事持续时间有别。薛军之征只有三到四月,而宾王在边地时间非短,绝不只三个月。如果用骆宾王边塞诗核之咸亨元年四月薛仁贵西征吐蕃事,王增斌文中二、三两点质疑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在重新对骆宾王所有西征作品及李峤相关酬赠诗作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后,尤其是全面核检近年来唐史学界和敦煌吐鲁番学界对唐前期西北军事史研究的成果之后,发现骆宾王此次参加的并不是薛仁贵所统帅的西击吐蕃的战争,而是与薛军同时出发、东西线相互配合的,由阿史那忠率领的前往西域执行安抚任务的一次军事行动。
对于咸亨元年阿史那忠安抚西域的军事行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完全失载。但是,立于昭陵的《阿史那忠碑》(下文简称《阿碑》)和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下文简称《阿志》)则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历史信息。《阿志》云:“而有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公问望著于遐迩,信义行乎夷狄。饷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阿碑》云:“寻又奉诏X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乘X则发,在变以能通,扙义斯举,有征而无战,威信并行,羌夷是X,洎乎振旅,频加劳问。”据郭平梁、陈谦等学者研究,这两段文字记载的都是咸亨元年唐朝派兵西讨吐蕃事。郭平梁认为,唐朝似乎有一个惯例,每次岀征要派两支军队,一支“讨伐”,一支“安抚”。当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隅取龟兹拨换城,被迫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时,唐朝为了平定这一变乱,除了派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外,还派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与薛仁贵军主要是到青海出讨吐蕃不同,阿史那忠所统帅的军队则远征西北边陲,对西域地区受吐蕃贵族挟制的那些部落和地区做“一些解释和招纳工作”。骆宾王在咸亨元年参加的就是阿史那忠的军队,其集中诸多从军西域之作与阿史那忠的这次军事行动合若符契。
首先,阿史那忠军出师时间与骆宾王诗中所写相合。史籍明确记载薛仁贵军是在咸亨元年四月离京西征的,阿史那忠军当与此同时出发。陈熙晋、王增斌都曾根据骆宾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推定骆宾王此次从军是在秋季,所以王增斌认为陈熙晋所持骆宾王咸亨元年随薛仁贵出讨吐蕃说时间不合。其实,陈、王二人和现当代大多学者不仅都错解了此诗,也忽视了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和李峤《送骆奉礼从军》诗中所透露出来的时令信息。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诗末云:“上苑梅花发,御沟杨柳新。只应持此曲,别作边城春。”“梅花”、“杨柳”等,既是言《梅花落》、《折杨柳》等别曲名,也是在写送别之境,说明骆宾王离京时在春夏之交。李峤《送骆奉礼从军》诗中云:“琴尊留别赏,风景惜离晨。笛梅含晩吹,营柳带余春。”“笛梅”、“营柳”等,不只是用别曲《梅花落》、周亚夫军细柳典,同样也交代了送别之境——“余春”。而骆宾王《早秋岀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并非作于离京之时,很可能是骆宾王随阿史那忠军队西行出玉门关,回顾经行路线时作。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薛仁贵军四月离京,七月方至大非川、乌海一带,行军用时长达三月,是有缘由的。从薛仁贵被任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的头衔看,唐朝这次派薛仁贵出师的主要目标是讨击吐蕃,直指吐蕃的首都逻娑(即今西藏拉萨),但是薛仁贵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护送被吐蕃所灭的吐谷浑还故地。《新唐书•吐蕃传上》述此事时即云:“并护吐谷浑还国。”而此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及弘化公主正在凉州避难,薛仁贵军要先至凉州接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然后才能南下击吐蕃,所以行军时间较长。薛仁贵军和阿史那忠军可能于六月底抵达凉州,然后薛仁贵军保护着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和弘化公主南下,经鄯州,至七月中于大非川遭遇吐蕃论钦陵的大军。而阿史那忠军在凉州与薛仁贵军分手之后,则继续西行,大约至七月上中旬至玉门关。骆宾王《早秋岀塞寄东台详正学士》疑即写于出玉门关时。阿史那忠军行至蒲类海时,骆宾王又作有《夕次蒲类津》,诗中显示节令仍是秋季:“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显然与其《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时间相距不远。所以,骆宾王集中西行出塞诗作之时令与咸亨元年唐朝派阿史那忠出兵西域之行军时间是完全相符的。
其次,骆宾王从军西域诗中所写地名亦与阿史那忠军出征路线同。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长安西通凉州有南北两条驿道,唐军出兵西域常走北线,因沿途镇戍甚多,容易集结招募兵力。史料记载,薛仁贵离开京城时兵力只有五万,而到大非川与吐蕃大军遭遇时,则变成了“十余万''。这多出来的五万余人,可能是薛仁贵军离京北上西行途中,经过邠州、泾州、原州、会州、凉州等地沿途集结招募的兵力。阿史那忠军从长安至凉州这一段时间,当与薛仁贵军同行,沿途可能也有增兵之举。骆宾王《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诗云:“塞荒行辨玉,台远尚名轮。泄井怀边将,寻源重汉臣。”说明他离京时就知道此次出征是要出玉门关,目的地则在西域的轮台、疏勒等地,与薛仁贵军任务明显不同。骆宾王随军行经泾州,恰与时任安定县尉的李峤相会,李峤为之作《送骆奉礼从军》。骆宾王岀玉门关时所作《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则回顾了自京至边关行经之处及心境,其中“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乃言其自长安北上,途经邠州、泾州、原州之状;“汉月明关陇,胡云聚塞垣”,盖述其自关中入陇,“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则写出玉门关时之悲愁。骆宾王岀塞后诸作如《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宿温城望军营》、《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边庭落日》、《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诗,则具体反映了阿史那忠军安抚西域时行经地点和路线。《阿志》述阿史那忠之西行是“饷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用这些古老传说中的地名来形容其行程之远,骆诗中则出现了贺延磧、流沙、轮台、疏勒、蒲类海、和阗河、天山、交河、弱水、龙鳞水、马首山、密须、宿温城(即温肃城)、碎叶等具体地名。史载当时吐蕃攻陷了龟兹的拨换城,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安西四镇都曾落入吐蕃手中,然据西域史学者近年来的考证,唐虽于咸亨元年被迫下令罢安西四镇,但由于西域形势发生变化,实际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二镇,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并未放弃,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四镇可能只是遭受了一次围困,唐朝守军并未放弃。阿史那忠军遂得以在天山南北对西蕃诸部落“频加劳问”。
另外,阿史那忠此次远征西域执行的主要是“安抚”、“劳问”的任务,是“有征无战”,《阿志》用“情不论功"、“事非饰让”等隐晦之词刻意曲避阿史那忠此行无甚功劳的史实。与之相应,骆宾王诸戍守西域诗亦未有战斗、献捷或败绩的描述,诗中弥漫着消沉、郁闷的情绪,如其《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诗云:“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即言自己随军远行万里,征而不战,劳而无功的抑郁之情。《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云:“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徒。'‘则是厌于戍边,思念故园,亦情有可原。
总之,骆宾王从军西域既不像王增斌等人所说是在调露元年或显庆四年随裴行俭赴西州,也非如陈熙晋等人所言是咸亨元年秋从薛仁贵赴青海讨击吐蕃,而是在咸亨元年四月随阿史那忠西行远征,对西域诸藩部落进行“安抚”、“劳问”。
03
陈熙晋、王增斌诸人论骆宾王从军西域都存在着一个错误,即大多认为骆宾王是在罢或离东台详正学士任西行的。实际上,骆宾王从未任过东台详正学士一职,骆诗中多次出现的东台详正学士只是其在京友人所任之职。
陈熙晋谓骆宾王入京为奉礼郎后不久又任东台详正学士,在奉礼郎和东台详正学士任上从军西域。此说实误。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奉礼郎是太常寺从九品上之卑职小官。而详正学士则是门下省弘文馆中由五品以上大臣兼任的图籍校理官。骆宾王要由从九品上阶的奉礼郎而升任或兼任五品以上的详正学士是不可想象的。王增斌则认为骆宾王是由侍御史兼任或升任详正学士,然后在详正学士任上从军西域的。我们认为,侍御史官居六品,肯定不可能兼任详正学士,虽有升任详正学士之可能,但是,如前所述,骆宾王刚任侍御史就因“频贡章疏讽谏”,得罪武后,被诬下狱。后虽被赦出狱,但从骆宾王出狱前后所作《在狱咏蝉》、《萤火虫赋》、《畴昔篇》、《宪台出系寒夜咏怀》诸诗之抑郁愤懑之情看,武后对骆宾王似乎余怒未消,不太可能在骆出狱后擢升他为详正学士。事实上,不久之后骆宾王就被谪为临海丞(从第八品上阶),更说明骆宾王在出狱后无由担任详正学士。另外,如果骆宾王确实担任过详正学士这样的清望之官的话,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和新旧《唐书》骆宾王传也不太可能只记其任侍御史这样的六品官,而失载其任详正学士一职。
骆宾王既然没有可能担任过详正学士,那么他在咸亨元年出塞时为什么又有两首赠与东台详正学士的诗作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骆宾王此前在太常寺奉礼郎任上与东台详正学士过从甚密、情感较深的缘故。因为朝廷在制定朝会礼仪时,虽由太常寺相关官员主事,然详正学士亦得参与。《唐六典》卷八《门下省》条即云:“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授教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另据《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一》,唐高宗乾封中大臣对许敬宗、李义府所修显庆新礼普遍不满,多有讨论,以至仪凤年间“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贞观、显庆二《礼》自乾封至咸亨初年,骆宾王在太常寺奉礼郎任上,当因修礼、议礼之事与门下省弘文馆详正学士有所交往。加上骆宾王文才横溢,可能与详正学士多有诗文之雅集。他后来在边城所作《久戍边城有怀京邑》:"棘寺游三礼,蓬山簉八儒。”回顾了从军前在京为奉礼郎事。《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昔余迷学步,投迹忝词源。兰渚浮延阁,蓬山款禁园。彯缨陪级冕,载笔偶玙璠。”则叙其在奉礼郎任上“陪”、“偶”东台详正学士,诗文唱和雅集之状。“汲冢宁详蠹,秦牢讵辨冤。”乃言东台详正学士之工作,非己之职事。所以,当他在奉礼郎任上随军西征时,与善诗擅文的“故人”东台详正学士辞别、酬赠,应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当时东台详正学士的总召集人崔行功,正是现存阿史那忠墓志的作者,且在墓志中对阿史那忠咸亨元年安抚西域之事多有褒扬,可见崔行功与阿史那忠关系也不一般。咸亨元年阿史那忠率军西行时,崔行功及东台众详正学士完全可能为之送行。骆宾王随军西行时虽身为奉礼郎,然因主帅和自己两方面均与东台详正学士有关系,作诗与东台详正学士饯别、酬和亦属情理中事。
另外,我们从骆宾王诗中东台与详正学士之并称,亦可证明骆宾王从军西行必在咸亨元年十二月之前,前文所述王增斌、薛宗正、郭平梁诸人所持调露元年说显误。据《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门下省改称东台始于龙朔二年(662)二月,终于咸亨元年十二月。郭平梁为了证明骆宾王从军西域是在调露中,力主骆宾王此两诗中“东台”系沿用咸亨前旧称,并举岑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诗为例,说“岑参系唐玄、肃、代宗时人,时东台之名早被废弃,他所用的东台当系旧称,这首诗告诉我们,骆宾王西域之行是仪凤之后的事。”实际上,门下省之称为东台见于唐代存世诗文中唯此二例,更未见有人在咸亨后诗文中用此旧称。郭文所引岑参诗题中“东台”非门下省之旧称,乃是唐人对东都御史台的俗称。薛平梁举此诗不当,系未明唐代官制致误。岑参此诗并不能说明骆宾王从军西征是在咸亨后。关于详正学士之设置时间,学界大多依据《唐六典》及新旧《唐书•职官志》谓始于仪凤中,然《旧唐书•崔行功传》记载:“显庆中,罢讎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其后又诏东台侍郎赵仁本、东台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行功仍专知御集。迁兰台侍郎。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上元元年,卒官。'‘据此,详正学士之设当早于仪凤中,始于咸亨元年东台复称门下省之前。所以,在骆宾王西行岀塞的咸亨元年,东台与详正学士均为当时实际之官名,诗题中并称之既非沿用旧称亦非后人所改。
综上所考,学界对骆宾王从军西域之考述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讹误。事实上,骆宾王之从军西域前只担任过奉礼郎,未任东台详正学士;离京是在咸亨元年四月,并非在显庆四年和调露元年;此次远征西域的统帅亦非薛仁贵,而是阿史那忠;他们此行之军事目的并非前往青海讨击吐蕃,而是远征西域,安抚、劳问被吐蕃威胁、挟制的西域诸藩部落。
需要图书推送、加读者群的各位师友请添加小编微信(sjhj2072),并备注“学校/单位/专业+推书/入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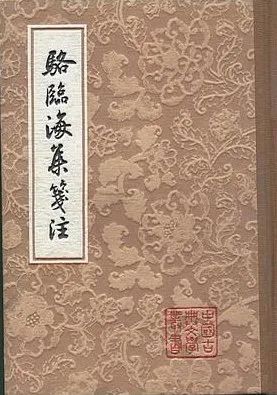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