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金城
丝绸之路人文艺术是一“大象”。这里的“大象”可以理解为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广大而无法名状的无形之象、一种氤氲出的大气象,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寓言“盲人摸象”中比喻的实在之象,都是想象和形容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的整体性存在。大象无形,并不是说大象不存在。
关于人文,中外古今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将人文理解为培养人健康成长的文化,主要是与人的内在需求相关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和规范,是先进的健康的价值观,涉及人类社会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以及心理、意识、思维等。从学科来说,人文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伦理、语言等。艺术当然也具有人文性,但是它的存在形态和表达方式又与一般人文领域不同,在学科分类中作为独立类别。关于“丝绸之路艺术”,取其广义概念,包括建筑、雕塑、绘画、陶瓷及其它器物、音乐舞蹈、织物服饰、戏剧、文学、写本等艺术领域。物质属性与审美属性融为一体是丝绸之路艺术的显著特点之一。
将“人文”与“艺术”并置,是基于对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并受葛兆光先生关于思想和符号关系观点的启发。
追溯古代人类思想的历程,需要有三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当古人有了“思想”。第二,这种思想中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观念。第三,“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因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想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之中,传达给他人,留传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
联系到丝绸之路研究,我对葛先生这段话的理解是,文字、图饰、图像、器物等符号的存在本身就蕴蓄了思想、观念和心情,带有这些符号的物品交流就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这些物品被相互欣赏,就包括了观念的认可。当然,思想和情感并不只有这种交流方式,但是丝绸之路的交流无疑以丰富的艺术符号将不同的观念、思想和情感带入了人类史、思想史和艺术史。艺术与思想的关系逻辑也可以延伸到艺术与人文的关系,人文与艺术,一为内涵和“血肉”,一为肌体和表达,互为表里,构成人文艺术的无形大象。
那么,如何触摸到这一“大象”,证明它是确实存在的,而不是虚幻和想象的呢?这既需要历史事实作为证据,也需要理论思维对其发现和建构。
丝绸之路人文艺术有具体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它不是已有现象和成果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类因为丝绸之路的交流而创造出新的艺术样态,它承载和传播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大到对某个时代甚至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宗教信仰和艺术倾向的相互交流和融通,比如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流布和传播,联系着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交汇和相互影响;比如“希腊化”对东西方文化艺术在当代和后世的广泛影响,比如中国的丝绸、瓷器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艺术创造、审美标准的影响,印度宗教、波斯艺术对中国和东亚的影响等等。小到具体的艺术现象中包含多种人文因素,比如某种服饰(参见李肖冰《丝绸之路服饰研究》、赵丰《丝路之绸》所述)、某种舞姿(如《丝路花雨》对“反弹琵琶”、高金荣对“千手观音”的研究创化)、某种乐器(参见金秋《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所述)、某种雕塑(如佛像的演变)、某种图像(如飞天形象的演变)、某幅壁画(如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敦煌249窟顶壁画)、某个符号(如卍型)、某个印章(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谷、地中海、中亚都有印章印珠或滚筒印章及其传播)、某种钱币图像(如在中国出土的罗马钱币)、某种纹饰图案(如克孜尔石窟中的菱格画)、某个器物造型(如来通杯)、某种窟型(如凉州模式)、某个动物形象(如马的形象、狮子形象)、某个故事变形(如猕猴王本生故事)、某种绘画技巧、某种题材演变、某种母题衍生、某种原型置换(参见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简史》)等等,都可以程度不同地找出与丝绸之路不同文明形态、文化模式、哲学思想、宗教信仰、艺术特质之间的渊源关系。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整理,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这足以说明,丝绸之路沿线的人文艺术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是客观存在的。这似乎是不需要特别论证的,或者说是不证自明的。然而,这一切似乎仍然不能说明丝绸之路人文艺术作为整体的存在,不足以使丝绸之路人文艺术作为自洽的研究对象进入主流话语。这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具体的事实层面,而在于认知的维度、理念和方法。
丝绸之路人文艺术所遇到的问题,与艺术学领域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它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关于“艺术一般”的认知问题。在艺术学领域,前几年因为在新的学科目录中,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分离出来,独立为艺术学门类,分为五个一级学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疑问就是,有没有一个被称为“艺术”的现象存在?艺术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质疑的理由是,有音乐与舞蹈学,有戏剧与影视学,有美术学,有设计学,有各门艺术理论,然而,超越这些具体门类的“艺术”在哪里?这个整体统称“艺术”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它是否真的存在?进而质疑,艺术能不能作为学科?“艺术理论”的概念能否成立、研究有没有意义?这种质疑或许暴露出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致命问题。现在,丝绸之路艺术面临的质疑也是这样:有丝绸之路上的建筑、雕塑、绘画艺术,有陶瓷艺术、音乐舞蹈艺术、服饰艺术等门类艺术;在丝绸之路沿线有两河流域艺术、印度艺术、埃及艺术、希腊罗马艺术、波斯艺术、犍陀罗艺术、草原艺术、中亚艺术、东亚和东南亚艺术等等;有粟特艺术、俄罗斯艺术、阿拉伯艺术、中国艺术、日本艺术等等,但是,有没有一个统称为“丝绸之路艺术”的事物存在?丝绸之路艺术是否是一个真问题?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人文艺术今天遇到的质疑与艺术学受到的质疑在性质和逻辑上是一样的。
对此,李心峰先生在《论“艺术一般”》一文中做了深刻阐释,这也适用于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研究。他将艺术学遇到的质疑视为关于“艺术一般”的观念问题,认为艺术一般“是我们的思维对各种具体的艺术事象进行合理的逻辑抽象、理论概括的产物,但逻辑反映着历史,思维依托着现实,抽象来源于具体,理论来源于实践,一般产生于特殊。艺术一般虽然产生于逻辑的抽象,但它绝非是非现实的虚构,而是就存在于现实之中,就存在于现实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艺术特殊之中。‘艺术一般’范畴之所以能够成立,其依据在于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的一般与特殊辩证统一的哲学原理”。据此“应将‘艺术一般’作为艺术原理、艺术概论或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来对待”。笔者很认同李心峰先生的观点,并认为其理论观点和逻辑也适用于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的研究。丝绸之路人文艺术遇到的问题,从逻辑上说就是具体现象与普遍一般的关系问题。有丝绸之路上的具体艺术现象的存在,就有“丝绸之路艺术”的存在。而以往丝绸之路艺术具体的研究成果丰硕,却基本限于具体门类或区域的研究,没有能够进入艺术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没有建立“丝绸之路艺术”的整体概念,没有从具体中看到一般的重要性。
笔者基于对丝绸之路艺术以往研究成果的感悟和认知,曾提出“丝绸之路艺术整体观”的理念,认为丝绸之路艺术的差异性与整体性是对立统一的,有丝绸之路具体艺术,也有丝绸之路艺术一般,它们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在我看来,丝绸之路艺术因为相互冲撞、交流、共融而生发出新的样态和现象,如果追溯其渊源,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埃及艺术、印度艺术、地中海和希腊艺术、波斯艺术、草原艺术、中国艺术等等既是独立的艺术体系,又是因交流互鉴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典型,这些艺术事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美与共,是用单一的民族、国家、地域范畴所不能涵盖的,在丝绸之路的视域中,这是属于人类共有的遗产,是经过几千年多民族、多地区、多文化模式、多审美取向长期孕育出来的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成果,也是值得我们为此付出心血和努力研究的瑰宝。进而如前所述,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人文与艺术互为表里,这些“和而不同”、无形的人文艺术关系所构成的整体就是丝绸之路人文艺术“一般”。对它的研究,既需要具体的微观研究,发现其特殊性,也需要宏观的、超越具体现象的整体研究,发现其普遍性。
把握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的“大象”,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是从各个具体的门类去把握,如丝绸之路历史、考古、宗教、知识体系等所涉及的广泛领域的具体研究,以及丝绸之路织物服饰艺术、陶瓷艺术、乐舞艺术等(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这一维度的把握打破了国家、民族、地域的界限,也是丝绸之路人文艺术必需的、最基本的研究,它可以形成专门史和专门的理论。另一个维度,就是对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的整体把握,是研究各门人文艺术现象所具有的共同性,阐释以人类对艺术的需求建构起的特殊的价值关系和意义链。“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道隐无名”却无处不在。这种整体性也涉及理论问题,比如是以传统的“艺术”概念和理论“匡正”、选择、淘汰丝绸之路中“非艺术”的内容,还是以对丝绸之路人文艺术新的研究成果改变“艺术”的传统观念?再如,丝绸之路艺术功能的未特定性、各门艺术之间的特殊关联性、物质实用与艺术审美的统一性等都是与丝绸之路相关却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此外,这种整体性还包括,由于不同时空中人文艺术的交流生发的艺术新样态,人文艺术传播过程中构成的意义链,长时段历史记忆的连续性,空间的差异对比、互为参照和贯通生成新意等内容。有了丝绸之路人文艺术一般的理念和思维,更便于发现其中的相互联系、反差冲撞、互融共存等复杂关系。
在人类史上,丝绸之路人文艺术是一个整体的存在,是一个有待开掘的富矿,是无形的大象,研究视域、维度和方法需要更新。对无形之大象的把握,“摸象”也许是难免的过程,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大处着眼,需要新的视域和新的理论把握,更加细分具体的研究与更加宏观整体的研究都是必要的途径和方式。笔者认为,站在新的历史和思想高度对这一大象的整体观照,或许才刚刚开始,丝绸之路研究应该融入人文艺术的视角和方法,包括有依据的推测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建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同时,历史维度的拓展与理论维度的深化,走向融通整合与更加细致入微,都将为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的研究开创新局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 〈16ZDA173〉研究成果;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该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科学报》 2019年7月31日 3版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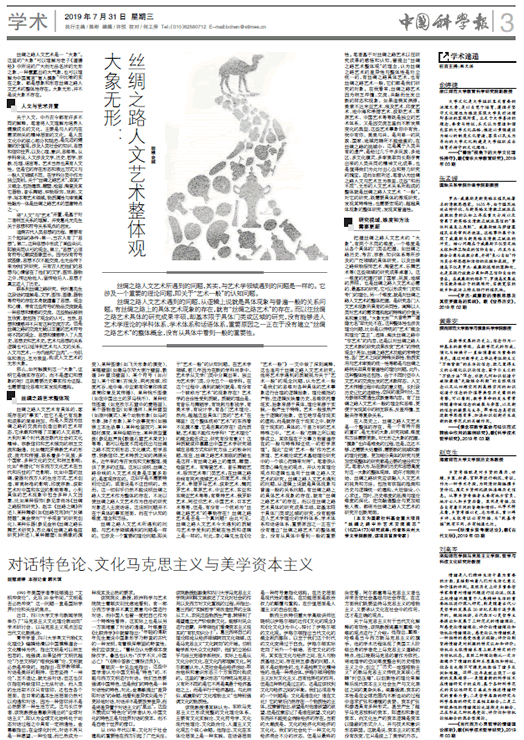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