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萧轶,实习生李睿康)10月19日晚,由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诗人、译者胡续东主持的《阳光打在地上——北大当代诗选(1978-2018)》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单向空间·花家地店举办。北大不同时期的三代诗人,80年代的西渡,90年代的胡续东、冷霜,以及00年代的徐钺和大家分享在校园写作时光留下的痕迹,以及那些共同被诗歌点亮的生命片段。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阳光打在地上》收录了包括骆一禾、海子、臧棣等不同时期的40位北大诗人的作品,该书的特点在于入选诗人有所减少,让入选者能有较多的作品展示;另外,相比表现校园诗歌文化,这本书侧重体现诗人的艺术水准上。希望从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诗中反观一个诗人从走出学校到现在在观念上和认知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不限于选入他们求学阶段的作品,而更多从“当代诗歌”成就的角度,来考虑诗人和诗作的取舍。限于篇幅,各人名下的作品数量仍是偏少,也无法容纳许多长诗。编者洪子诚在书的前言中说,这本书可以看作对臧棣、西渡的选本的承接和衍生。因为又过了20年,原来的诗人有了新作,也不断出现优秀的后继者。在这个喧嚣的消费时代,校园里的诗歌情热并未冷却,仍赓续繁茂,这让人感动——
它们是真实,宏大的。对短暂,激荡而易于疲惫的生命
它们恒久,平静,始终如一的饱满精神,是长存的抚慰。
在人们提起校园诗歌的时候,时常有一个悖论性的思索——“北大诗派”是否存在。诗人臧棣、西渡都不承认有“北大诗歌”的说法,这种拒认,部分原因是担心它被混同于“校园诗歌”,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诗歌史的考虑,而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最简单:任何诗人都只承认他们献身于诗歌,而不是臣服于带有地方性或群体性的归类概念。诗人胡续冬认为,一代代人的精神境遇迥异,在诗歌和诗歌之外的维度上面对的问题和用心无法简单通约。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并没有什么所谓北大诗歌传统可言。
但另一方面,大多数来自北大的诗人们也强烈地感到,在“北大诗歌”这一名称里很可能归结了某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当代诗歌的许多变化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阳光打在地上——北大当代诗选(1978-2018)》成书的目的,大概就在于,在阳光打在地上的片刻,拾回一段时光——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00年代——徐钺:每首诗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趋向一个单一的风格,我们在交流中仍然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阿吾写青春荷尔蒙,我不会写,但是我欣赏他。个人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尊崇思想的多元化,认同着对方,保持着自我。” 作为00年代的代表诗人,徐钺回忆自己在北大写诗的那些日子里,遇到的志同道合的人。
2001年进入北大计算机软件系,抱着一颗当“码农”的心重复着日复一日的习题课,后来出于对诗歌的热爱转入中文系,在百讲旁边看到“五四文学社”的社团招新,想起小时候父亲给自己做草稿纸背后印的诗歌,在小学为了偷懒减少字数交给老师的“处女作”,中学时代为了追求女生把诗歌当成一种工具,高中时代陆陆续续读了《太阳日记》产生的冲击,忽然觉得小时候一些懵懵懂懂的想法,在成长后会显得更加深刻。于是他加入五四文学社。但因为不参加社团活动而渐渐淡出。2005年,一堆爱写诗的人又窜在一起办诗会,这让他再次和诗社产生了连线。
每周徐钺都特别期待晚上和一群写诗的挚友们聊诗歌。北大静园5院,一群人,大冬天蹲在外面烤火,吃宵夜、聊诗歌。“当时因为天天吃宵夜,体重也飞速增长(笑),而伴随的也是整个人的飞速增长。总需要有人在旁边,和你一起,看你的成长。”
北大诗歌传统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从事青春期写作的初学者,往往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获得诗人的情谊和诗歌的进步,如姜涛所说:“学生时代总觉得身边的人写得好,这种心态很正常,所以你取悦的主要读者是身边的人,你最欣赏的人评价你,你就特别高兴。”这种交往既包括喝酒吃饭谈天,也包括由五四文学社、《未名湖》刊物、未名诗歌节和诗歌课堂等构成的切实存在的交流空间和平台。大家都想要互相进步,都愿意有一个交流,这是一个群体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的进步。
2002年,诗人雷武铃博士毕业,一年后,他写下《冬天的树》:“从温暖,明亮,深邃的书中出来/正是最迷乱的时刻:公共汽车轰鸣/车灯,路灯,橱窗灯交织的浮光与暗影里/漂浮着表情模糊,行色慌忙的人。”身处校园的写作者沉浸在知识和诗歌中,感到价值稳定,人生被光明照亮。“但一旦离开校园,离开诗歌,就陷入混乱。每首诗要回答你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迷惘。”
徐钺想要开始练出自己的绝活,疯狂阅读、疯狂打羽毛球。在和胡续东打羽毛球的日常中,也更深入地了解了90年代北大的诗人、时代和梦想。
90年代——胡续东、冷霜: “这些传奇而意外的经历,都是写诗带给我的”
“我不把自己放在“北大诗歌”这个框架性的语言,但是我很感谢这样的氛围带给我的改变。他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诗歌,更是一个2.0版本的改变。”胡续东说,在中学时代他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作为边缘小城暴力群首,孤僻,不善言辞,但是在智力上的有一种莫名的自负。 “当时我认为朦胧诗对我的智力不构成挑战。”当时他更喜欢读小说,马尔克斯、约瑟夫·海勒……
1989-1992那个时代的学生,都得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当时胡续东正偷看,旁边的哥们随手仍过来一本西渡编的《太阳日记》。“读完这《太阳日记》,我看着海子、骆一禾、臧棣的诗歌,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1992年9月进校第二天,我在三角地看到一张粗糙的海报上有8个字‘自得其乐,愿来就来’,是冷霜他们在为五四诗社招新,我觉得这简单粗暴的风格符合我这人性格,就风风火火冲去报名。他们的侃侃而谈让我觉得找到了组织。我隐隐觉得这是我可以触及的,但还没有拥有的东西。”
冷霜当时读《启明星》(北大的校园刊物),受到其中诗歌的影响很大,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脉络中。虽然每个人的起点不同,但是这种共鸣让人觉得你是置身在一个历史序列之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我如果能在《启明星》细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那可以说是很满足了。”
当年冷霜、胡续东等一大堆人,写诗、聊天,结交了一堆挚友。“写诗的人当时已经算是一个边缘的群体,但是我们之间会一直有一个交流。虽然现在看来很多当初写诗的人已经转行,但是他就如一座休眠火山,随时都在积蓄力量。其实很多人都在自己继续着,保持着自己的初衷,延续着自己的爱好。这也算是校园诗歌的魔力吧,温水一样,低调而持久。”
戈麦去世一周年的活动,对于胡续东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节点。“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从小仰慕的人。臧棣就像柏拉图,在正中央讲学;西渡就像亚里士多德,一幅现实版的《雅典学院》呈现在我这个小城暴力少年脑海。”但看到现实版的偶像时,胡续东却觉得和自己想的很不同。西渡小小的个子穿着空大的衣服,臧棣像《雷雨》里的公子哥周萍,油光满面;西川来的时候更震惊挎着个大包,一点也不像写《起风了》这样的诗的人。这一见打破了他们身上的偶像光环,胡续东觉得这群人,挺亲切。“正是这群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给了我太多的力量,让我的人生渐渐改变。我从一个社交恐惧症变成了一个善于沟通的人,我现在想来,这些传奇而意外的经历,都是写诗带给我的。”
80年代——西渡:写诗当时有一种“伦理承担”
西渡回忆道:“1985年我入学,正值朦胧诗从鼎盛走向衰落,第三代诗歌兴起。我拉着板车在学三食堂门口买当时出的诗歌选集,想加入北大五四诗社被拒绝,当时我很沮丧。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丢一个石头,砸出一个诗人。当时大饭厅座无虚席,大家都在听诗歌。慢慢到后来,现代化使得这样一种狂热慢慢冷却,后来去能容纳800人的教室,刚好坐满。在90年代最衰弱的时候差不多文史楼一个教室就可以。”诗歌的变化也可以作为一个切口,窥见时代的剪影。
1985年,22岁的西川常和五四文学社的一群人去圆明园找一块空地,围个圈子朗诵诗。在北大文化部小院的咖啡厅,他写下长诗《雨季》。“我所预言的都必实现,/我要你做的事你定要完成,/在高天之上我将注视你,/在我的卧榻之上我将注视你。/你要欢乐雨水给予,/你要生命雨水滋养,/你要我的祝福,/就请你时时念起我的名字。”这首霸气外露的诗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十月》,并得了“十月文学奖”,当时的编辑是骆一禾。
西川毕业之际,大学二年级的诗人西渡与四五位写诗的朋友第一次在中文系刊物《启明星》亮相,大三的另一位诗人清平为他们写了评论,对西渡鼓励有加。西渡回忆:“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因为写诗而结识的。”
差不多十年后,29岁的女诗人周瓒博士一年级,选了北大教授戴锦华的影片精读课,课上讨论的是费穆的《小城之春》和基耶夫洛夫斯基的《蓝色》。当时,周围写诗的朋友们正在进行关于纯诗的讨论,她以课上的艺术文本为基础创作了《影片精读十四行组诗》作为对讨论的回应,技惊四座。多年后,她亲身参与起了剧场活动,周瓒念起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无限地扩大着自己的生命,你等待又等待这独一无二的瞬间”,以铭记在北大写诗的日子。
西渡谈起骆一禾、海子等前辈,感叹当时北大诗人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对于骆一禾来说,写诗不是为了获得“诗人”的称号,而是与中国“文化复兴”命运紧密连接,是一种宏大抱负,恢复诗歌在创始阶段的极高作用。最早的1918年,《新青年》开启了白话新诗的头,从此诗歌和北大有了持久的缘分;1992年,活跃的诗人反映在公众的视野……从1916年来,北大走出的诗人的一代一代人也映衬着中国诗歌的脉络。
正如《希腊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对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诗歌缺少系列性的鸿篇巨制,能够凝聚民族精神。骆一禾认为,诗歌要有一种全新的改观,是担当着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作用的。那种雄心和抱负,令我们钦佩。新诗历史上前辈做出的尝试,虽然后来我们可能没有完全继承他们的道路,但是这种情感和伦理道德还是潜移默化影响着北大诗歌的气质、对社会的关怀。
西渡的时代是慢的,很多人都在“熬时间”。每天很轻松做完一天的工作就开始很闲。而在他眼中臧棣却很忙,每一天都在想着要去写诗歌。他把诗歌当成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最重要的部分。他说,不要迷信灵感这种东西,写诗是一种自己能够调节自己智力的影响状态,自己想写就能写。而戈麦则偏爱按计划写作。就像一个工程师一样,有一个蓝图,然后一步一步实现它。在那样一个年代,写诗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待灵感的爆发,而是一种主动地创造。
这种写诗的态度,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生活的态度,让人感动,同时也影响和塑造了北大诗人们一个共通的气质——青春、锐气、自由,这些北大的气质,也是时代的气质。
在一个微观的时间序列中,这40的变化很明显。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风格、特性和追求;但是若把时间放宏观的时空来说,这就是一个整体。在100年、1000年后看来,这40年来来往往的人,又会被放到一个时代中,1978年到2018年也会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时代周期被记住。在40年里,北大作为中国思想嗅觉最敏锐的高校之一,也可以回望四十年来反思走过的路。
说“北大诗歌”,并不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和群落的划分,而是一种同一场域下不同时间的群体的互动,他们各有特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文学的相通性,共同的血脉。
正如徐钺说的,“北大诗人”只是一个空间上的概括,只是一群人恰好在这里留下印记,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束缚每个人的特点,也不会因此排斥其他的诗歌。正如打野球一样,在某一个时间,我们可能就在一个场域上。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都一样,我们各有各的打法,但是我们能够配合在一起,并且大家打得开心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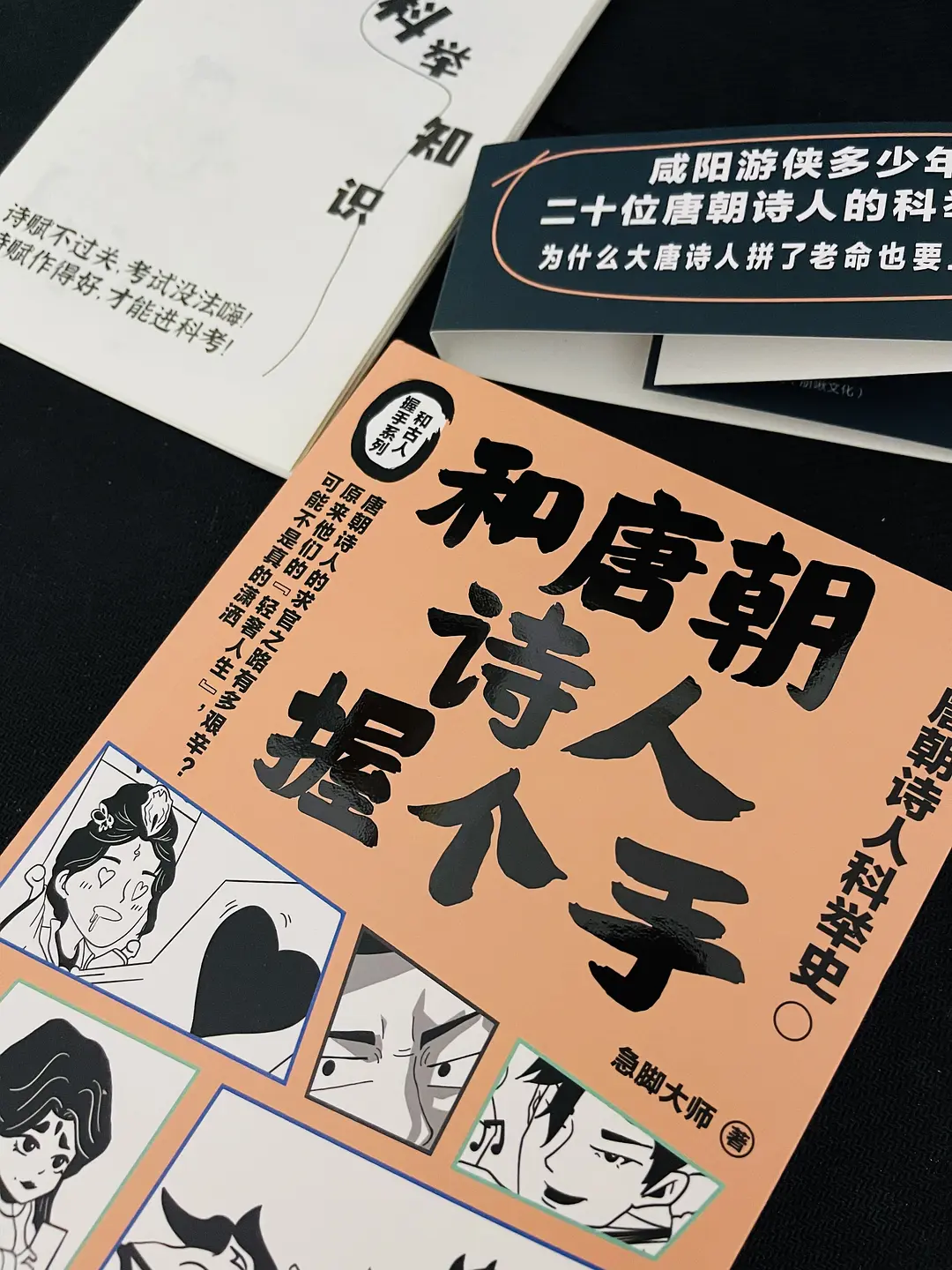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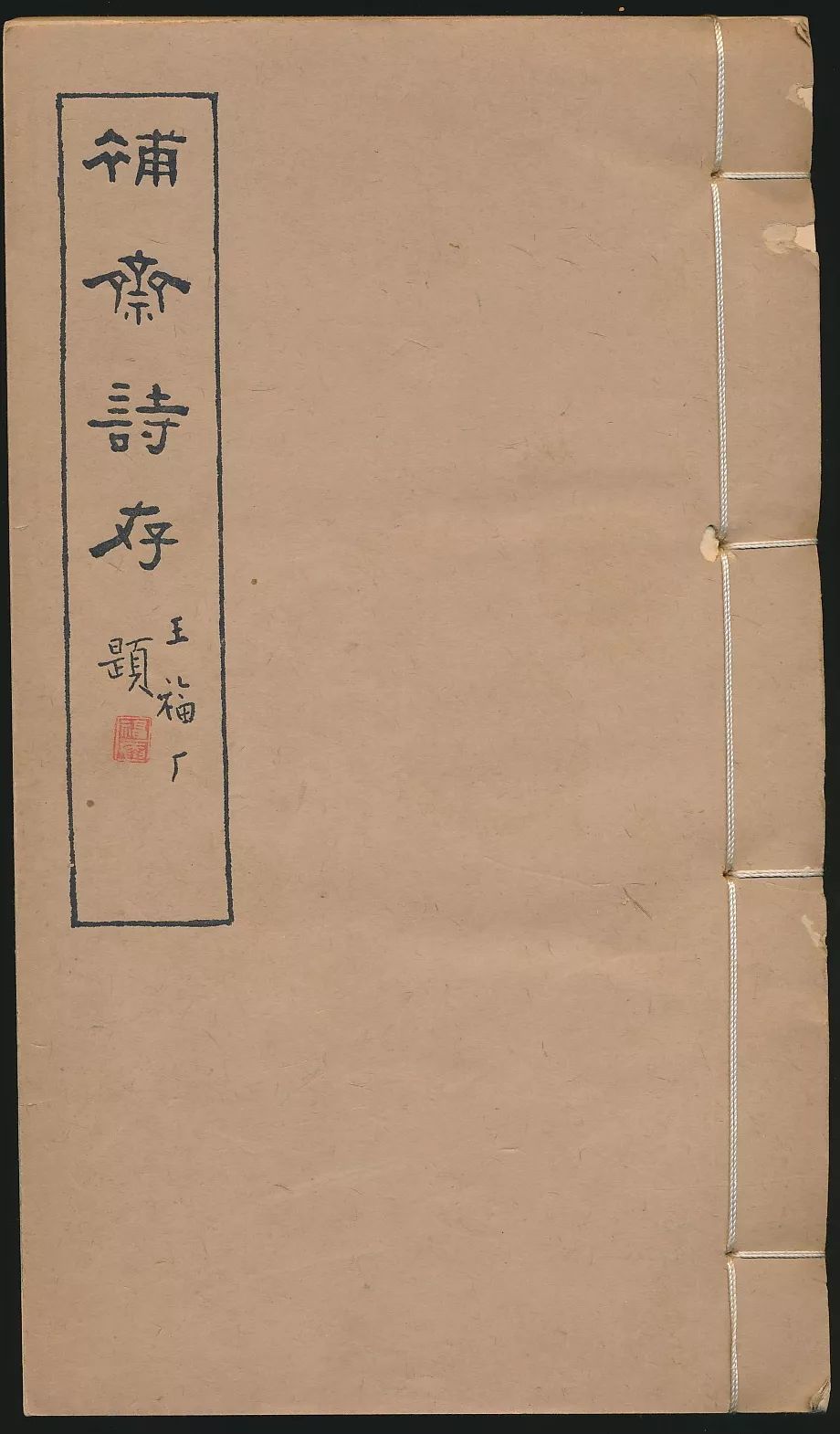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