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两千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渐形成一门学问——“史记学”。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的传播与初步研究时期,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文学史上的双重地位,宋元明清以来,《史记》的传播范围日益广泛,接受的群体不断扩大。这种局面的出现,都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廖可斌、陈文新、赵望秦三位教授的文章,揭示《史记》与明代文学发展的深层原因,探讨科举考试与《史记》之间的关系,阐述出版技术尤其是印刷术的发展对《史记》传播的重要作用。三篇文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不同的文化因素对《史记》传播与接受的影响,我们由此也可以对《史记》的魅力和生命力有进一步的认识。(张新科)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明初洪武年间的情况与永乐以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朝初年的文化还多少遗留了一点元代文化相对多元和自由的风气。当时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宋濂、刘基等为代表的“浙东派”文人,他们在学术渊源上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开创的理学门派“北山学派”的传人,其文学主张自然以“明道”“征圣”“宗经”等为宗旨。“浙东派”因较早追随朱元璋集团而成为明朝的开国文臣,依托其政治优势,他们的这套主张自然也成为明初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但“浙东派”文人毕竟不是纯粹的理学家,而是兼理学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于一身。因此他们不同于理学家“轻文”甚至“废文”的态度,而是比较“重文”,其理想目标是“文道合一”,以至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北山四先生学案”的“按语”中批评他们“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他们既然重文,就不可能不关注作为古文之崇高典范的《史记》。如宋濂一方面声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一方面又赞同唐子西的说法:“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班固。六经不可学,学文者舍迁、固将奚取法?”在《叶夷仲文集序》中他再次强调:“昔者先师黄文献公(溍)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
及至永乐年间,经过朱元璋、朱棣父子高压政策的摧残,社会思想文化更趋封闭保守。在文学领域,以歌功颂德、宣扬程朱理学为职志的“台阁体”应运而生。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将取法的主要典范,由《史记》《汉书》转移到唐宋八大家之文。解缙是“台阁体”前期的领袖人物,其散文创作受《史记》影响甚深,连“台阁体”后来的代表人物杨士奇也认为他的文章风格是“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处逼司马子长、韩退之”(《解先生墓志铭》),但解缙在《廖自勤文集序》中却认为,学文只能学六经,像庄周、申不害、韩非、贾谊等人之文,“非惟不足经天纬地,而且有害焉”;“近世为文者尤甚患此,反从事《史》、《汉》、《战国》、百家方外之书,剽窃奇漏,纵横腐败,神鬼荒忽,极其镌巧形容,以为此古文也。论及性理则以时文鄙之,援及《诗》《书》则以经生目之,是将为天地人心世教之害,有不胜言者,此予之所甚忧也……予厥后稍喜观欧、曾之文,得其优游峻洁,其原固出于六经,于予心溉乎其有合也”。在“台阁体”的中后期,由于明仁宗的提倡,和作为江西人的“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推动,模拟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江西籍作家欧阳修、曾巩的文风成为时尚。
兴起于明中叶弘治年间的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复古派“前、后七子”提出了“文法先秦两汉,诗学汉魏盛唐”的主张,打破了文坛的沉寂,开启了明后期文学革新思潮的先河,是明代文学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在散文方面,复古派作家取法的主要对象就是《史记》。现在可见的《史记》在明代的最早刻本,是正德十二年廖铠序刻本,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由“前七子”的重要人物康海主持的。因廖铠系镇守陕西的太监廖鸾之从侄,而康海《对山集》中有一篇《史记序》,与署名廖铠序基本相同。复古派作家不仅学习《史记》的叙事、描写、抒情的技巧,模仿《史记》的章法、句法、字法,也力图继承《史记》思想相对自由、感情充沛、文气跌宕起伏、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特点。但由于他们取法的对象过于单一,手法过于机械,难免暴露出模拟的痕迹。如“后七子”中的宗臣留下了一篇《读太史公、杜工部、李献吉三书序》,反映出他一生阅读和取法的文学典范可能就是《史记》、杜甫诗集和复古派“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文集。他所写的文章,每篇的开头语几乎都是同样的句式,如:“余尝往来齐鲁燕蓟之区”(《赠金君序》);“余稽往牍,抽绎千古,睹于群才,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晋陵白公集序》);“余读金陵诸记,其东盖有燕子矶云”(《燕子矶记》);“余读汀记,归化东北五里,盖有滴水岩云”(《滴水岩记》);“余读秦汉以下诸书,未尝不叹戎狄之为中国忧至长也”(《桐乡县城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都是在模仿《史记》的句法。
当时与复古派对垒的,有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所谓“唐宋派”。他们最初都是复古派的追随者,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曾努力模仿《史记》。如茅坤自述“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怛悲凄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后来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启发下,热衷于探讨理气性命等心学问题,讲究说理、语言相对接近的唐宋古文模式比较适合表达他们的思想,于是他们自然改变了取法的对象。如王慎中“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尽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悉出入曾、王之间。唐荆川(顺之)见之,以为头巾气。仲子(王慎中)言:此大难事也,君试举笔自知之。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至于在后世享有盛名的归有光,近代以来人们往往把他归入“唐宋派”,其实他在当时文坛上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一直注意学习《史记》,几乎终生未改。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宗尚发生转变后,不仅对自己从前学习《史记》等秦汉散文表示悔恨,而且反过来对复古派作家模拟《史记》等提出批评。如“唐宋派”的追随者蔡汝楠就责难“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专门学《史记》,“屈曲逐事变,模写相役”(王世贞《赠李于鳞序》)。当然,“唐宋派”作家对复古派作家学《史记》表示不满,并不仅因为在写作技巧方面有分歧,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司马迁和复古派作家的思想比较自由,不完全符合正宗的儒家学说。在这一点上,“唐宋派”的羽翼薛应旂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何(景明)之言犹或近于理道,李(梦阳)则动曰‘史、汉’‘史、汉’。一涉于六经诸儒之言,辄斥为头巾酸馅,目不一瞬也。夫‘史、汉’诚文矣,而六经诸儒之言,则文之至者。舍六经诸儒不学,而唯学马迁、班固,文类‘史、汉’,亦末技焉耳。何关于理道?何益于政教哉?”(《遵岩文粹序》)
勃兴于晚明的文学革新思潮,倡导个人性情的自由表达,与《史记》所代表和复古派所追求的古典审美理想有本质区别。代表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在散文创作方面成就的是小品文,不再以《史记》为主要取法对象。从语言形式等方面看,它们与唐宋古文的因缘相对要深一些。明清易代之际,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重倡“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艾南英等人则再次为唐宋八大家辩护,两派之间曾发生激烈论战。至于在小说、戏曲领域,《史记》的影响也很深远。许多小说、戏曲作品都以《史记》的内容为题材,都借鉴《史记》的艺术技巧。戏曲、小说理论家也往往以《史记》为典范,探索叙事文学的内在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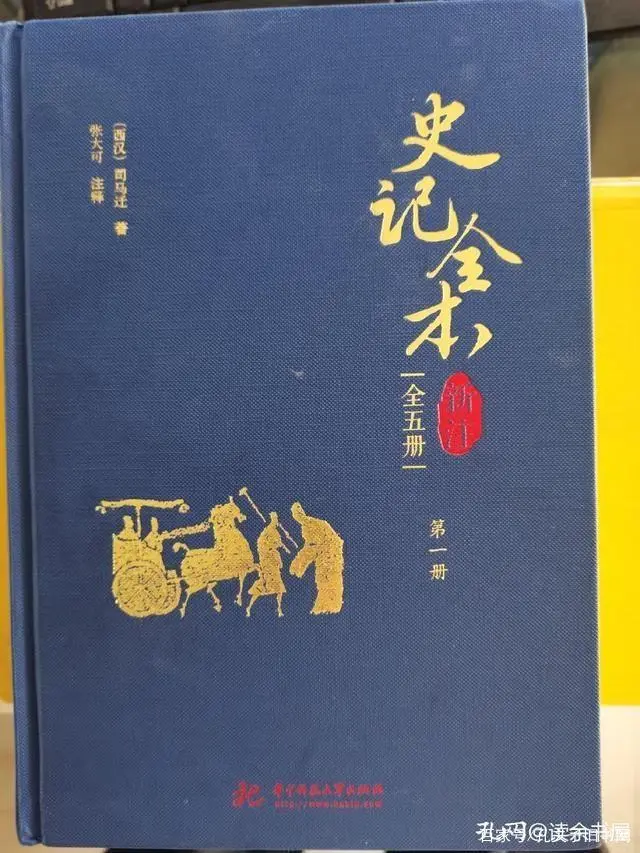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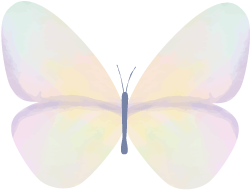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