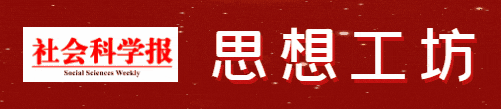
诠释
随着教育部学科目录的调整,艺术学的理论建构可以被置于以艺术学为中心、以跨学科研究为情境的具体展开中。其中,对艺术理论与历史意识研究的综合考察,或可作为当下艺术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参考。

原文 :《艺术理论与历史意识研究的跨学科视角》
作者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陈书焕
图片 |网络
设计学视野中的艺术理论
随着“设计学”从“艺术学”目录中独立出来,设计学开始成为一个交叉学科,它对艺术理论与历史意识问题的关注呈现出一种新的跨学科视野。在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艺术学名词审定中,不少设计学领域专家的加入是一大亮点。相对于艺术学研究,尤其是其中艺术史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设计学研究,或者说其中最先确立的设计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是在20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高校发展起来。在设计学研究者对设计史方法论的思考中,艺术史理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艺术史作为设计史的遗产来源、比较对象或者批评靶子,如在法兰(Kjetil Fallan)的《设计史:理解理论与方法》、沃克(John A. Walker)的《设计史与设计的历史》中都有明确的体现。设计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如《设计史期刊》(Th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设计问题:历史·理论·批评》(Design Issues: History · Theory · Criticism)均有相关文章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并大多结合具体设计史家的个案加以展开。
在上述研究中,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是被论及最多的设计史家之一。作为德语艺术史传统的继承者,佩夫斯纳在20世纪30年代移居英国以后逐渐转入建筑史和设计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英国建筑史和设计史后续学科建制的基础,其著述如《现代运动的先驱者》《欧洲建筑史纲要》《英国艺术的英国性》在艺术史、建筑史和设计史研究中有着深远影响。佩夫斯纳在其写作中贯穿了他对过去和当下、英国和欧洲大陆、设计和艺术之间历史相关性的自觉思考,并以杂志《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为阵地,尝试把英国美学传统中的“如画”理论实践性地运用到20世纪的城市、园林、建筑规划与公共设计领域。当代园林史家亨特(John Dixon Hunt)肯定了佩夫斯纳这一做法的有效性,但佩夫斯纳的学生、建筑和设计理论家班纳姆(Peter Rayner Banham)则予以激烈批评,认为这是现代主义和过去的不必要妥协。
在近年的设计学学科属性探讨中,设计与艺术之当下和过去的关系以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展开,其旨向在于设计学相关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再思考,其中既包括艺术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对设计学研究的启示,又包括设计学研究对艺术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观照。在该探讨中,设计理论家布坎南(George Richard Buchanan)把设计看作一种公共性修辞,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关联起来,而马格林(Victor Margolin)则把设计史的历史观念纳入到更为普遍的历史观念架构中,以艺术史领域的世界艺术史写作为参考,进行世界设计史的写作。在此意义上,设计学相关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再思考,为艺术理论和历史意识研究的当下面向,提供了一种视域交织的在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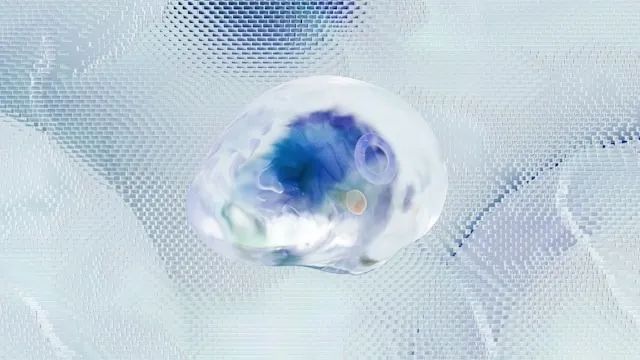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艺术理论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指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他主要引用了二十世纪著名比较文学家韦勒克(Ren?? Wellek)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说明目前新文科体系中艺术学理论建构的迫切性。实际上,在比较文学和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宏观架构内,除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如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可以作为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参考,在具体问题的考察方面,比较文学研究对艺术理论也有着切近的关注。韦勒克在比较文学领域的经典著述,尤其是以文学批评为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著述,如《近代文学批评史》《批评的诸种概念》《辨异》,其中对文学批评的时期、风格、概念的考察,和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研究中对相关时期、风格、概念的考察有着自觉的理论呼应或者文献索引相关性。以文学研究中的“巴洛克”概念为例,韦勒克指出,艺术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确立了“巴洛克”概念在艺术史上的意义,而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把“巴洛克”概念从艺术史领域扩展运用到文学领域,他把“巴洛克”作为与“文艺复兴”并列的一种主要风格的分析,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理论推动。
除了以比较文学为专门领域的学者(如韦勒克),还有不少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为专门领域的学者,在具体研究中也注意考察相关批评概念在文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中的沟通。这些学者实际上是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关注艺术理论的进展,这方面具有影响力的代表学者如布鲁姆(Harold Bloom)、德曼(Paul de Man)、米勒(J. Hillis Miller)对19世纪批评家如罗斯金、佩特、尼采的研究。著名文学批评家科莫德(Frank Kermode)在其《关注的形式:波提切利和莎士比亚》一书中,直接以标题的形式点明了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在理论概念与阐释方式上的历史相通性,二者共同面向这一问题:“我们以何种方式赋予艺术作品价值,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如何影响我们关注它们的方式?”科莫德以艺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个案——波提切利在19世纪的“重新发现”为例,指出由于某种特定的现代敏感性,批评对波提切利所形成的“意见”作为一种舆论,真正奠定了波提切利的声名,并引导了后续诸多艺术史家更为全面而深入的对波提切利的知识性研究。
在此之外,视觉文化研究学者米切尔(W. J. T. Mitchell)和上述比较文学学者韦勒克、文学批评学者布鲁姆和科莫德等人一样,具有比较文学视野,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以布莱克(William Blake)为重点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但和上述学者不一样的是,米切尔同时在英语系和艺术史系任教,其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研究倾向更多是在视觉文化层面,这从其众多关于图像研究的著述(如《图像学》《图像理论》《风景与权力》)可以看出。从布莱克作为诗人、画家的综合艺术创作,到当代图像研究的多重面向,米切尔在其中贯穿起了历史意识在媒介表达层面上的复杂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视觉表达和话语表达的关系,这些都是在一以贯之的比较视野下进行的。米切尔还主编了享有盛誉的《批评理论》(Critical Inquiry)杂志,致力于艺术学和广泛人文学科的批评理论研究。在此意义上,基于历史意识在批评层面的共存共通,艺术理论有望在比较文学的参照下拓展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史学理论视野中的艺术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对艺术理论在历史意识层面的关注,主要围绕视觉艺术不仅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还作为历史写作的隐喻性启发而展开,其中又以对绘画艺术的探讨为主。何兆武、陈新等国内学者在相关文章中指出,历史学不仅作为科学,还作为艺术,因此需要注意发掘历史写作中的艺术性要素,注意考察艺术理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在这方面,20世纪西方著名史学理论家怀特(Hayden White)和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怀特在其论文《历史的重负》、专著《元史学》、论文集《话语的转义》等著述中注意到绘画艺术的修辞性力量,并以布克哈特的艺术史写作风格和当时的印象派画风之间的相似性为例进行说明,指出历史写作的模式并非只有以19世纪小说为典范的故事性叙述,还可以有以现代艺术为典范的绘画性表现。怀特的倡议在历史写作和艺术史写作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当下和过去的关系,即不仅“叙述”过去,而且以新的眼光“看”过去,以此重新“写作”历史。在受到怀特直接影响的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中,卡里尔(David Carrier)和霍利(Michael Ann Holey)是重要的两位,前者的《艺术史写作原理》、后者的《回视:历史想象与图像修辞》对怀特的观点多有借鉴。
如果说怀特启发了一种回头“看”历史的史学思考,那么安克斯密特则旗帜鲜明地提倡一种历史表现中的“图像转向”,并分析历史文本图像化相对于历史文本文学性的优势。对图像的重视是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契机,其中,“表现”“经验“等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以图像为参考建构的历史理论关键词。其论文《陈述、文本和图画》可作为该主张的一个明确而集中的代表,以此尝试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的考察,其中,视觉艺术被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型。其专著《历史与转义》《崇高的历史经验》则是该主张在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展开。在安克斯密特关于“图像的转向”的历史表现理论中,对风景画和画框的讨论是与艺术理论最为相关的部分,风景画作为扩大了的画框之新的中心与历史写作的进展隐喻性地关联起来,而画框的生成性意义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艺术表现对历史表现的切近理解。
综上所述,艺术理论和历史意识的关系是综合人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一方面,这是艺术学在历史意识层面对设计学、比较文学、史学理论的开放;另一方面,这也是设计学、比较文学、史学理论在历史意识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的参与,二者内在于一种相对面向的关系之中。该论题的展开将有助于推进艺术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论建构,以及跨学科视角下的综合历史意识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世纪英国艺术批评理论和历史意识研究”(20BA016)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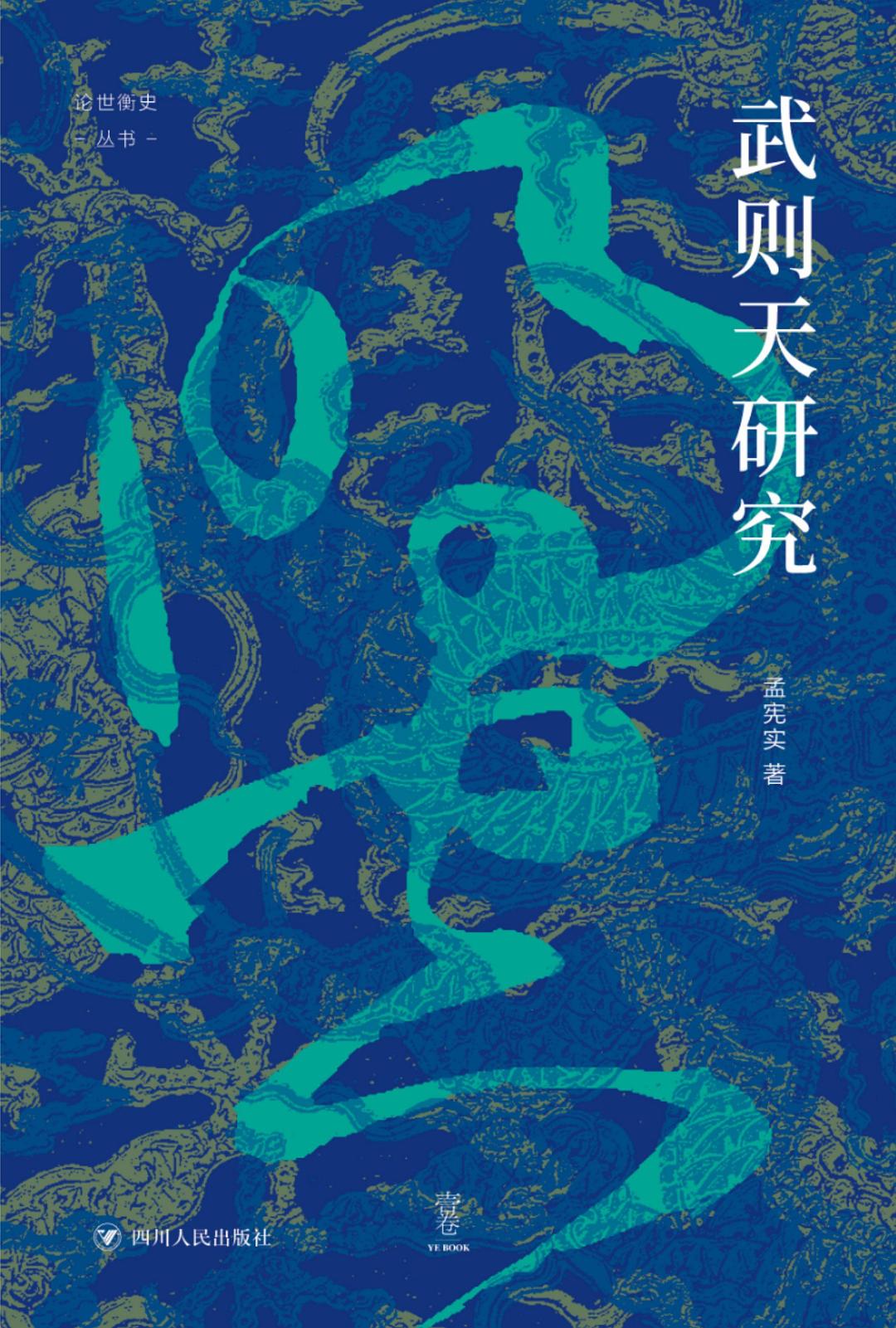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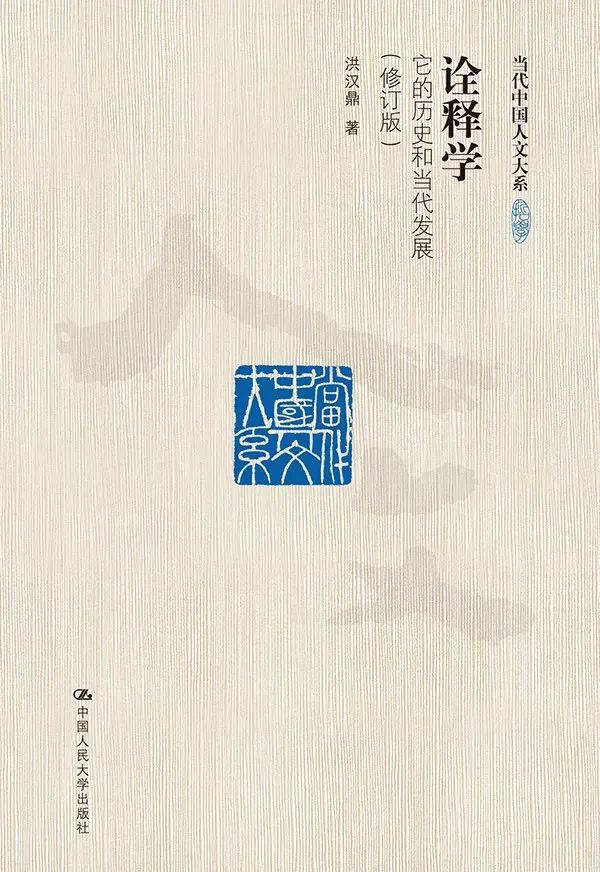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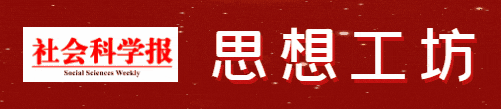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