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本《道德经》第十九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中的“绝”“弃”二字,是同义并列关系,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断绝”“舍弃”之意,而不是要留下“圣”“仁”“巧”,而舍弃掉“智”“义”“巧”。
但有不少人,至少从清代全真道士李涵虚之后,对上述“三绝”“三弃”的解读就陷入了留一半、弃一半的死胡同,他们将“绝”理解为“至”“极”,“绝圣”“绝仁”与“绝弃”三个词语,就是极其圣明的圣人和至仁、至巧之人。而《道德经》要表达的本意是:圣、仁、巧,跟智、义、利一样,都是要“绝弃”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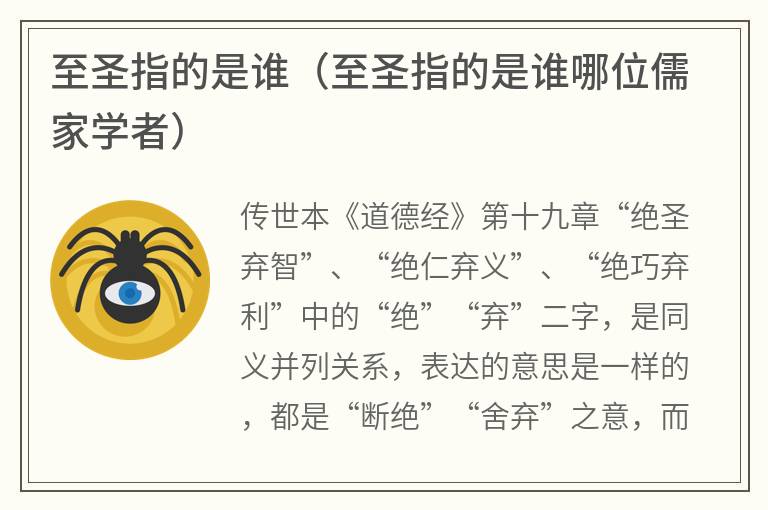
至圣指的是谁(至圣指的是谁哪位儒家学者)
出现这么对立的理解,问题在于对“绝”的理解上,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解读者的主观愿望,具体说来,就是用先入为主的儒家思想套解老子思想造成的。
“至圣”一般是指道德智能最高而超脱凡俗的人,有时特指孔子,比如“至圣先师”就是孔子的专属称号。而《道德经》中的圣人跟儒家所说的道德智能圣人不是一回事,而是老子塑造的一个文化图腾,是“道”的化身,他不具备道德教化的职能。
魏晋玄学家试图打通孔老思想,遂以《易经》中的“圣人观”来协调孔老两家的“圣人观”。而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等人,均是当时大儒、经学家,他们认为“老不及孔”,因此在解读《道德经》时,难免以儒解道,以孔解老,将老子思想“玄化学”,以削足适履于儒家学说。这一学术风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至深至远,从魏晋到南北朝,再到两宋理学,直至今天,仍影响深远。
在此强大玄风的裹挟下,即便是三教合一的清代全真道士李涵虚,也难能跳出以儒解老、以佛解老的窠臼,他对“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做出的解读,迎合了部分儒释道圆融的老子思想研究者。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其大意简言之就是:君主抛弃神圣化的道德说教、仁义的粉饰以及利益诱惑的手段,民众会有更多的利益,会回复孝慈,盗贼会自然消灭。
李涵虚的全章解读却是这样的:
绝:大也,又至也。至圣不用智,风尽敦庞,民多利益矣。至仁不用义,俗尽亲睦,民归孝慈矣。至巧不谋利,谋利者,皆机巧之徒。上无机巧,下无盗贼矣。圣不足于智,仁不足于义,巧不足于利。圣、仁、巧三者,若有质而无文也。浑浑噩噩,一道同风,故使民各有攸属,亦从其质实而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民之文亦不足也,然而美矣。
李涵虚的解读,以儒入道,先入为主,割裂了老子“尊道贵德”思想。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只有“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接下来的“上仁”、“上义”、“上礼”都属于“为之”的,从《道德经》的思想体系来看,从“德”到“礼”是渐次递降的,因此老子总结说:“故去彼而取此。”就是要舍弃掉“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而归之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而李涵虚把“道”“德”之后的“圣”“仁”“义”提高到与“道”并驾齐驱的地位,把施政行为的“巧”理解为“至巧无巧”而“不谋利”,这与老子“以智知国,国之贼也;以不智知国,国之德也”的反权谋伎巧的思想截然相反。
同时,李涵虚把“绝”“弃”二字肢解开来,把本来并列且表示决绝的两个动词“绝”、“弃”二字独立出来,分别当作形容词和动词来用,造成该“弃绝”的“圣”、“仁”、“巧”,反而成了被赞扬的“至圣”、“至仁”、“大巧”。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绝圣弃智”不是司马志先生理解的“废弃通达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也不是刘新升理解的“至上圣人无需动用智慧”。必须注意:老子不反智、也不反文明。
提供几个参考注解。限于篇幅,仅以“绝圣弃智”为例,并附上作者对个别注解的点评。剩下的两句参照该句来理解。
唐玄宗:“绝圣人言教之迹,则化无为。弃凡夫智诈之用,则人淳朴……”——对于“绝弃”的理解正确,但他把针对君主的三绝三弃理解为“君”与“凡夫”二者,其余两句则分别指向“人”,明显是逃避作为君主的责任。
宋徽宗:“圣智立……则圣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绝而弃之……其利博矣。”
苏辙:“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也。”
即便是玄学家王弼的注文,也是把“绝”“弃”作为同义词来理解的:“圣智、仁义、巧利……而直云绝”。
《道德经》原文中的“圣”与“智”对举,“仁”与“义”对举,“巧”与“利”对举,其态度毫不含糊,“三绝”“三弃”,就是要“弃绝”掉圣智、仁义和巧利。
在《道德经》思想里(指编著者的思想,不一定就是老子的思想,下文将简单对比),老子主张“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反对“多言数穷”的教化约束和“法令滋彰”的强制施压,而这些都是传统教化中的“圣人”所为。故庄子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制礼作乐,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是传统教化中的圣人,以至于孔子几日不曾梦见周公,就感慨大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很显然,以周公之碌碌,不可能是《道德经》中的为道“无为”的圣人。
以上说的较多的是“绝圣弃智”方面,下面再探讨一下“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与“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上文已经说过,“圣智”“仁义”“巧利”都属于被“绝弃”之列。为什么说“绝仁弃义”,会“民复孝慈”?因为“孝慈”纯属家庭私事,孝慈是亲情,是天性,是自然而然的人伦关系。而一旦施行仁政,权力势必会干预家庭私事,将自然天性纳入礼教规范来管束教化,将自然天性标准化、程序化、教条化。
而“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要绝弃掉“巧”“利”,是“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伎巧”,是“民多利器,而国家兹昏”的“利”,是国君绝弃敛财之欲,奢糜之行,国泰民安,盗贼不生。
战国出国出土的简本《老子》恰好有传世本《道德经》这一章,其内容跟传世本《道德经》相差很大,主要表现在“三绝三弃”上。楚简本《老子》的“三绝三弃”原文是:
传本的“绝圣弃智”在楚简本《老子》里成了“绝智弃辩”,“绝仁弃义”变成了“绝伪弃虑”。
且不说传本与楚简本那个更接近老子思想,可以肯定的是,楚简本《老子》的出土,在帛书《老子》之后,又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直通老子思想的方便之门。
就文字来看,楚简本是一般地批评世俗价值,而传本是直接地否定儒家的基本思想。学者们,比如裘锡圭、庞朴、刘笑敢等人认为,《老子》版本有一个从楚简本到帛书本,再到傅奕本和河上本、王弼本逐渐演变的过程。
这种演变的文本证据就是,越是股本越是没有分章和标题,越是近本,标题越来越规范;虚词减少,四字句增多;自由舒缓的句式减少,急促加工的句式增多;散文化的句式减少,整齐化的句式增多;以及批儒成分由少到多,由一般性批评到尖锐批评这样的一个编校过程。
楚简本《老子》大约抄写于公元前300年前后的战国时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抄本,文本中的“绝智弃辩”“绝伪弃利”是对普通社会普通价值的批评。而传本《道德经》则是“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很显然,针对的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因此专家们推断,包括帛书本在内,可能都是战国中期受儒道之争影响的黄老道家们编校、加工的,因此加大了批儒力度,形成了后世的传世本《道德经》。
因此,读懂老子思想,还是要主攻一本,兼顾他本,以老解老,旁涉诸家。切不可先入为主,固执己见,盲人摸象,贻笑大方。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