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父与巢山
方克逸
巢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巢山则是一座鲜为人知的名山。
第一,我所认识的巢父
首先,巢父是一个传说人物。

安徽省巢湖市巢山雄姿
巢父是唐尧时期的一个隐士,或曰传说人物。《辞海》释“巢父”词条:“古代隐士。相传因巢居树上得名。尧要把君位让给他,他不受。尧又要把君位让给许由,他又教许由隐居。”《辞源》释“巢父”词条:“传说为唐尧时隐士。在树上筑巢而居,时人号曰巢父。尧以天下让之,不受;又让许由,亦不受……”198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共收词条四千多条,计3755人。其中远古时期收入盘古氏、有巢氏等26人,许由、巢父在列其中。其释“巢父”词条:“古史传说中隐君子。与许由同时……”上述权威辞书有一个共识,结论便是:巢父是唐尧时期的一个传说人物。至于巢父是哪里人,谁也没有表述。
这并不奇怪。传说是由神话演变而来但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故事。若将这种故事的主人公以史实记载下出生年月日和出生地,那才奇怪呢。
通常传说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年代遥远的过去。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人们要对历史做纪录只能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巢父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信众而名垂青史的传说人物。
其次,巢父、许由是一对孪生兄弟。
《辞海》、《辞源》和《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等辞书在收录人物词条时,都将“巢父”、“许由”同时记载,二人事迹互为印证。
巢由人物最早出现于《庄子•逍遥游》,说的是尧想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拒绝。理由是“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鹪鹩又名巧妇,俗称为山蝈蝈,一种善于筑巢的小鸟);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鼹鼠,即田鼠)”,我有这么多就够啦,要天下做什么呢!?《吕氏春秋》在《逍遥游》的许由故事上,增加了“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晚,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的内容。巢父人物则稍睌出现于晋代皇甫谧《高士传》:许由在发表了“鹪鹩鼹鼠论”后逃尧隐居,尧又召其为九州长。许由一听,就跑到颍水河边去洗耳朵。他的朋友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见其洗耳,问其原故。许由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我嫌这话污了耳朵,所以来洗洗。”巢父批评许由:“你若是隐居到髙岸深谷人迹罕至处,谁能找得到!像你这样的隐居还是在求名啊。这水被你弄脏,我的牛犊饮不得了。”于是,牵着牛到上游喝水去了。
由此可见,巢父是作为许由的朋友出场问世的。前人多怀疑“巢父”、“许由”是一化为二,汉代人常说的“巢由”即“巢栖者(结巢而居的隐士)許由”,汉魏文献也常注“巢由”,并称为巢由或巢许,用以指代隐居不仕者。自古以来,巢父、许由以隐居圣贤齐名,俨然是一对不离不弃的孪生兄弟。
再次,巢父是巢文化特有的人文符号。
笔者最近在网上看到山西平陆网民的一个贴子:我们从小就知道平陆县历史上有“七贤八景”,其中“七贤”首推巢父、许由。但到了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一处提到他们是平陆人。为什么?他们究竟是哪里人呢?
现在一般认为:许由是唐尧时代的贤人。帝尧在位的时候,他率领许姓部落活动在今天的颍水流域,这一带后来便成了许国的封地,许由从而也成为许姓的始祖。
而巢父则是与许由同时代生活在巢湖流域的部落首领,解甲归田后成为隐居南巢的贤士。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巢氏,有巢氏之后。尧时有巢父,夏商有巢国,其地在庐江,子孙以国为氏。”宋代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辨证》:“有巢:古帝者有巢氏后”。《高士传》则云:“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1999年版《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进而归纳结论:“巢湖及带‘巢’字的行政区名称均源于古巢国。古巢国源于有巢氏所建方国。”这些记载,与巢湖方志和民间信众是一脉相承的。从有巢氏、巢国,到巢父、巢山,或国以人建立,或人以国为氏,以特定的名氏基因或曰人文符号,一脉相袭,历代相传。
在巢湖,巢父是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1673年刊刻问世的康熙《巢县志•沿革志》记载:“罗泌《路史》:称有巢氏。帝尧陶唐氏,有居巢父,以巢为居,因得名。”并按:“帝尧当栋宇既作之后,而巢父仍居有巢之旧,或遂以名其地云。”卷之十五人物志在“名贤”栏介绍“巢父”:“陶唐时人,以树为巢,栖息其上,故曰巢。今与许由并祀于万家山傍,名二贤祠”。卷之二十志在“古迹”栏介绍“洗耳池”:在教场西,相传为许由洗耳处。并按:“许由洗耳于颖水,隐于箕山,疑不在此地。然古以巢、许并称,巢父当洗耳时,责其浮游于世,以求名誉。而父实巢人,必不游颖滨矣。大抵先贤遗迹,无容湮没。姑两存之,可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康熙《巢县志》此处敲定“父实巢人”,这就给“巢父”上了巢湖的户籍,这无疑是向世人宣告:巢父是巢湖人!与此同时,志中并没有将“许由”占为己有,而是“姑两存之”,足见先贤修志客观与包容的智慧。
由此可见,巢父作为唐尧隐士,毋庸置疑是巢湖人;作为传说人物,则是巢文化特有的人文符号。
第二,陆游《五律•巢山》二首再探
笔者曾撰小文《巢山景物自成诗——陆游二首初探》(2011年6月7日安徽文化网发布),试图探讨陆游歌咏巢山与巢湖巢山的关系。由于孤陋寡闻,不敢妄下定论。随后有幸拜读宁业高、黄鹏程二位先生《揭启巢山显身隐名之谜》大作,可谓坐实了陆游歌咏的巢山就是巢湖的巢山。

本文作者与有巢氏画家许红海先生(右)在一起
然而,对此社会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值得我们正视应对,以析真伪。
有人提出,1983年署名周始编撰的(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非正式出版物)《皖志述略》有记:“巢城西南百里道人山,又名巢山,县志收陆游《巢山》诗二首。但陆游此诗作于山阴故里,也与巢县山水无关。”且云:“此类牵强附会、移花接木之弊,在旧志中常见。”
而陆游《五律•巢山》二首收入康熙《巢县志》有注:“巢山本名道人山,在县西南百里,唐天宝年敕改名。”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古人笔下的安徽胜迹》收入陆游《五律•巢山》更有明确注释:“巢山:据《太平环宇记》,本名道人山,在县(巢县)西南一百里,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敕改为巢山。”
那么,二者孰是孰非?
这里,《皖志述略》既没有以文献史实否定道人山在天宝六年敕改为巢山,又没有考证确定陆游山阴故里有一座巢山,就妄下“牵强附会,移花接木”的论断,显然犯下主观臆断、以偏概全之修志者大忌。
反之,《古人笔下的安徽胜迹》作者朱世英、高兴在《序言》中申述:“凡前人已注释过的,我们对照各种注本,根据自己的理解,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中有不完备或不确切的,则尽我们的能力作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可以说治学严谨,客观可信。
还有一种说法:陆游《巢山》二首,应属于陆游“晚造平淡”的田园诗作,这与诗人旅行天下,歌咏巢湖“巢山”的设想是矛盾的。并以陆游《山居》“平生杜宇最相知,遗我巢山一段奇”的诗句,佐证诗中“巢山”当在陆游故里。
诚然,阅读欣赏,见仁见智,无可厚非。笔者以为:1、既然本名道人山,在天宝六年敕改为巢山,即不影响巢湖“巢山”之成立。2、笔者在《陆游二首初探》中,从诗句“何曾蓄笔砚,景物自成诗”看,假设陆游《巢山》应是身临其境即兴之作。这当然有待进一步求证史料记载,但在确认之前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3、因无文献记载陆游《巢山》写于巢湖“巢山”,姑且采信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陆游《巢山》庆元元年(1195年)夏作于山阴。但这只能说《巢山》成诗不在巢山,并不能确定与巢湖“山水无关”。陆游《山居》一诗钱氏校注为绍熙二年(1191年)春作于山阴(早于《巢山》4年)。但是,由于吟诗作文自古即有“即席”与“追记”之别,即使《巢山》、《山居》作于山阴,也不能否定诗人是歌咏巢湖“巢山”。而《山居》“遗我巢山一段奇”及其随后的《巢山》“短发巢山客”诗句,常规解读:“遗”乃赠予之义,这里应指诗人客旅他乡(或即巢山)留下的美好记忆。因为故乡是诗人一生的根,总不该仅有“一段奇”吧!正是有了这“一段奇”,诗人又作为“巢山客”,接着回忆写下了《巢山》二首。
第三,巢父与巢山价值观及其现实意义
人文始祖有巢氏之后巢父,作为古史名贤,一直为后世所景仰,李白、杜甫和陆游等历代文人墨客均有为之诗词歌赋。而鲜为人知的巢山,最近又由政府部门将“象山”或“相山”俗称恢复敕改“巢山”之正名。巢父与巢山作为历史人物和特定地名,不仅是个人名字和所处位置的标记,它更是人类活动的遗迹,是历史进程的载体。这一遗迹与载体,蕴藏着历代传承的基因密码。就像我们生命代代传递的基因中不变的部分,是共同血缘关系的标志。这也是《安徽省志》作出“凡带‘巢’字的行政区命名都与古巢国有关”论断的依据所在。
巢湖自古人杰地灵,风光秀丽。巢父是巢文化特有的人文符号;巢山则是巢湖一道美丽的风景。这次巢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巢父价值观及其现实意义。对此,我的思考至少有四个方面价值或效用:一是在政治生活上,反腐倡廉的警示效用;二是在人际交往上,洗耳恭听的和谐效用;三是在处世修身上,纯净心灵的教化效用;四是在社会发展上,回归自然的生态效用。借此机会,笔者衷心期待通过这次巢湖市“巢父文化节”学术研讨会,打好、打响“有巢故里,安徽巢山”这张牌!

专家学者赴巢湖市巢山考察合影留念
感慨系之,且诌小诗谨贺:
邑南巢父与巢山,雄视沧桑若等闲。
今日群贤犹洗耳,清风济世著新篇。
(本文系作者在2012年7月27日巢湖市“巢父文化节”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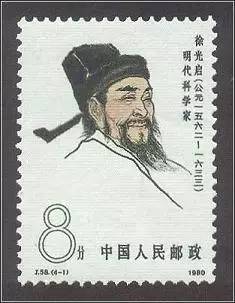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