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怀不乱,最早出自于《荀子·大略》,故事讲的是柳下惠宿于郭门,有一妇人来投宿,他怕妇人夜晚冻死就让一妇人坐在自己的怀中来取暖,而始终未有非礼行为。于是,后人用这个典故来形容正人君子。

坐怀不乱(坐怀不乱是什么意思)
后来许多人表示异议,“我们纵使不从柳老先生的生理角度来理解,换个角度想一想:假使真有其事,又是谁传出来的?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那女子说的。但是,可能吗?一个女子能够大大方方躺在一个陌生男人怀里过上一夜,然后还惟恐天下不乱地大事宣扬?另一种可能是,柳下惠自己说的。如果真的如此,这个柳老夫子也就够无耻的了。这不是要坏别人的名节吗?”
那么让我们看看原文:
《荀子·大略》载:
子夏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
唐杨倞注:“柳下惠,鲁贤人公子展之后,名获字禽,居于柳下,谥惠,季其伯仲也。后门者,君子守后门至贱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恶与后门者同,时人尚无疑怪者,言安于贫贱,浑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闻,言闻之久矣。”杨之注根本不涉女色,荀文原意也和后世所谓的坐怀不乱无关。
成于西汉初年的《毛詩故訓傳·巷伯》云:
昔者,顔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顔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壊,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户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栁下恵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栁下恵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學栁下恵之可。”孔子曰:“欲學栁下恵者,未有似於是也。”
这里有个词,就是“后门者”是什么意思?
是男人?
是女人?
还是看门的?
还是后进门的?
如果我们不看是否男女,而从原义上看,本是指柳下惠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但一涉及男女,好象成了花边新闻,人们有了热议。
其实,道德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柳下惠死后才有老子,而到老子骑青牛西去才留下了千古名言,今人用现在的观点去考量古人的行为,自己多有不解。
也许是个误传,但柳下惠之君子之风总是无疑的吧?
即使是个误传,老先生算不算乐于助人?
中国人对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龙”崇拜了几千年,又有谁说过不对?
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期望总是在想像借喻中发展的,现在来看,即使当时柳下惠没有办这事,但人们把愿望的结果安放在了他的身上,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他的高尚。
只有一个高尚的人才能受到人们的仰慕,
只有一个高尚的人才有可能作到“坐怀不乱”,
只有人们做不到的事情,才认为圣人能做到。
也许人们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榜样,也许人们在骨子里就有“和”的意识,在聚积沉淀中互相发功,将鼓胀的热量用一个火星点燃,照亮了人们心灵阴暗的角落,有什么不对?
“坐怀不乱”这事有没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灵如我们自我的要求与想像得到净化,净化到《般若金刚波若蜜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古人把自己心灵的“和谐”之美喻于一人,实际上是把“和谐”拟人化,“动画”,这是中国古文明之路上必然的进程。
让我们也抛弃满脑子的肉欲,进入自己的心灵世界,
让“和谐”之音纯净自己的心灵空间,
让人类真正进入一个“和谐”时代,
用和谐来拯救危机,
人类要想达到和谐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
我们不要再去实践“坐怀”了,
我们最后只是看“乱不乱”?
你们说现在到底“乱不乱”?
难道我们不需要柳下惠?
我说的是他的品质与精神!
需要,太需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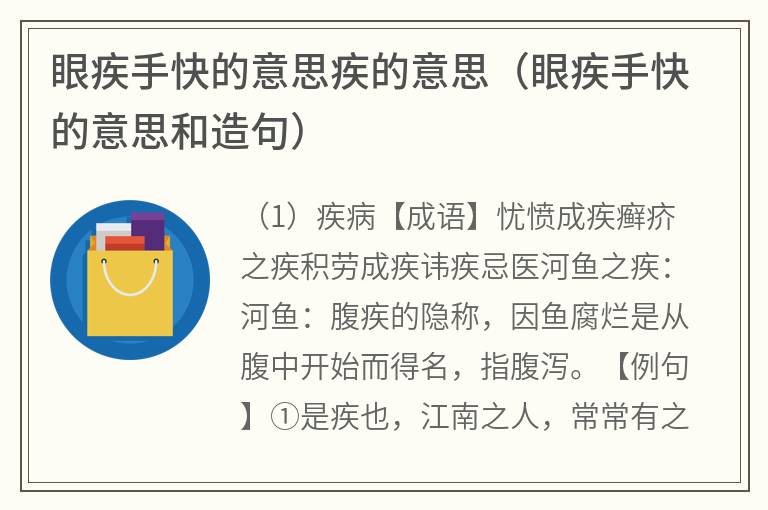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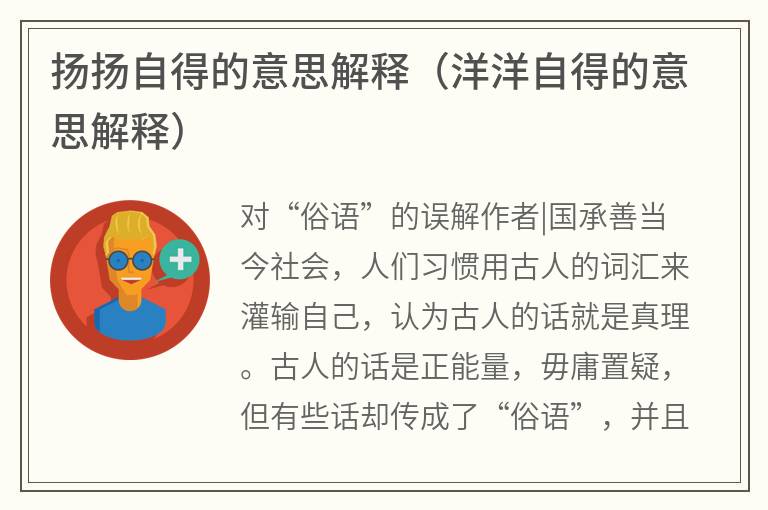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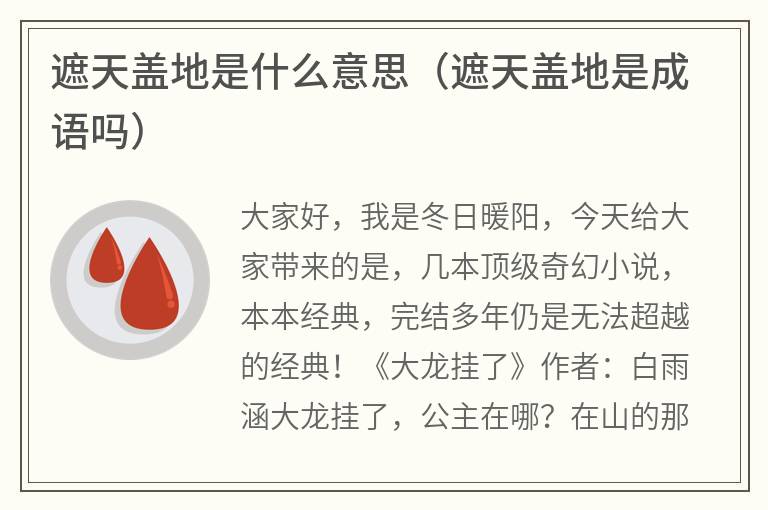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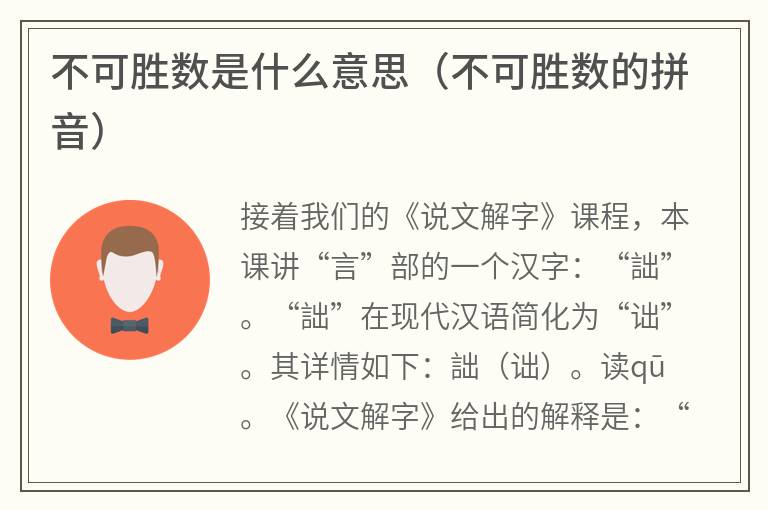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