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率吉字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1868年8月16日,梁王张宗禹兵败徒骇河,西捻军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与捻军,是十九世纪中叶爆发的两场影响深远、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他们相继失败的背后,却成就了湘军、淮军这两支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汉族武装力量,在中国大地的迅速崛起。
湘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两者内部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令人深思的是,这两支系出同门的兄弟部队,却从未显示过任何情同手足的友谊。

李翰章(李瀚章和李鸿章的关系)
当然,出于“剿匪”的形势需要,两军之间曾有过并肩合作,也有过相互扶持,但更多的,是恶性的竞争和戕害,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与怨怼。
而试图厘清湘军与淮军的“是非对错”,就不能回避两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曾国藩与李鸿章,这两位国之柱石间的“恩怨纠葛”。
曾国藩、李鸿章,晚清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两者均是当时最顶尖的汉臣代表,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比各自所统领的湘淮军更加复杂而微妙。
二人既有师生之谊,曾对李还有知遇、提携之恩,曾国藩全力支持得意门生创建了淮军,而李鸿章对自己的恩师则是一生恭敬有加。
同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与左宗棠老死不相往来,左宗棠与李鸿章一生针锋相对,但至少从表面来看,曾、李二人在大多数时候,都维持着一种休戚与共、同气连枝的默契。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今天的文章,就为大家揭秘最真实的曾、李之交,以及二人背后湘、淮两军的明争暗斗。
道光十八年(1838),27岁的湖南人曾国藩以三甲第三十八名的成绩,高中戊戌科进士。
无独有偶,这一年的同榜进士中,位列三甲第一百一十二名的安徽人李文安,便是李鸿章的父亲。
冥冥之中,两位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产生了联系。——因为曾国藩与李文安的“同年之谊”,李鸿章及其兄长李翰章便以年家子(科举中同年者的晚辈)的身份拜入曾国藩门下,求义理经世之学。
李鸿章天资聪颖,曾国藩对这个学生也极其欣赏,认为“其才可大用”。果然,两年之后,年仅24岁的李鸿章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出众表现考取丁未科进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因母丧丁忧返籍的曾国藩,奉命在湖南老家筹建湘军,而李鸿章志向远大且心高气傲,自是不愿久居人下,所以并未选择投靠恩师曾国藩,而是回到老家安徽帮办团练,想藉此作为契机,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谁知事与愿违,书生从戎的李鸿章不谙兵法,虽沐风栉雨、甘苦备尝,却屡战屡败,只落得个“专以浪战为能”的恶名。
愈挫愈勇之后,李鸿章在战事上虽稍有建树,却又因功高遭妒而致谤言四起,于乡里间几无立锥之地。
1857年因父丧丁忧归乡,其被迫结束五年团练生涯,次年太平军攻陷庐州,李鸿章只得携家眷出逃南昌,寓居其兄李瀚章处。
几经辗转,咸丰九年末(1859),走投无路的李鸿章致信恩师曾国藩,表达了投效之意,而湘军在经历了1858年的三河镇惨败后元气大伤,亦正值用人之际,两者一拍即合,就这样,李鸿章来到江西建昌湘军大营,充作曾国藩幕僚。
然而,战火纷飞之中,曾、李师徒再次相聚,却没有上演珠联璧合的好戏,反倒在重逢不久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1860年,曾国荃率吉字营大举围攻安庆,主帅曾国藩则驻节皖南祁门督战,而此时恰逢忠王李秀成率十数太平军万途径皖南,徘徊于祁门之外。
李鸿章见此处居万山丛中而形同釜底,乃兵家所忌的“绝地”,再三劝告主帅移营,但曾国藩不为所动。恩师执意置身险地,李鸿章苦劝无效,围绕祁门的去留问题,师徒二人心中已渐生芥蒂。
祁门
此后又因为湘军将领李元度徽州战败,落荒而逃,曾国藩愤而罗列三大罪状纠参,而李鸿章则以“(李元度)久共患难,不可罪”为由,拒不拟稿。
曾大帅的执拗劲也上来了,你不操刀,我便自行上奏,李鸿章见状更是针锋相对,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若执意弹劾,我便辞职归乡。
至此,曾、李二人矛盾彻底爆发,李鸿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祁门的师生反目,其实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也无关大是大非的争论,曾、李在共同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劝说之下,也很快便重归于好。
但这次争端背后隐藏的深意却值得好好分析,不过在此之前先简单说明一下曾国藩移营祁门的原因和背景:
1860年,正当安庆争夺战如火如荼之际,忠王李秀成的东征也取得重大胜利,苏南赋税重地,纷纷落入太平天国之手,而上海也处于太平军的围攻之中。
咸丰帝迫切地希望湘军能立刻回援苏常,而作为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守土有责,只是安庆之役正处于关键时刻,湘军主帅又不愿轻易撤军以至功亏一篑。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以主力继续围攻安庆,而将位于安徽宿松的总督行辕前移至皖南祁门,摆出向苏南用兵的架势,也以此举向咸丰帝交差,只是不想李秀成阴差阳错用兵皖南,正好出现在了祁门周围。
此时曾国藩身边仅有亲兵二、三千人,在李秀成大军压境之际,选择避其锋芒,迁驻别处,确实是一种稳妥而安全的选择。
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移营,曾国藩等人化险为夷的同时,必然会对安庆的整体战局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
在这种前提之下客观分析,曾国藩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透着一股湖南人特有的“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的倔强劲头。也符合“文臣尽忠,武将死节”的封建道德行为准则。
而李鸿章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则更多地体现了徽皖文化中“经世变通”的特质。同时追求现实利益、注重实际效果,也是李鸿章一生信奉的“实用主义”。
李鸿章考虑“小我”的切身安危,因为只有在生存的前提下,方能谈及其他价值的体现;曾国藩顾及的是“大我”之得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个人的奋不顾身中,多少也有点追求忠孝节烈的惨烈味道。
正所谓见微知著,祁门的矛盾和分歧,对错暂且不说,反映出的却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师生之间,在性格人品、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境界格局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而这种差异,对于此后二人创建的湘军、淮军也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曾国藩在1853年时,已官居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其人本身亦是当时湖南的文坛领袖,不说名满天下起码也是蜚声湖湘。
曾文正公不可能未卜先知地意识到湘军会成为后来左右时局的第一劲旅,也根本不会将湘军作为有利可图的政治筹码。
而本土的文化特质,在曾国藩创建湘军的过程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湖湘文化就其传统内核而言,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远大抱负和责任担当。
因此,曾国藩的墨绖从戎,既是受旧时代士大夫忠君报国,剪除“乱臣贼子”的内在使命感所驱使,也体现着儒家传统思想中,文人“修身、齐家”之后,“治国、平天下”的终极追求。
而曾国藩这种“澄清天下”的大志,与李鸿章创建淮军时的初衷,又有本质的不同。
二十一岁的李鸿章第一次赴京赶考,以《入都》为题,作诗十首,其中“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佳句,在展现李文忠公超卓胸襟气魄的同时,也透露了其封侯拜相的现实愿望。
金鳞本非池中物——初办团练不成,后又久居湘军幕府之中,心高气傲却一事无成的李鸿章,急欲实现人生抱负和政治理想,而机会就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1861年9月,湘军取得安庆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曾国藩准备稍事休整之后,便乘胜直扑下游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而此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等地城池,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沪上官绅惶惶不安,派人至安庆向曾国藩泣血求援,并承诺若湘军东援,将月奉白银十万两劳军。
湘军这种私人性质的地方武装,从成立之初便是自筹饷银,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时时都处于“饥寒交迫、嗷嗷待哺”的状态。
面对这种难以拒绝的条件,曾国藩当即决定由胞弟曾国荃领兵往援,但九帅心系天京,一心想成就平定太平天国的不世奇功,因此婉拒了兄长的安排。
曾国藩只有转而与门生李鸿章协商,久居人下的李鸿章正在等待改变命运的机会,闻言欣然领命并火速返回庐州老家招募乡勇。
此时的李鸿章,有没有其恩师从戎时重振朝纲,解万民于水火的理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依靠领兵打仗而扬名立万、加官进爵的功利心理,却是不言而喻的。
其后,随着淮军的崛起与不断壮大,李鸿章也更多的是将这支部队视作实现个人目的和达成个人愿望的工具。
而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暗示之下,淮军以及李鸿章不断培植的内部势力,自然就成为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
1862年3月,李鸿章携新募两淮丁勇,即后来淮军中大名鼎鼎的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核心四营于安庆集结。
而曾国藩对于李鸿章这个得意门生可谓照顾备至,不仅将创建淮军这把改变命运的钥匙交到了弟子手中,更举荐其署理江苏巡抚一职,从而使得无尺寸之功的李鸿章,在出师之前便距位列封疆仅一步之遥。
同时因担心弟子势单力孤,又资助其两江总督专属亲兵二营,再由湘军中抽调熊字、恒字、春字各一营,尤其是程学启的开字二营,此后更是成为了淮军中的王牌。
如此一来,淮军十三营中,原属曾国藩的湘军便占据九营,而淮军在组建之初,其募兵思路、营制饷章、训练方法、管理制度也基本由湘军沿袭而来,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淮由湘出”的说法。
1862年4至5月间,淮军6500人分成七批,乘英国商船由安庆出发,经下游太平天国防区后,抵达上海。
李鸿章也确实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一片苦心,甫至沪上便用虹桥、北新泾、四江口的三场胜仗打开了局面。
在解除了上海的燃眉之急后,李鸿章获得了当地士绅的支持与信任,再加上上海的关税、厘金收入,淮军的装备不断升级,规模也一再扩大。
1862年,湘军规复庐州,扫荡皖北,曾国荃吉字营兵临天京城下,声势如日中天,而曾国藩以钦差之尊,领两江总督之职,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政民务,整个东南战场均唯其马首是瞻。
同样是这一年,淮军亦迅速崛起,立足沪上后进取苏常,而作为主帅的李鸿章,抵沪第七个月,便被清廷实授江苏巡抚,后又委以通商大臣之要职。
如此一来,淮军独占上海富庶之地,又有国外势力的支持,清廷更仰仗其平定苏南乱局,经济上完全独立、实力持续提升,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又不断凸显。
加上此时李鸿章权柄在握,成为江苏第一号实权人物,以其为首的淮军军事集团,已逐渐从湘军中剥离而出,成为又一支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和私人性质的汉族武装。
而随着淮军的崛起和独立,湘、淮军以及各自主帅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慢慢浮出了水面。
首先是饷银问题,曾国藩之所以同意派兵东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海乡绅承诺的每月十万两的资助。
而李鸿章抵沪半年内,便两次协济湘军九万两军饷,但此时正值天京战役的关键时期,湘军投入近八万兵力参与围城,用度之大、开销之广实在难以计量。
曾国藩虽然在此前曾强调“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但面临天京城下的困境,也只有向李鸿章硬性规定“每月酌提四万两,万不可减”,
而此时淮军初具规模,也同样在苏常鏖战,李鸿章家大业大,虽有沪上各项关税、厘金、捐资,但也并非十分宽裕。
面对老师的出尔反尔,还强制摊派军饷,李鸿章“意甚不平”,在写给曾国荃的书信中牢骚满纸,甚至以秦相李斯临死前的名言“东门黄犬,其可得乎”,来表达自己为官遭祸,抽身悔迟的不满。
1863年底,淮军克复苏州,随即又攻陷苏南重镇的无锡、常州,苏常地区已基本为其掌控。而湘军却依然在天京城下泥足深陷、一筹莫展,清廷便屡次催促李鸿章领淮军西援天京。
但李鸿章考虑到曾国荃屯兵天京苦战两载,眼看大功告成之际,自己领兵冒进,无论如何也洗脱不了贪功争赏之嫌。
何况湘、淮毕竟一脉相承,自己受曾国藩提携大恩,创军之初又蒙其鼎力相助,所谓饮水思源,就更不敢有任何“僭越”的非分举动。
因此,哪怕顶着朝廷的严旨催逼,李鸿章仍然是一再拖延,但主帅有所顾虑,淮军众将面对天京这块肥肉,却是垂涎欲滴,甚至表现得急不可耐。
淮军第一悍将刘铭传甚至公开放出狠话:“到得天京城下,若是曾老九敢阻拦,就让湘军尝尝淮军开花大炮的滋味。
刘铭传
由此可见,逐渐强大和独立之后,淮军将领在心理上对湘军并没有任何的依附和归属感,尤其是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就更谈不上半点同门的手足情谊了。
作为主帅的李鸿章也同样如此,其是皖人出身,早年在湘军阵营中颇受排挤,发迹之后,虽对恩师心存感念,但对于湘军集团却没有什么好感。
其私下写给淮军将领潘鼎新的信件,应该代表了大多数淮军将领的心声,这其中既有对湘军老资格的不满,也表达着作为后起之秀,希望沙场争功、彰显门庭的强烈愿望。
而正是淮军上下怀有的这种竞争与敌对心态,在1867年的尹隆河之战中造成了一次人为的冤假错案。
当时分属湘、淮两军最强的鲍超霆字营与刘铭传铭字营,原本约定联手夹击东捻军。
但刘铭传贪功冒进,提前出发,以至为遵王赖文光所困,全军覆没之际,幸得鲍超率霆军及时赶到救援,刘铭传及残部方才死里逃生。
谁知刘铭传自知行为失当,竟在战后诬告鲍超故意迁延,贻误战机,而当时的剿捻主帅李鸿章明知其中缘由,却一味偏袒部下,致使湘军第一悍将沉冤难雪,含恨辞官归乡。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捻军又在北方兴起,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清廷无奈只有请曾国藩再度出山。
但克复金陵以后,湘军遭大量裁撤,湘军主帅只能被迫以淮军的班底剿捻,而李鸿章表面上承诺对恩师鼎力支持,实则阳奉阴违,甚至为保存部队实力,暗中怂恿麾下悍将刘铭传以伤病为由脱离战场。
这样的举动,令曾国藩大为恼火,并以少有的严厉口吻责备李鸿章道:“目下淮勇各部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
但无论如何,淮军这支隶属于李鸿章的私人武装,曾国藩难以向曾经的湘军一样如臂使指。最终在剿捻战场上耗时弥久却徒劳无功,只能黯然离场。
而李鸿章随即接任剿捻钦差之职,统领淮军在两年内迅速镇压东、西捻军,完成了老师的未竟之事。一起一落之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这对晚清最顶级的汉臣,也完成了权势和地位的交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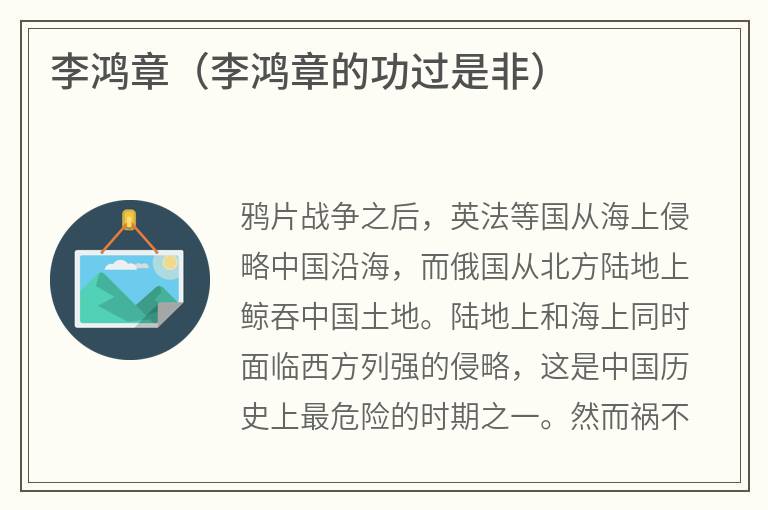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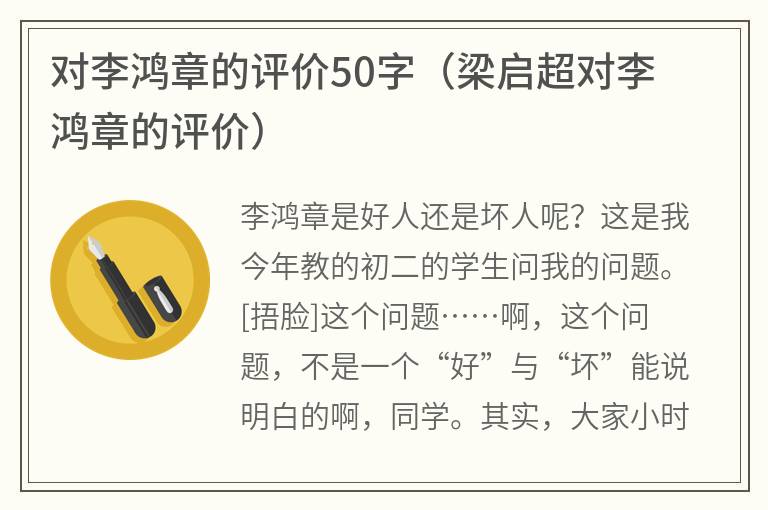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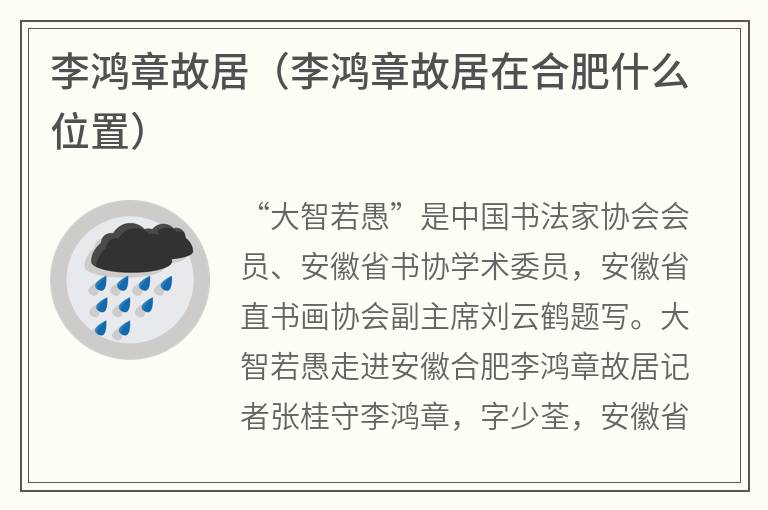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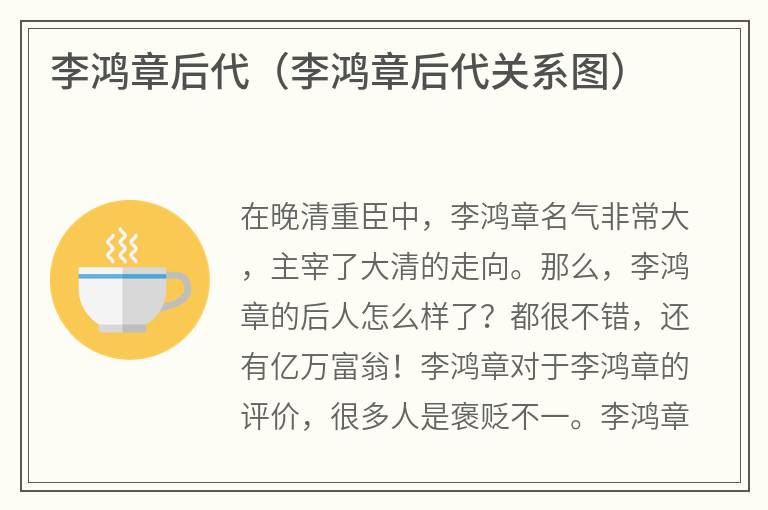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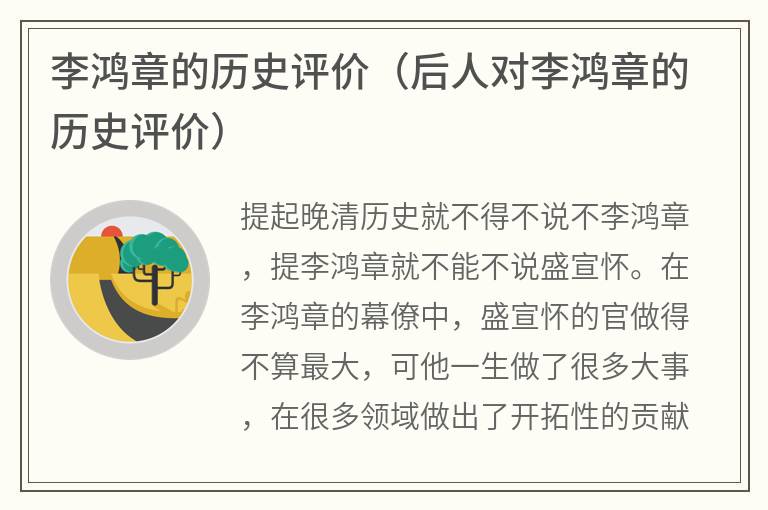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