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帝国时代是中华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一统帝国时代,不同于之前的秦汉、隋唐帝国,明清帝国时期疆域空前辽阔,经济发达,人口繁盛,国力臻于封建时代巅峰。自明太祖建国,明军灭亡元朝并先后多次北伐扫荡蒙古高原,北元势力苟延残喘。而清朝入关之前便已降服了整个漠南蒙古并通过盟旗制度实施有效的统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对蒙古诸部重新行使了自盛唐以后便丧失的宗主权,国威所至、四夷宾服,远至辽东、青藏、滇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偏偏有这样一个发源于遥远叶尼塞河的“边鄙”部落,在穿越戈壁沙漠,跨越阿尔泰山一路东进的过程中不断强盛,曾一度君临全蒙,并两次向极盛期的中华帝国发起挑战,这个部落便是蒙古部族中的“非主流”有着突厥血统的西方来客—瓦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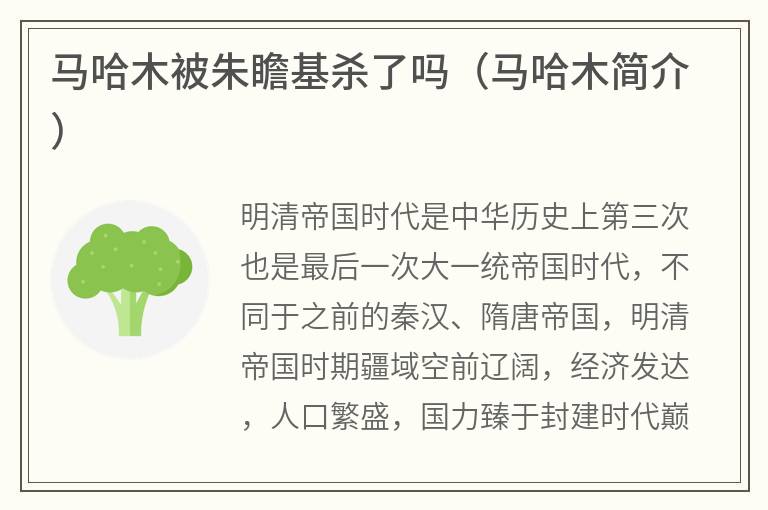
马哈木被朱瞻基杀了吗(马哈木简介)
民族起源
瓦剌,文献记载始见于《蒙古秘史》,史称为“Oyirad”,汉语音译为瓦剌、斡亦剌惕、卫拉特,一意为“森林中的百姓”;另一意为“联合者”、“同盟者”。最初发源于色楞格河下游、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附近森林地带,人数众多,部族繁盛,各有自己的名称,如斡亦剌惕、古儿列兀惕、兀良合惕、秃麻惕、巴尔浑、不里牙惕、贴良古惕、兀儿速惕等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统称为“秃绵斡亦剌惕”,汉译为“万户斡亦剌惕”即林木中百姓的联盟,斡亦剌惕为其中最大的一支,是由若干个邻近森林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并非某一具体部落。斡亦剌惕最早见诸于史籍之活动便是自13世纪初先后与弘吉剌、塔塔尔、乃蛮、泰赤乌、札答阑等部结盟,参与反对铁木真的联盟战争。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为了扫除南下金国之时的后顾之忧,1207年命其长子术赤出征林木中百姓。此时的蒙古帝国声望如日中天,斡亦剌惕首领忽秃合別乞率先迎降,成为蒙古军之先导,为征服林木中百姓建立了极大的功勋。为表彰其功,成吉思汗将女儿扯扯干嫁给忽秃合别乞的儿子脱列勒赤为妻,将术赤的女儿火鲁嫁给其另一个儿子亦纳勒赤为妻,并把美貌的秃麻惕首领塔尔浑夫人嫁给忽秃合别乞本人;并保留和扩展斡亦剌惕的领地和属民,允许其保留独立军队,封为四千户,以亲家忽秃合别乞为千户长,在大蒙古国内“亲视诸王”地位超然,由此斡亦剌惕形成了相对完善和独立的体系,“四卫拉特”时代也自此开启。
在随后百余年时间里,虽然卫拉特联盟内部各部族之间势力略有消长,但对外则“将各自所属部落统称为卫拉特”,随着蒙古帝国的多次西征,作为从属的卫拉特人也逐渐扩散到天山南北和中亚各地,并融合和兼并了很多蒙古及突厥系部落,不断壮大着自己的力量,而忽秃合別乞家族作为蒙元皇室世代婚配的勋戚,地位尊崇,史籍记载成吉思汗系公主配于斡亦剌惕贵族共16人,斡亦剌惕贵族女尚元室后宫者12人,凭着这层裙带关系,忽秃合别乞家族牢牢地掌握着卫拉特部落联盟的领导权。
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故元势力退回漠北,黄金家族汗权式微,经过百年韬光养晦和发展壮大的斡亦剌惕乘机摆脱元庭的羁绊,雄长西北,而继元而立的明朝史籍中也赋予了斡亦剌惕一个新的称呼—瓦剌;瓦剌与元代的斡亦剌惕部既有继承关系,又有着新的发展和变化。新加入瓦剌的有兀良哈绰罗斯部、阿里不哥后裔辉特部、克烈部后裔土尔扈特部和科尔沁部后裔和硕特部,随着领地扩大和属民的增多,原来的四千户卫拉特发展为“四万户卫拉特”,源于不儿罕山哈勒墩山兀良哈的绰罗斯部替代了忽秃合別乞家族逐渐成为卫拉特联盟(瓦剌部落)的领袖,在绰罗斯贵族脱欢也先父子统治时代瓦剌达到全盛,并通过几次战争差点颠覆了整个东亚帝国的格局。
瓦剌与中原交往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成吉思汗时代,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成吉思汗西征之时,在斡亦剌惕人居住区谦州已有“汉人工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到了元朝时代政府把大量中原地区的汉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迁往叶尼塞河上游谦州从事农垦和手工业,并利用当地条件发动斡亦剌惕人和汉人实行军屯和民屯,并由“南人”给斡亦剌惕人带去水利灌溉技术。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斡亦剌惕人和内地人之间了解不断加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斡亦剌惕人学会了内地的农耕、陶冶、冶铁和手工业技术,接触到了先进的汉文明,对遥远的中土有了初步的认识。
统一漠北
元末明初,瓦剌部落在首领猛哥帖木儿(非满清始祖猛哥帖木儿)率领下逐渐走向强盛,根据《蒙古黄金史纲》记载当时的瓦剌部族已有四万之众,兵力称雄西域。自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元朝势力被打回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时期,新生的明帝国为肃清边患,不断挥师北伐,在明军的频频打击下,北元政权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剌即西蒙古,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明朝主要军事目标仍是拥有蒙古可汗名位的鞑靼部,在连番打击下鞑靼部实力和权威大为削弱,已无力对其他蒙古部族进行有效控制,而瓦剌部因未正面受到元明战争波及,并且不断侵蚀和吞并邻近蒙古部落及突厥语系部落,实力逐渐壮大,摆脱了蒙古可汗的束缚,并向鞑靼部势力范围的游牧区移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瓦剌的克呼古特乌格齐哈什哈杀掉当时的蒙古部落大汗额勒伯克汗,蒙古之正统为瓦剌所篡夺,原本是北元臣属的瓦剌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明朝洪武时期的史籍《殊域周咨录》中对鞑靼和兀良哈都有单独记载,唯独瓦剌没有列传是附于鞑靼之后,一则说明瓦剌与明朝相隔遥远彼此并不了解,二则说明当时两者并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到了永乐六年,瓦剌首领,猛哥帖木儿之子马哈木向明廷称臣纳贡,翌年明成祖册封三位瓦剌首领马哈木为特进紫金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紫金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紫金光禄大夫、安乐王,此时的明剌关系进入短暂的“蜜月期”。当然促成明朝和瓦剌在这一阶段维持和睦关系并逐渐走到一起的是因为彼此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蒙古鞑靼部,此时的蒙古鞑靼部在可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的带领下,先后征服了兀良哈三卫、哈密和河西地区,截断了瓦剌和明朝贸易的通道,永乐七年六月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率军侵入瓦剌,结果被马哈木等击败,当年瓦剌部占领蒙元发祥地和林一带,永乐九年,在西北吃了败仗的鞑靼杀死明朝使臣郭骥,导致明成祖亲征鞑靼,并于斡难河畔大败本雅失里,并旋师东向于兴安岭击败阿鲁台,战败的本雅失里后为马哈木所杀,阿鲁台拥哈撒尔后裔阿岱台吉为汗,马哈木拥阿里不哥系后裔答理巴为汗,两者并称东西两汗,蒙古部保持东西对峙的分裂状态。
在明成祖第一次北伐鞑靼之时,瓦剌虽然仍保持着臣礼并献上元朝传国玉玺。但当时的朱棣已感受到瓦剌的骄横和野心。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不久便遣使北京,请求和明军共击瓦剌,而瓦剌也因为之前节节胜利和势力范围的扩大,对明朝的态度由恭顺转变为“表词悖慢”,永乐十一年,马哈木拥兵三万东渡饮马河,翌年瓦剌游骑甚至到达明朝边境兴和刺探虚实。为了保持蒙古诸部分裂现状,防患于未然,同年三月明成祖再次亲征,此次北伐明军直抵土剌河,瓦剌被打得大败,“损兵数千名王以下被斩首数十”,马哈木、太平等仅以身免,此战之后,马哈木自知不敌,于永乐十三年重新向明朝贡马谢罪。
经历此战,瓦剌损失惨重、实力大减,答理巴、马哈木、乌格齐哈什哈相继死去,夙敌鞑靼趁其新败联合兀良哈大举来犯,瓦剌无力抵挡只能求助于明朝,明成祖为了牵制鞑靼,于永乐十六年册封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之后的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明成祖连续三次亲征鞑靼,鞑靼部损失巨大,野心勃勃的脱欢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于永乐二十一年夏在饮马河大败阿鲁台,掠夺其人马牛羊殆尽,鞑靼部被打得四散奔走。在暂时消除外部威胁后脱欢回过头来整合瓦剌内部权力分配问题,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脱欢起兵征伐土尔扈特部贤义王太平,击溃其众,至宣德年间,脱欢逐渐合并了太平、把秃孛罗部众,土尔扈特、和硕特诸部首领已无力挑战脱欢,脱欢终于统一整个瓦剌部落联盟并成为最高首领。宣德六年春,脱欢再次大败鞑靼部阿岱汗和阿鲁台,逼得鞑靼远徙辽东,虽然此时的瓦剌从军事上已经完全压倒鞑靼,但在蒙古民族心中仍视具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血统的阿岱汗为正统,为了弥补政治上的劣势,宣德七年脱欢拥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立为太师。宣德九年七月,瓦剌杀阿鲁台,阿岱汗余部逃至陕西、甘肃一带。正统三年九月,瓦剌攻杀阿岱汗,在瓦剌和明朝持续打击下,鞑靼部趋于没落,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蒙古黄金史纲》提到“所谓卫拉特篡夺蒙古异国之政”,起源于岭西的“森林部落”统一了整个漠北。
消灭阿鲁台和阿岱汗后,瓦剌不断征服和吞并漠北的游牧民族势力,其疆域西北起额尔齐斯河上游,到达巴尔喀什湖,北连安格拉河以南、叶尼塞河上游,东至克鲁伦河下游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控制了女真诸卫并威逼朝鲜,南抵长城,到达了蒙古被驱逐出中原后最强盛的时期,此时的脱欢声望和野心已达到巅峰,一度想自立为汗,但却突然暴毙。脱欢的死在蒙古史料中颇有神秘色彩,传说一天,脱欢骑着马来到成吉思汗陵前,用剑劈其帐壁,出言不逊,说要取代成吉思汗,要做全蒙古的大汗。他的言行惹怒了挂在陵寝帐壁上撒袋中的弓箭,弓箭发出响声,脱欢背上应声出现了箭伤,口鼻流血。惊惶的人们看到撒袋中有一支箭还在颤动,箭头上沾着鲜血。此后不久,脱欢就含恨死去。这显然是一则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但也反映出了当时脱欢想做全蒙古大汗而又迫于蒙古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有黄金家族后裔才能合法继承蒙古大汗汗位的正统观念的阻碍,最终也未能当上大汗的历史事实。正统八年脱欢太师暴死,其子也先嗣位,自号太师淮王,明朝即将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土木惊雷
进入也先时代,瓦剌持续发展壮大,原本和明帝国有限制的贸易交往越来越无法满足瓦剌在经济、政治上的需求;此时的蒙古瓦剌部在疆域和军事实力上已不逊色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游牧民族草原帝国,经济上它寻求着更大的贸易范围,政治上也先也不再以“朝贡部落”自称,而开始自视为“北朝”,称明朝为“南朝”。早在脱欢时代,瓦剌便已开始小规模地袭扰明朝边境。至也先时瓦剌对明朝发达了全线战争,终于酿成了震惊历史的“土木堡之变”。
战争的导火线发端于双方经济贸易的纠纷。瓦剌和历史上所有的草原民族一样,单一的游牧经济使其迫切需要同农耕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交往,以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各种必需品。素来蒙古所需“锅瓮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明朝政府便利用蒙古各部的这一弱点,“各授以官职而不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采取了扶此抑彼、自相削弱的政策,加以控驭。就此瓦剌和明朝之间产生了特殊的经济政治关系—朝贡。瓦剌通过朝贡,向明朝表示顺从,损失一定的政治名誉,但他们得到的经济补偿却十分可观。朝贡包括称臣、进贡、贸易三个基本程序。瓦剌各部从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时期开始派遣使臣向明朝通好,明廷也不断派官去瓦剌各部,颁布敕谕,进行赏赐。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明成祖“以继位遣使颁诏,谕和林、瓦剌等处诸部酋长。”永乐元年,明廷遣镇抚答哈帖木儿等持敕书往瓦剌,招谕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永乐六年十月,马哈木等遣官向明廷供马,并“请印信封爵“,自是,岁一入贡,朝贡始行,瓦剌三王得到明廷的大量回赐、给赐物品。1412年,马哈木死,脱欢继位,仍不断派遣部属向明朝进贡名马方物,明廷也遣官答赐之。1418年,明廷令脱欢袭顺宁王爵,并遣官赐祭马哈木。对于归附的瓦剌人,视情节封官授爵,予以安置,正统初年居住在北京的蒙古人就有万余。正统四年,脱欢去世,子也先称太师、淮王,不再请求袭爵,但其部属中受明廷封爵者为数不少。有了上述政治关系,就能建立经济联系。进贡,是瓦剌和明廷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瓦剌诸部经常派遣使臣,带着马匹、骆驼、皮张、玉石、海青等物产向明朝朝贡。明朝原则上对”凡各处夷人贡到方物,例不给价”,但以给赐、回赐作为酬答。凡瓦剌诸王、一至四等头目以及使团的一至四等使臣,均有给赐、给赐物品有彩缎、绢、纻、衣帽、靴袜等。另计算所贡方物,给予相应的彩缎、纻丝、绢以及折钞绢等,称回赐。瓦剌贡使大体是每年十月由大同入境,十一月到达北京,参加正旦朝贺,次年正月离京。马哈木时期,瓦剌朝贡贸易规模不大。脱欢时期,朝贡人数及贡马数量明显增多。至也先时期,除1449年因与明朝发生战争没有通贡外,每年贡使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所带马驼成千上万。以景泰三年(1452年)的进贡为例,当时也先遣使3000人,贡马驼4万匹。仅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的20年里,瓦剌向明廷派出贡使团43次,其中13次的贡使人数为24114人,11次贡马驼68396匹,5次贡貂鼠、银鼠等各种皮货186332张。常常前使未归,后使踵至,出现了使臣“络绎乎道,驼马迭贡于廷,金帛器服络绎载道”的繁荣景象。
在如此大规模的朝贡贸易中,明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是给赐。如永乐、宣德中,赐瓦剌顺宁王彩缎十表里,妃五表里,头目一等者五表里,二等至四等四表里。外有加赐、回赐。与此同时,除京师会同馆为贡使们提供食宿外,沿途官驿也须按站接应,所需开支超出寻常。正统年间,仅大同每年往来解送及提供食宿,就要消耗“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一年的馈赠费用超过30余万两白银。随着瓦剌势力的强大,遣来贡使的频繁,所赠物品的剧增,使明方不堪重负,难以应付,比通贡造成的财政负担更严重的是武器流出,虽然明廷严禁出售武器以削弱蒙古武装,但武器走私十分盛行,屡禁不止,瓦剌方面对于武器的需求更是刺激了这种走私贸易。正统年间,也先东征西讨,急需明朝火铳之类的先进武器。明朝朝政日趋腐败,边疆官吏利用与瓦剌贡使接触之便,带头进行走私贸易。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铜铁箭头,用瓮盛之,与瓦剌使臣。也先每岁用良马等物赂(王)振及敬以报之”。上层如此,在京及沿途官军民等更肆无忌惮。1442年“瓦剌贡使至京,官军人等无赖者以弓易马,动以数千,其使得弓,潜内衣衫,遇境始出”。1445年“瓦剌使臣多带兵甲弓矢铜铳诸物。询其所由,皆大同宣府一路贪利之徒,私与交易者”。通过走私,大量武器流入瓦剌之手,直接威胁到明朝的国防安全。
正统十二年,也先的使臣一方面在明朝“构衅生隙”,一方面谎报使臣人数,希图冒领赏赐,明廷查明之后,仅以实数给之,凡虚报人数均不以承认,也先大怒,终于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发动了对明朝的全面侵略战争。正统十四年战火首先在辽东爆发。辽东“广宁沿边屡报烟火”,为了试探明朝虚实,也先唆使兀良哈和女真诸卫袭击明朝边境,明军反击初战告捷。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倾国而来“分道刻期入寇”:也先率主力寇大同,至猫儿庄,明军右参将吴浩迎战,战死;大汗脱脱不花偕兀良哈部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并遣别部寇甘州。蒙古军一路所向披靡,横扫了明朝边境。此时年青的明英宗朱祁镇在亲信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为了重现先祖的武功,轻率地作出了亲征的决定,土木堡之战拉开了序幕。
土木堡之战的结果已毋须赘述,但关于这次大战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团,其中最令后人关注和困惑的就是此战双方兵力对比之悬殊及结果之巨大反差,流出最广的是明英宗率领的五十万明军被两万瓦剌军击败,这个说法古往今来各种文献已连篇累牍地记录,似乎言之凿凿,由此引申出明军腐败不堪一下,明朝江河日下等各种观点,即使明军再脆弱无能,瓦剌再精锐强悍,区区两万人马真能全歼五十万大军,上演小蛇吞象的戏码,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不妨让我们来探究一番:
关于土木堡之战明军参战人数,在明清官方正史如《明实录》《明史》中均无记载,明代的《否泰录》《国榷》《北虏考》,清代的《明史纪事本末》写作“五十余万人”,《古穰杂录》《西园见闻录》《明书》等记为二十万人,说法不一;不过参考明帝国兵员数量倒是可以推敲出些许信息,洪武二十六年,明帝国全境共有329个卫所;明成祖时代都司卫所增加到493个,一个卫所兵额一般为5600人,总兵力约共计2760800人,而明军在京畿附近的武装力量主要是京营和畿内卫所兵,明成祖时设立了京营七十二卫,兵员在四十万规模,而卫所军也有二十余万;到了宣德年间,明朝又确立了班军制度,自宣德元年起,每年都会征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凤阳)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到京师备操。备操军分春秋两班,每班八万人,满额共十六万员,由此得名“班军”,由此看来明帝国京营额军人数当有四五十万人,似乎五十万大军出征也是顺利成章,但是以上数据都是额定兵员数,并非实际兵力。
从宣德五年开始,京营中五军营的额定兵员就逐渐缺失了,据明人叶盛《水东日记》所载,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战前夕,五军都督府并锦衣卫等卫官旗军人应有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缺员1633664名;即便如此将近三十三万的纸面人数也并非全部都是作战部队。明朝建国初期,耕稼尽废,百废待兴,急需与民休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当时的情况如果课税养军,就会使国家经济不堪重负.于是明太祖便下令各卫所就地屯田,卫所军士自己屯田耕种,以为军饷,是为屯田制。卫所军士通称为旗军,旗军又分为屯军和守军,屯军专务屯田,守军专务操练及对敌。京营之中,操练而不屯田的战兵满额人数应为十四万六千余人,这与《明实录》中正统二年记载的三大营额兵数量大体相当。由此可知京营战兵纸面总人数为战兵十四万余加上班军八万余人,大约二十二万。当然即使这二十多万人也无法全部随明英宗亲征。正统十四年六月底,明帝国和也先交恶,边防形势急剧恶化,明英宗令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军队前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一万五千军队前往宣府,以准备抵御随时可能入侵之蒙古人。说明在土木堡之战前夕,京营就已派遣了四万多人前往备边,留守京城的战兵已经不足二十万人。由此推测,战争前夕京师能战之兵倾巢而出业已不到二十万了,而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神奇”地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可见即使从京师以外的卫所征调兵马也根本来不及,我们可以断定,土木堡之战明军方面兵力不会超过二十万,约在十五、六万左右。
当然,就算土木堡之战明军只有十五、六万,但面对两万瓦剌军,一路被打得狼奔彘突,断后部队连番被吃掉,最后十几万大军一战而溃,也已经算明帝国建国以来的奇耻大辱了。而给明朝带去如此耻辱的瓦剌,也凭借自己的实力,在汉人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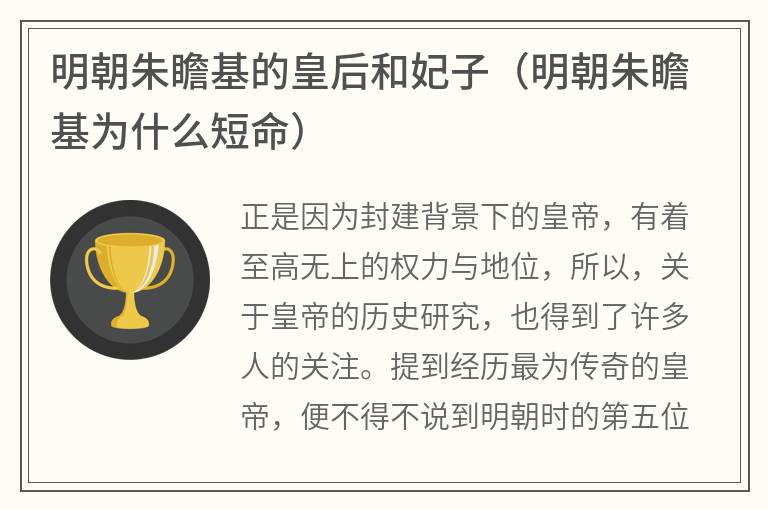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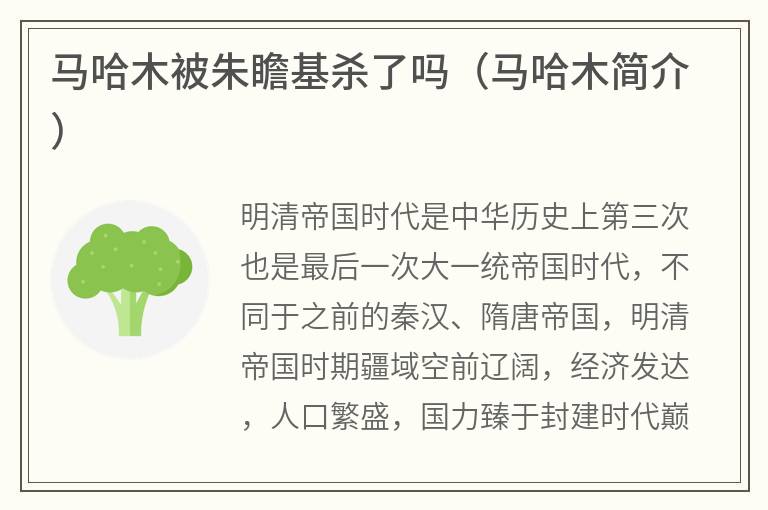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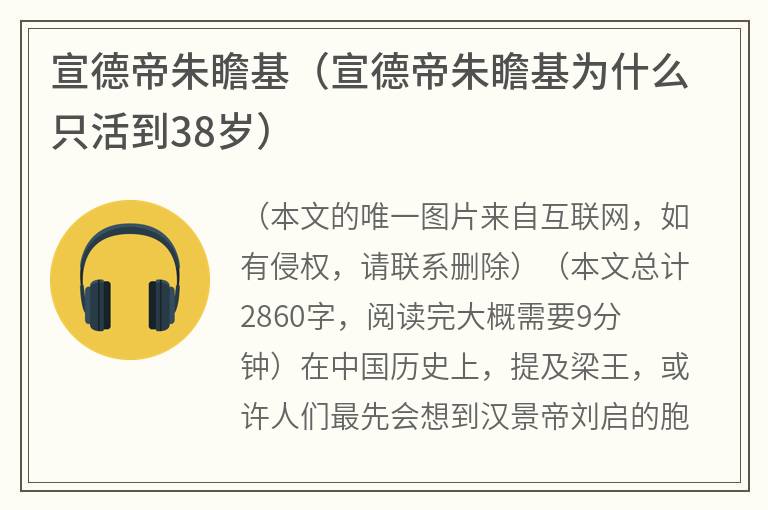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