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还觉得那桥很大。也就六七岁吧,我追着妈妈的自行车跑,跑过那段上坡的桥面,跪在拱桥的中央,就再也跑不动了。妈妈说,过一阵就把我接回来。她两脚一上一下歇在脚蹬子上,任车子从桥顶溜下去,越溜越快。她还笑着。我就哭了。爷爷慢吞吞赶上来,钳住了我的手。那条河在不远处拐了个弯,泛着黄晕晕的波光,弯进一丛绿柳中了。
桥的西面是爷爷的家,厂职工宿舍楼。东面就是学校。
“我给你看一个秘密吧。”同班一个男孩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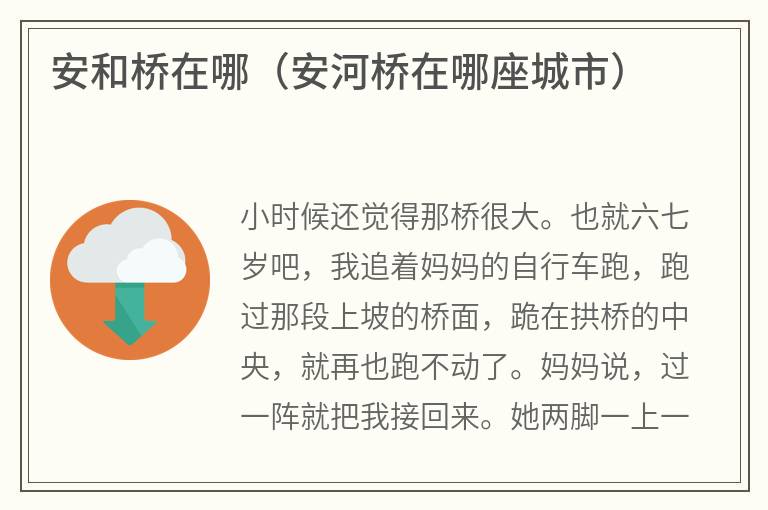
安和桥在哪(安河桥在哪座城市)
那是我转学到这里的第一天,放学后。
男孩的头发是个不规则的正方形。那时候都剪板儿寸。他显然是长时间没有去理发,就像只方头的小鸡。眼睛很大,嘴唇也厚,好似个外国人,但脸皮是焦黄的,脸颊上有一块一块的白斑,不知是起的皮还是什么。
“可别告诉别人。”男孩脸上很严肃,声音也压低了。
他从栏杆上翻下去,钻到安河桥拱形的桥身下面,阴影里。“小心呀。河里淹死过人。”他压低嗓音,脑袋伸出来,露在太阳下。夏天的风,暖的,一刮起来,路两边,不知长了几百年的杨树叶哗啦啦地响,好像站在海边。
我撅着屁股,攀着栏杆,用一只脚向下试探,总算站到桥底下。男孩不知从哪里掏出一颗颗的纸球来。
“看!我有钱!”
黑暗中,我只看到虚幻的彩色的光斑。等那些光斑安生了,才在男孩的手里看到棕色的纸币、灰色的纸币、绿色的纸币,一大把,揉成了一颗颗纸球,在他的手里缓缓舒展开,好像一朵朵灰暗的花,绽放。
“我捡的。”男孩说,他的脸藏在影子里。他留下一张来,把剩下的塞回桥洞的砖缝。然后,探出脑袋来,确保四周无人了,才爬上去,带我去了桥北面的小卖部。
“你想买什么?我请你。”
小卖部的门脸被高大密集的杨树叶笼罩着,窝在一片低矮的泥房子里。里面昏暗的墙面上挂满了玩具和小吃。一个胖女人磕着瓜子,坐在玻璃柜后面。柜子一层层的,也都是些零食、洋画儿。她的脑袋从上面探出来,用审视的眼睛看着我们,不说话,只有牙齿磕在瓜子上发出“咔咔”的声音。
我最喜欢奥特曼,挑了一个,头朝下塞进裤兜里。男孩则买了冰壶儿,七喜和一大联儿萝卜丝。一联儿就是十二个白色的小方口袋,上下衔接在一起。我从没一个人进过小卖部。妈妈带我去合作社买零食时,也都是一袋一袋得买,从没有买过一整联儿的。
玻璃瓶的七喜,我还是第一次喝。不对,我爸爸喝过,他喝剩下一口,给我喝。冰冰凉的,男孩在路上大口喝进去,脑门直疼。“哎呦”他直叫唤,低头,一手攥拳,顶着前额。等他好些了,就扬手把玻璃瓶砸在墙上:“去你妈的!”瓶里还剩很多,在土墙上画出一个星形深色的印。我和他都哈哈笑了。
天擦黑了,他拉我去他家玩。棕红色的方正的宿舍楼群,只有楼顶和窗沿涂着白色的新漆。一栋栋的,没有一点区别。往深了走,若不是看着每家窗户内的摆设不同,墙上用白漆写的数字不同,真就迷路了。
男孩的家,楼角上用白笔头画着奇怪的符号。我那时候就能看出,那不是汉字。进门前,他把吃剩的半联儿萝卜丝甩手扔进了垃圾桶里。
他的家是一套狭小的一室一厅。一张男孩睡的小床,一台两个手掌大的黑白电视,还有一张顶着暖气片摆放的小餐桌。这阴黑,没有窗的小厅,就只能挤下这么多了。
他撞上房门,说:“你坐这吧。”指了指自己的小床,声音故意说得很大。
我坐在他床上,闻着他家一股奇怪,温暖的味道。我那时很小,但那潮乎乎、又暖和的甜味,一闻,就莫名联想起女人来。联想起女人的奶。我盯着自己的两只鞋,鞋边互相蹭着,不自在,想说回家,但又害怕失礼。
一个女人从里面卧室的房门走出来,只穿了一件吊带的睡裙,露着肥嘟的胸脯和半截屁股。睡裙是滑溜溜的材质,在黑暗中还能反出光来。我忙低下头,只看着那女人赤裸的膝盖。
“不是不让你带人来。”女人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来。
“这是我朋友。”男孩的声音已经有些生气了。
女人站在原地,脚挪了挪,脚趾冲向我:“你们一个班的吗?你爸爸是哪个?”
我说了爸爸的名字,女人没出声。我说了爷爷的名字,爷爷是干部,女人才“哦”了一声。
“我给你俩倒口水喝。”女人转身进了厨房的门。隔壁传出水柱冲击的声音和玻璃杯被搌布摩擦时咕叽咕叽得响。
男孩用胳膊肘捅捅我,挤眼睛,吐了吐舌头。他迈过我的膝盖,低声说:“看看”就去开电视。电视打开了一片白雪花,纱响。他捋着右侧银色的频道按钮,挨个按了一遍,没有一个台有画儿。他又在电视机上用力拍拍,晃晃顶上的天线,还是没有,就关上了。
“今儿不灵。”他说。
女人进来,拿着两个挂着水珠的玻璃杯放在小饭桌上,就用暖壶往里倒水。开水挂着白烟,打在杯子里,发出呼的哨响。水快倒满时,水杯突然碎裂成几瓣,几滴开水溅到我的腿上。她慌忙拿来毛巾擦桌子,又用手指抹擦我大腿上的皮肤,看有没有烫破。她的手擦在我的腿上,有一种和这房间契合的温暖与潮湿的甜味。手指肚碰到我的大腿,我像憋尿一样,浑身一抖,一股奇妙的激动冲到我的腿根上,头脑里,不自主把大腿移开了。那感觉,却在之后几天反复追忆着。
女人愣在那里,要说些什么。“啪嗒”,卧室的房门开了。走出一个中年男人来,把一件旧夹克搭在一边肩膀上,迈过我的腿和女人的头顶,推门出去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卧室的门开着,传出浓郁的香味。我的心咚咚地跳,只觉得想从这里逃出去,又后悔没有钻到那卧室里,钻进那香味里去。女人和那男孩都愣在那里,什么也没有说,好像走出去的男人只是个幻影,只有我看到。
回到家时,楼门口停着辆警车。我还趴在车窗上看,看里面的记速表最大写到多少。进了家,班主任、警察和爷爷都在客厅里坐着。原来,第一天上学,天黑了都没有回家,家里人以为我被掳走了。
家里人多,我害怕,一边说着下午的经历一边竟哭了起来。
“你说去谁家了?”班主任问我。她是个烫着卷头发的中年女人,领子上的扣,总扣到最高一个。规矩。
我才想起那个男孩的名字,他叫蒋超。
“别跟蒋超玩。”班主任告诉我,她又看看爷爷和警察:“就是55号楼那个女人,她的儿子。”
我也不知为什么不能跟他玩,但隐约间也认识到这件事中有我不能理解的隐情。我擦着眼泪,用力地点头,什么也没再说了。只是裤兜里,压在大腿下,那个奥特曼玩具,头朝下,硌着我的大腿,都硌得青了。
后来,我再拿起这玩具时,从来只想,这一款已经绝版了,小卖部里也没有了。可我到底是没想起过,这奥特曼究竟是怎么来的。
第二天去上学,我就不再和蒋超说话了。蒋超远远的,一个人,昂着头走路,头发竖直着,像一只还没褪去绒毛就有了打鸣做派的小公鸡。他也没再和我说话,像是知道了什么。
倒是班里的那些好学生,一下课就把我围起来,劝我:
“别和蒋超玩。该把你带坏了。”
“蒋超他妈是鸡。”
鸡是什么呢?他们也说不好。
“鸡就是屁眼里面乱下蛋!”有人给出了解答,孩子们都笑了。我也跟着一起笑,用力笑,还带头学着动画片中的卡通公鸡,喔喔喔的叫唤起来。好学生们也笑了。我也成了好学生。
“不许你说我妈!”
蒋超喊道。
他是在安河桥上这样喊。
他站在安河桥上,把我按在桥栏杆上。我的身体被压得后仰着,都要被推下去了。
“不许你说我妈!”
他嘶吼,眼睛红着,要流出泪来。脸颊上,一块一块的白色,像是糖霜。两侧的柳树枝晃悠着墨绿的影子,沙沙响。淡蓝色的天空正中,划过一道修长的白线。那是飞机经过的痕迹。它好长啊。在天顶上划了一个连续的半圆,好像在蒋超炸起来的头发上戴了个发卡。
他放开我,从桥栏杆上翻下去,像只猴子一样,翻进桥拱下的阴影里去了。河水下面可以看到长长的水草,好像长在浑浊水底,泡开变大的狗尾巴草。我听说,这条河里,每年都淹死过人。
上到中学时,我妈妈才来看望我几次。她和我记得的完全不一样了。我偷偷想过一阵子,他们是不是换了一个人来当我妈妈。她把我接过去住,住了一阵子,这想法也就不见了。
中学来了不少农村的孩子。厂子里的孩子再凶,打不过他们。我在中学的楼道里,听到过蒋超的声音:“不许你说我妈!”他呼喊着,就和人打了起来。这样打过几次,也就听不到了。
几个农村的孩子,个头比蒋超大,坐在楼道的窗台上。阳光照进来,好像坐了几尊黑黢黢的怪石。蒋超蹲在楼道正中,听那些孩子骂他,骂他的妈妈。他蹲着,低着头,一声也不出了。原来同一所小学的,那些好学生们,围着看,也不敢说话,也不敢笑。只有一个站出来,大着胆子,先清了清嗓子。楼道里的人都看向他,蒋超低着头,用眼角看。那男孩子“喔喔喔”地学了几声鸡叫,楼道里的孩子都笑了。他以后就坐到了窗台上,成了又一尊怪石。
我暗暗不平。因为这鸡叫,正是我的发明。
男孩子长得快,脸上长了胡子。胡子把鼻子嘴巴都遮住,再剃光,鼻子嘴巴也变了样,变了一个人似的。
同学聚会时,大家吃饭喝酒递名片,唯独没有蒋超。也没有人提起他。我和几个混得潦倒些的,喝完了酒坐着地铁,就回家了。
从安河桥站出来,走路还要半个小时,几个人打一辆黑车,刚好。路边,一个矮个子男人叫出我的名字。他的头发像株疯狂的仙人掌,脸上有一块块的白斑,是蒋超。
“坐车吗?我带你们。走。”他拉开停在路边的车门,撅起厚嘴唇,拽住一个同学推进车里:“不收你们钱。”那同学老实,低头上了车。我也只好跟着,抢一步,坐进了后面。
车里没人说话,蒋超扭开收音机,左调右调,全是广告。
“你们去哪了?”
没人吭声。蒋超盯住那个坐副驾驶的倒霉蛋。他在机关里上班,最是沉着老练。他压着头,左右微微摇晃着,好像古代人要背四书五经似的:
“也……没去哪。就我们几个。”他说。
蒋超没再问,送我们到了厂门口,15块钱的路程,他向那副驾要了20,还要客气着:“以后坐车都找我!”
我们走得远些了,蒋超还停在那里,一条胳膊放在车顶,看着。他好像猛地涌上些感情来,对着那老练人喊:“代我问你妈好啊。这么多年了。”
那人一个劲儿地点头:“好好。也问你……一样。”硬生生把蒋超他妈吞进了肚子里。
我最后一次看到蒋超,是在去年,厂子门口的超市发。我在货架后面,他在收银通道的尽头,身边跟着个染了一头黄发的女人,和一个小儿子。
他的妻子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裙,能隐约看到里面,后背上、后腰上勒着根细细的带子。我躲在货架的深处,远远地,又能闻到那熟悉,潮湿的甜味,纠缠着飘过来。我的大腿、腿根,一直到心窝里,猛地一紧,想起了女人手指尖上的温度。我原来从没忘记过,或许还无数次地梦见过。只是梦里不能相认,醒来就更不敢了。现在,我倒羡慕起那个把夹克搭在肩上离开的男人,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来,我真的是,从小,就被这个,蒋超,给带坏了。
夜已深,我胸口一股郁闷,无处消解,就在厂子外面的小路上走。走到安河桥上,发了兴致。从桥栏杆翻下去。这对一个成年人来说,竟如此容易。只是钻进拱桥下面就难了。我弓着腰,窝在里面,用手机照着桥下石砖的洞隙。
风吹着,不知长了几百年的杨树叶,发出海浪一样的呐喊声。乌黑的河水流动着,那里面每年都淹死过人,下面粗大的狗尾巴草弯着腰,一下下地鞠躬认罪。这河向南流,不远处一拐,便进了颐和园,昆明湖,一汪盛景。
我把手伸进砖石洞里,抓出蒋超的宝藏来,一一摆在河沿上,用手机照着。那是一颗颗纸币揉成的球,有棕色的,有灰色的,有绿色的,是老版50元,100元和2元的纸币。它们在河沿上滚动着,停下来,缓缓舒展着身子,绽放。黑漆漆的水中发出“咕咕”的泡响,河面上浮出白色的尸身,是男人的脸孔,平静,是女人的乳房,硕大。过往死在这里的人,都浮了上来,密密麻麻地排在河面上,沉默地向下流动。我把石缝中藏得玩具也摆开来。几十个,约手掌大小,古怪的人偶,在河沿上站着,风中摇晃。人偶的两手在胸前交叉成十字。那是奥特曼。那是在小卖部里绝版的奥特曼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