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一场主题讨论“正史的编纂与历史观念”。
史书以既有资料为依据,史书文本的形成过程主要是“编纂”而非“创作”。通过细致的文本比对与分析,了解这些文字被取舍改编的来龙去脉,了解史家工作的普遍规则与特别处理,是继续探讨文本背后的事实与观念的前提条件。本场讨论包括五篇报告:李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五帝本纪〉取裁看太史公之述作》、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章怀注引用后汉史的形态与后汉史编纂》、苗润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辽史·天祚皇帝纪〉史源新说》、陈晓伟(复旦大学历史系)《大金国号金源说与祖先函普传说——论女真文化本位观念之演变》和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完颜挞懒死事之讹变——〈金史〉与宋代文献记载的对读》。
李霖的报告致力于挖掘《史记》作者的个人意图和主张。史书作者的主观因素犹如一面“历史的透镜”,并不直观呈现客观历史,作者的主观因素,与其视之为对客观历史的扭曲而摒弃,不如将其视为另一种客观对象加以独立地考察。
《史记》并不天然是历史书,太史公本人自称撰写《史记》是在“述往事,思来者”,叙述过往的历史,是指向当代、开启未来的,就像《春秋》的性质一样。《史记》的历史叙述中包涵的太史公的意图和主张,超乎多数学者的想象。发掘太史公的主观因素,方法一是立足于《史记》的内证,在全书中作横向比较。第二是做史源学的考察,讨论太史公可能对史源所作的取舍、删改和裁断。
作为《史记》首篇,《五帝本纪》凝结了太史公的一些重要思考。通过对读《五帝本纪》及其史源《五帝德》、《帝系》、《国语》、《尚书》等文献,可知《五帝本纪》对五帝历史的构建,背后遵循着一套关于王朝更迭的理论。《五帝本纪》开篇所以强调黄帝的战争,五帝三代血统所以皆出于黄帝,黄帝至禹所以同姓而异其国号,且皆行夏正,可能是因为太史公认为易姓受命必须通过战争来实现,且必须改正朔;而同姓则同德,同姓之间的王朝更迭是和平交接,也不改正朔。如此,《史记》五帝王朝更迭的原则才能与汤武革命、秦代周、汉灭秦等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机理和合法性保持一致。
《史记》要处理两千多年的历史,王朝的更迭和兴衰是头等大事。《史记》对王朝更迭问题所持的理论是一以贯之的,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结构,既是思想结构,也是文本结构。在抄本的时代,文本是不稳定的,但作者的原意绝非不可把握。揭示一部文献内部的稳定结构,研究“历史的透镜”的结构特性,可以丰富我们对该文献的认识。
聂溦萌的报告从范晔《后汉书》章怀注入手讨论诸家后汉书和后汉史编纂。诸家后汉史已经亡佚,研究相关课题必须以辑佚为基础。传统的辑佚以求全为主,重视旁征博引,但并未对每一种辑佚来源先进行深入研究。近来学者逐渐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弊病,尤其是类书引文的书题往往名不副实,据之辑佚并不可靠。史注的引文标题比较准确,且注文还与正文存在对应关系,信息可能更丰富。因此本报告从史注所引佚文开始,对后汉史佚文进行基础性研究,具体来说,调查研究的范围是范晔书章怀注中的“史学性”条目,其中引录的佚文以诸家后汉史为主,也包含少量郡书、杂传、文集等。
对安帝以前史事,注释引旧史以《东观汉记》为主,与刘知几说“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已下阙续”相应。安帝以来列传注释引用谢承《书》较多,但权重和文本贴合程度都不如《东观汉记》之于安帝以前传记。结合范晔《后汉书》列传的时代布局,可以推论《东观记》列传只有安帝以前成型,而晚期东汉史以士大夫运动为重心而书写,由此导致安帝以来与士人群体关系较远的人物常被合入早期传记中,安顺时期更几乎没有独立的传记。
由于东汉史的编纂有上述过程,如何分插合传可能成为不同史家反复尝试的问题。同时,东汉史的类传也在《东观记》以后还经历不少发展。合传选择及类传设置都与杂传的编纂密切相关。《东观记》安帝以后传记的欠缺,为后人留下了更开阔的历史撰述空间。
苗润博讨论《辽史》中末代皇帝天祚帝本纪的史源。元朝史官编纂《辽史》诸帝纪,一般是根据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进行采择、删削。但辽末丧乱之际的历史,在辽金旧史中阙略甚多,因此《天祚帝纪》的史源和编纂问题颇为复杂。
既往研究对《辽史》史源的讨论,缺陷之一是对整体文献源流把握不清,将文本的雷同简单等同于线性传抄,这主要体现在对《辽史》与《契丹国志》关系的认识上。《契丹国志》题为南宋叶隆礼所著,但实际上是一部拼凑宋代文献而成的伪书。它所依据的文献,有可能被元代史官直接取用。重新排查《辽史·天祚纪》与《契丹国志》的雷同文本,可以发现《辽史》文字虽总体更为简省,但亦时有关键细节不见于《国志》,而这些内容又多可得到《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亡辽录》,或《裔夷谋夏录》的印证。因此,《辽史》《国志》《谋夏录》《会编》应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它们都曾直接取材于史愿《亡辽录》,故而互有详略。过去冯家昇先生提出《辽史》三源说,对《契丹国志》的史源地位定位过高,而忽视了《亡辽录》及其他宋代的辽史文献。
既往研究一般只在辽史相关史籍的范围中考虑《辽史》史源,而元末宋辽金三史同修,在实际资料使用过程中常常互通有无,元代翰林院藏书实构成三史的共同资料来源。本报告由《辽史·属国表》辽金交聘、作战的记载切入,重新考察了《天祚帝纪》与金朝实录的关系。通过文本对比发现,金朝史官增入的记录,尽管还留有一些机械抄录的破绽,但总体上经过打磨,错误较少,与原本的辽朝系统记载融合度较高。而《天祚帝纪》中元末史官新增的涉金史事则颇为粗糙,存在系年舛误,且插入和删改都很生硬。
此外,前人通常默认耶律俨《实录》成于天祚帝初年,不记天祚帝事,因此在讨论《天祚帝纪》史源时只关注陈大任《辽史》和《契丹国志》。本报告指出,《辽史·历象志》闰考、朔考两部分一直到辽朝灭亡不久前的保大年间仍标有耶律俨《皇朝实录》的闰朔。而《天祚帝纪》的一些迹象也显示出,它也存在一个辽朝系统的史源。因此,辽《皇朝实录》也应部分记载了天祚帝史事,并成为今本《辽史·天祚帝纪》之一源。
陈晓伟围绕大金国号起源问题进行讨论。过去讨论金朝国号的起源和含义,基本持非此即彼的态度,但若关注承载诸说之文献产生的时间先后及文本源流问题,会发现金朝政治家对于大金国号释义和理解可能存在历史变化,从而可以发掘其背后所体现的政治文化特征。通过梳理“大金”国号诸说的各种史源,可以剥离出不同的文献层次,可归整为宋朝文献系统和金朝文献系统。研究发现,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显然迎合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境,抑或是为应对现实政治需要进行的宣传。
家族记忆与国号取义的历史叙述本是两条独立的线索,以《金史·世纪》为代表的早期记载中,女真始祖函普出于高丽,长期辗转才到达按出虎水。再次强调女真整体民族源流与完颜氏统治家族起源相区分的学术意义,并从这思路对祖先传说与按出虎水关系展开详细分析。

苗润博(左)、陈晓伟(右)
邱靖嘉讨论金初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熙宗天眷二年的挞懒谋反案。《金史》称挞懒在案发后畏罪自燕京南逃,后被杀于祁州,所记较为简略,而宋代文献却留下了有关挞懒之死更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有史料提到挞懒在被捕前曾有北逃沙漠之举。前人研究皆倾向于前者,否定挞懒北逃说,但梳理宋金史料,会发现其其事件经过颇为复杂。
宋朝文献中,应充分注意《神麓记》和《金虏节要》的记载。《神麓记》相关记载提到的地点、人物皆可在金、宋文献中得到印证,且所述挞懒死事经过亦合情合理,可信度很高。据该书,挞懒被夺去兵权后,本欲亲赴阙下面君,为引开追兵,遂派人佯装北走,出居庸,取道山后,趋凉陉,而自己则从虎北口东出,然因萧招折告密事泄,挞懒父子被宗弼擒获,赐死于祁州。
《金虏节要》与《神麓记》有关挞懒死事的记载在某些具体细节上可以相互补充。然两者相较,《金虏节要》将挞懒出走完全定性为一场叛乱,且仅言其北走“至沙漠儒州望云凉甸”,而不提挞懒实欲东出赴阙之事,很可能就是与挞懒早有嫌隙的宗弼奏报熙宗的说辞,以促使熙宗下诏赐死挞懒。由此,挞懒北逃沙漠之说便流传开来。
后来的南宋史书记述挞懒之死,主要依据的就是上引《神麓记》和《金虏节要》之说,而从未提及如《金史》所称的挞懒南逃奔宋之事。若其事属实,宋人不应毫无记载,而《神麓记》所述班班可考,不大可能出于宋人杜撰。今《金史》所记挞懒死事当源出《熙宗实录》,金朝史官编纂时一方面因袭宗弼上奏朝廷的说法,将挞懒出走定性为谋反叛乱之实据;另一方面,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又将北窜沙漠改为南逃入宋,从而产生了“南走”之说。
对话一:太史公的“真”与“善”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我想请教李霖。你的文章是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研究的一个个案,而你说《史记》中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太史公的信仰和他的史德是一致的,这在他全书当中都可以呈现吗?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在讨论久远的事情时,他建立了非常符合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秩序。但当他讨论到晚近的事情,比如李陵这样的故事,与他的历史理想很不协调,他自己也写下很多充满疑惑的感慨,在较晚时代的叙述里他对历史秩序的信念会不会动摇?
李霖:我认为司马迁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感受是相互塑造的,所谓的“通古今之变”,古和今是相互影响的。您说的问题在伯夷、叔齐身上就很典型。伯夷、叔齐的德极高,但最后都饿死了,不得善终。太史公就在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中不断追问和质疑所谓天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样的讨论并不妨碍《史记》有一以贯之的思想。我所说的一以贯之,是指用同一个理论应对同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的问题,就会运用不同的理论,而不是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理论使所有的局部都去服从。《史记》是多元的、复杂的,但同时也具有一个稳定的结构。
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我想再向李霖先生讨教的一个问题。听你的报告有一个印象,你把太史公作《史记》的思路大致归结为两条线索:经学系统的求善,和史学系统的求真。文章似乎比较强调前者,会不会是《五帝本纪》在反映太史公对于善的追求上是不是会比其他传记更有力一些?当时有多种五帝说,给了太史公很大的选择空间来求他的善;而对汉代人物,不太可能随意选取史实。

陈勇
李霖:非常感谢陈老师指教。首先,文中的“求真”“求善”,是我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采用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汉代经学家、史学家的求真、求善是统一的,他们应该是真诚地相信,通过善的原则求得的历史就是真实的。据我观察,这不是太史公特有的,甚至不是汉代特有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有传统的。
对于太史公当代的事情,在事实层面当然不容他信口雌黄。而他在处理远古历史时,也是要根据他能看到的文献来说话,同样不能信口雌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教科书,就像《春秋》是一部教科书,太史公一定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太史公甄别史料的工作,和今天实证史学里先确定历史事实再以之“资治通鉴”的思考方式是很不同的。他利用一套价值观来甄别那些离他很遥远的历史事实,而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的叙述当然是基于所见所闻,但并不妨碍他运用自己的笔法,寓裁断于叙事,表达自己的倾向和态度。比如在《匈奴列传》当中,每一次讲态度武帝伐匈奴取得了胜利,接着就讲第二年又遭到匈奴入侵受到损失,这样一种叙述会促使读者自己去思考,伐匈奴是否值得。而司马迁之所以反对武帝伐匈奴,是和“五服”的理论密切相关的。这个理论源于《周本纪》穆王伐犬戎,天子对于要服、荒服去兴兵征伐,是不正义的。在此《史记》的古、今是贯通的。只是对于远古的事情,《史记》的表达会更明确,对于当代的事情,表达会非常隐晦。就像《春秋》对于传闻的时代和孔子所处的时代,“书法”也会有所区别。
我对《史记》全书的内容已经大致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理解,其中《五帝本纪》是我觉得需要率先抛出来的,所以先写了这一篇。《史记》对于很多事情都有非常强的个人态度和见解,而大部分都是通过叙述史事流露出来的。司马迁的这些态度,史学研究者可能认为不影响客观事实,所以可能不太重视。其实如果认识不到、不了解太史公的主观因素,包括他评判史料可信与否的标准、他对史事的态度和评价、他所持的一些经学理论,那么对于我们今天通过《史记》认识历史事实,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对话二:统治家族起源与王朝起源
苗润博:女真的家族起源和王朝起源叙述的分离非常明显。直到元朝修《金史》时,还保持着统治家族阿骨打家族从高丽来的叙述,从没改变过;但关于王朝起源,就像刚才陈师兄讲的,是阿禄祖的故事。这种分裂,在以往北族王朝的历史叙述里很罕见。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个案?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汉化胡化就能够概括,如果说“金源”是对汉化的反动,它的统治家族和整体统治集团的分离该怎样理解?
陈晓伟:我正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与孙昊老师交流,他大概意思是金初是讲祖先从高丽来,后来因为军事实力强大,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抹掉高丽因素,用“金源”取代了原来的叙述,这个意见有道理,但会遇到一些反证材料。我个人还是主张,祖先记忆和王朝的起源应该是两条线索,不能混同。
苗润博:关键的问题是,以往关于北族历史的叙述中,这两条线索是合一的,而且家族叙述往往是构成王朝叙述的核心要义。我想金人的这种分离意味着他们的现实,这不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而是现实政治结构怎么来反映在历史叙述中的问题。
罗新:我完全同意这个的思路。这不是简单的有一个观念去进行塑造,去调整,不是简单的书斋里的工作。这应该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构造,他的政治体的构造使得统治家族和整个统治集团不能合在一起。他们处理得也很好,没放弃任何一个,重心放在“金源”说上面。所以要知道契丹早期的构造怎样搭建,才能理解这个问题。
邱靖嘉:相关问题很复杂。宋辽时期的女真人,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长白山的女真三十部,而我们现在讲的建立金朝的女真并不在其中。后来完颜氏崛起,就把自己家族的历史写进了《金史》里。看起来《金史》在讲女真人起源的历史,实际上并不是当时真正的情况。而且女真人真正的族群边界在哪里,也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讨论,绝不是《金史》里讲的那么简单。
我也写过祖先起源的问题。我认同晓伟的部分观点,但有的我不太赞同。比如完颜氏家族把他们的祖先追到高丽,这没有问题,但你认为后来女真和高丽是类似华夏和夷狄那样的关系,我觉得风险比较大。你举的一些例证我觉得也有问题,比如关于完颜和王家。
陈晓伟:对,华夏与夷狄这部分已经改动,修改稿基本删掉了。而完颜与王家的问题,我仍保留自己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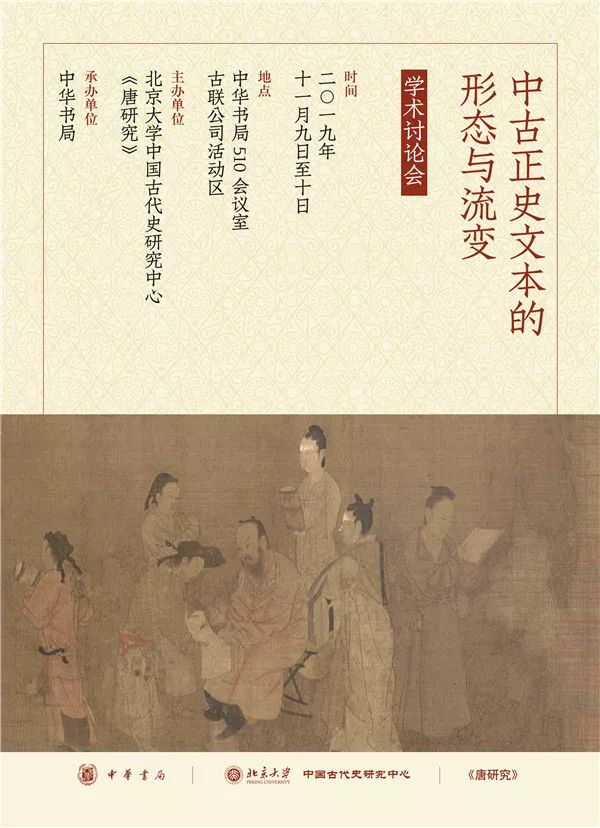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