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唐史十二讲》代前言:《我和唐史以及隋周齐史》第二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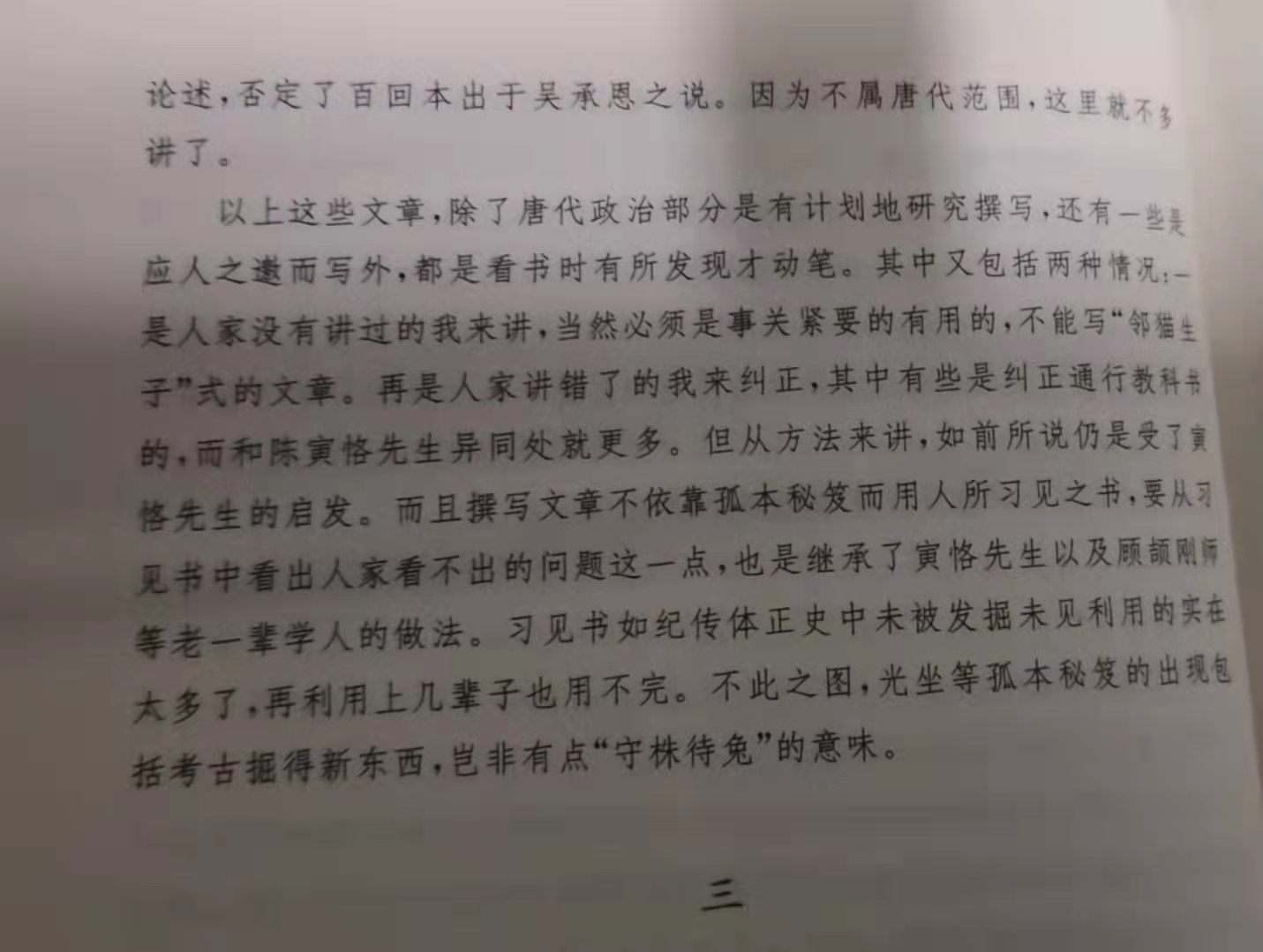
如上所述
我从未想到,年代四部曲的坑还未填,“谈一谈史料”却快成一个小的系列了。黄永年和辛德勇两位老师的史料观,和学界的通行观点是有差别的。(黄永年先生是辛德勇先生的老师)
学界的一般观点是什么呢?是掘地三尺,去土里或各种边边角角里,找新的材料。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虽然并不那么“科学”,但历史研究也属于广义上的“科研”工作,进而历史学者就也要“卷”——也要发文章,出成果。
这就不得不提到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创新性原则。从哪里创新呢?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材料。这三个方面里最好搞创新的,就是材料嘛。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的论文是要过查重的。引用的史料飙红,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与此相对应的是黄永年和辛德勇两位先生的观点:历史研究要走大道、走正道。
上面大家也已经看到,黄永年先生斥这种把创新的希望放在考古掘出新材料的做派为“守株待兔”。认为习见书——正史和其他传统史料中,还有很多值得发掘利用的内容。
我的《文选》老师曾经提到公文纸背的问题。(“公文纸背”是古籍版本学的叫法)在宋元时期,流行一种蝴蝶式的书籍装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古人常用用过一面的纸的背面印书。这些古籍保存到今天,学者们整理被古人认为是废纸的书页背面,找到了很多新的原始材料,这就是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当然,公文纸背不一定都是“公文”,也不是都来源于蝴蝶装古籍。关于公文纸背的研究方兴未艾,新的方向,新的一手材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真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
辛德勇老师显然不在此列。壬寅年春节,辛德勇先生做了一次关于古籍版本学的直播,互动时,我请教了一下辛德勇先生对“公文纸背”的看法。先生对公文纸背研究很是不以为意。认为这种不看正面看背面,去边边角角找材料的行为纯属吃饱了撑的。认为公文纸背文献如果必须要用的话可以用(可以但没必要)。最后,辛老师告诫道:“历史研究一定要走正道”。实在是振聋发聩。
我又想到,黄永年和辛德勇两位先生,与北京大学的田余庆等其他几位先生关于《资治通鉴》和汉武帝晚年政治转向问题的争论,也可以通过这种史料观上的差异来解释。
关于汉武帝晚年究竟有没有转变其政策的“商榷”已经延续了千年。去年《文史哲》的那篇文章把大家的目光又引到这个问题上来。我没有能力去研究司马迁和班固谁说的对,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至于去年的争论,实在是过于饭圈化了,当事双方、粉丝、黑粉和吃瓜群众乱成一锅粥,不好也没有必要去评价。所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黄永年、田余庆、辛德勇几位先生身上。
相传,北大搞秦汉史的先生们,有带着研究生读《资治通鉴》的传统,这一派的代表作自然便是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与之相对的就是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田余庆等各位先生为什么重视并使用《通鉴》呢?因为秦汉的史料太少了。辛德勇先生为什么反对呢?因为他认为《通鉴》不足信——毕竟《通鉴》是二手史料,而且里面满是司马光的私货。
最后,有争议是好事,有争论学术才能发展。如果没争论了,或者说大家都想着用学术范围外的手段去让对方闭嘴,去搞“武力征服”那我们就遇上大麻烦了。我一无名小卒,没有资格参与大佬们的争论,君不见社科大的副教授都没资格掺合进去吗?甚至我连实践一下大佬们的某一种史料观点的资格都没有。但这并不影响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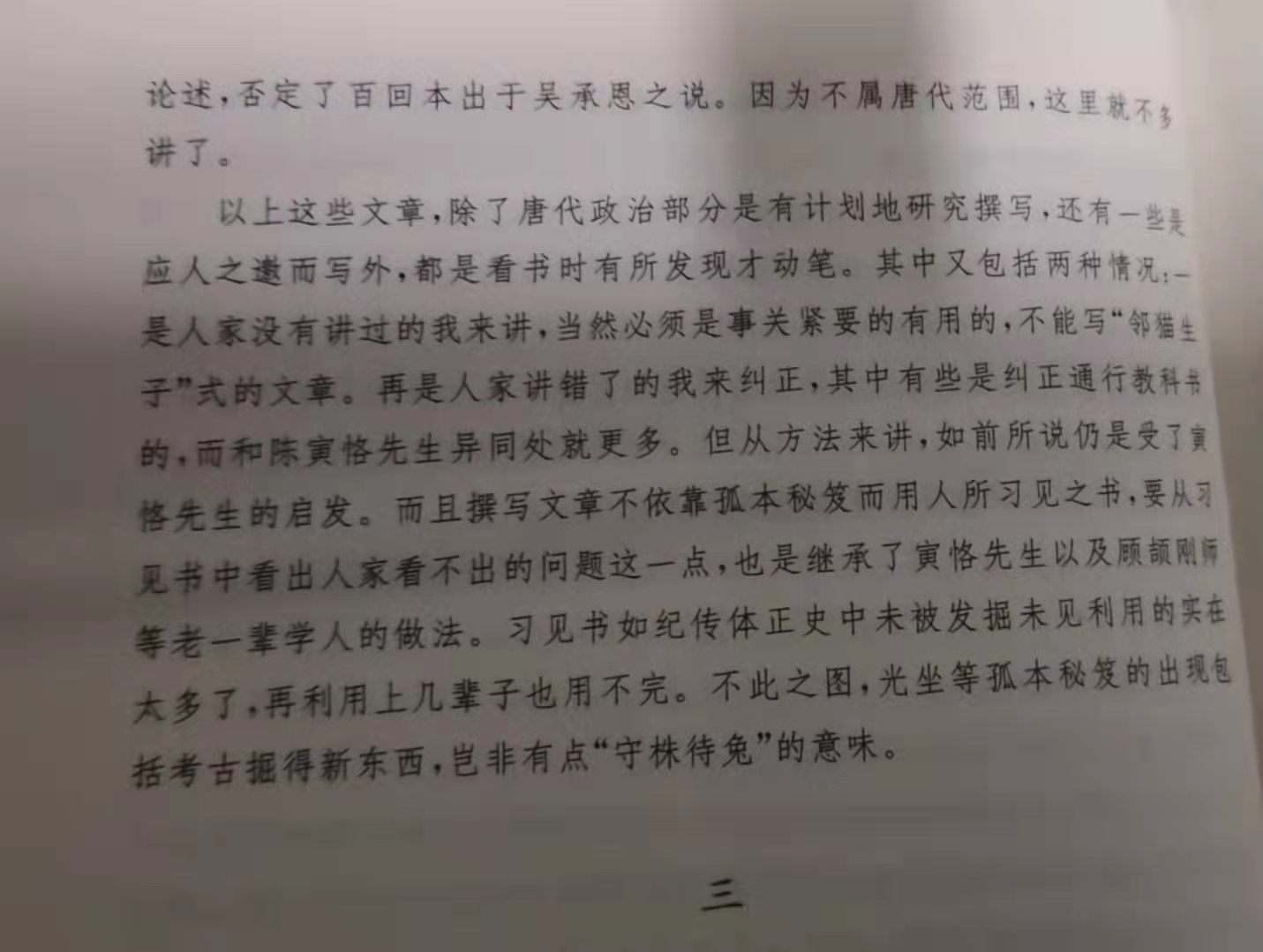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