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马小红
近代“罪刑法定”的原则包括两个基本的含义,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这个原则近代以来风靡全球,为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认可并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也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强调严格依法定罪的宗旨在于防止法官罪行擅断,以保护人权。

但是,作为一种思想与人们对公平正义理想的追求,罪刑法定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更不是西方传统所独有的。其实,儒家所强调的断狱得其“平”,法家强调的“一断于法”都含有罪刑法定的因素。尤其儒家经典将历代断狱的有益经验总结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疑罪从赦”等,更是体现了罪刑法定的因素。法家的“一断于法”虽然就思想而言,也有罪刑法定的意思,但由于其将刑罚置于了“万能”的境地,不仅造成了立法的困境,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会发生轻罪重判及无罪罹刑的状况。汉代以后,法家思想受到批判,而儒家用刑以“平”的思想得以确立。与学界通识有点不同的是,儒家思想的确立并没有削弱人们对罪刑法定的追求,反而为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注入了丰富的元素。
以儒家为本的中国古人“罪刑法定”的出发点似乎较我们现代保护人权来得更“实在”和“人文”一些:“实在”表现在古人的罪刑法定目的直截了当,就是为了防止冤狱;“人文”则强调断狱者要心存怜悯,体恤民情,以德礼教导民众,使民众远离犯罪。这种警惕冤狱与宽仁的儒者之心在班固撰写的《汉书∙刑法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班固以“向隅而泣”的典故告诫统治者要警惕冤狱的发生,因为一桩冤狱会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气氛。班固说:“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悽苍于心。”大意是,如果一家人都在饮酒欢乐,但有一个人面墙而悲泣,那么一屋子的人都会为之不乐。一个仁义的君主统治天下,对于天下的苍生,就如同家长之于家庭成员,只要有一桩冤狱发生,也应该心有凄然不安。班固继续用孔子的话告诫统治者,要谨慎用刑,尤其对于死刑应慎之又慎。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立法用刑的目的不是为刑而刑,恰恰相反,用刑的目的在于“省刑”,甚至在于“刑措不用”。《汉书∙刑法志》这样说道:“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大意是:“孔子说:‘古代熟知法律的人知道用刑的目的在于减少犯罪,少用刑,这是用刑的根本目的;而现在熟知法律的人为的只是用刑罚惩罚犯罪,这不是用刑的根本,而只是用刑的枝节问题。’又说:‘现在断狱的人在量刑定罪时往往重判,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古代断狱的人则对罪犯心存怜悯,希望能保全他们的性命。’用刑原则应该是宁愿漏判有罪之人,也不要冤杀无罪之人。”
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也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与罪刑法定相对的罪行擅断也并不罕见,但古人对罪刑法定的追求也不曾间断。晋代律学家刘颂上疏,期望“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大意是:量刑定罪应当依据法、律、令的正文;如果正文没有规定,则按照名例律的原则判处;如果正文、名例都没有规定,则不为罪。“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何等的相似!古人的坚持也并非毫无成效,距今约一千四百年的《唐律》中赫然出现了这样的条款:“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违者笞三十。”即:定罪必须引用律、令、格、式,违反者,判断狱官笞三十之刑。断罪必须引法律条文、以法为据是对法官法律知识与观念的考验,也是对罪行擅断的限制。
对罪行擅断的限制不只存在于立法中,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籍中,司法实践的案例可以随手拈来。让我们看一下《后汉书∙郭躬传》的记载。郭躬出身于法律世家,他的父亲郭弘是州郡职掌断狱听讼的“决曹掾”(官职名称),史家称他“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他所断的案子,涉案人员无论是被释放还是被判刑,都心服口服,没有喊冤者。“仁者寿”——这位判案公允“积有阴德”的老者一直活到了九十五岁才离世——在古人眼中这是上天对断狱心存仁义悲悯之心的人的莫大奖赏。郭躬则子承父业,深谙儒家心存悲悯、“疑罪从赦”的断罪之道,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言行予以赦免,对可轻可重的案件从轻发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一位名叫秦彭的武将作为副帅随主帅窦固出击匈奴。秦彭与窦固兵分两路,各自安营扎寨。秦彭在没有请示主帅窦固的情况下,依据军法而处死了一位下属,窦固以为这是擅权之举,上奏朝廷,请求处秦彭极刑。明帝召集朝臣公卿议处此事,郭躬以深谙法律的原因也被诏入朝。朝臣公卿几乎一边倒地以为窦固所奏有理,应该处秦彭“专擅”之罪。而郭躬认为:“依据法律,秦彭有权斩杀下属。”明帝反问道:“在征伐的过程中,军队中的一切都要听主帅的命令,秦彭是一名副帅,手中也没有可以处决死刑的斧钺(权力),难道他可以不经过主帅的同意专擅杀人吗?”郭躬则根据法律分析道:“征伐中的军队一切听从主帅之命,是指主帅亲自所率领的将士而言。
而秦彭的情况有别于此。秦彭单独率领一支军队行动,虽然没有主帅的斧钺,但也持有证明身份的棨戟。征伐的过程中,战况瞬息万变,独自率领军队的将领无法事事先禀告主帅,更何况汉制规定‘棨戟即为斧钺’。所以,根据法律,秦彭无罪。”明帝以为郭躬的分析有理,因此而判秦彭无罪。《汉书∙郭躬传》还记载了郭躬所判的另一疑案。也是明帝永平年间,有兄弟两人共犯杀人罪,但断狱者分不清谁是主犯。案件上报到朝廷,明帝以为,兄弟共同杀人,在分不清主次的情况下应该将兄长判为主犯重判,因为兄长负有教导弟弟的职责,两人共犯杀人罪,显然是“兄不训(教导)弟”的缘故。中常侍孙章在宣读诏书的时候将重判兄长误说成重判兄弟两人,尚书因而上奏,弹劾孙章“矫制”,罪当腰斩。明帝又诏郭躬,询问他的意见。郭躬认为,对于孙章的这一行为,应该判处罚金。明帝不解,反问:“孙章矫诏杀人,难道就只判罚金?”言下之意是处罚太轻。郭躬依据法律分析:“法令规定,犯罪分为故犯和误犯两种情况。误犯从轻。孙章传错了诏令,应该属于‘误’,按法律规定应该从轻发落。”明帝仍有疑惑,说道:“孙章与那杀人的兄弟两人是同乡。因此,我怀疑他是故意传错谕旨,以报私仇。”郭躬再次为孙章申辩道:“周公开辟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的平坦(‘周道如砥’,即公平),像离弦的箭一样笔直(‘其直如矢’,即正直)。
孔子也说过君子不能心存恶意地揣测别人的言行(‘君子不逆诈’)。君主应该效法上天,公平正直,量刑时要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不要妄加揣测而牵强附会。”明帝赞叹道:“善。”郭躬与明帝间的问答,充满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相通的精神。对孙章传错谕旨的行为,郭躬心存仁厚地认为是“误”而不是“故”,“误”应从轻判处。他反对明帝主观臆测,认为“君子不逆诈”,无证据证明孙章是“故”,那么就只能从轻认定为“误”。其实,值得一起赞扬的还应该有明帝那种从谏如流的胸怀,面对臣子引经据典的批评,能给予真诚的肯定和采纳。难怪史家以战国曾子的话来盛赞郭躬与明帝断狱是“哀矜勿喜”。
在中国古代如郭躬一样的执法者并不匮乏,因为主流思想及价值观认可的循吏基本都是主张“疑罪从赦”或者“从无”的。宋人郑克编写的《折狱龟鉴》,将“释冤、辨诬”作为刑狱的头等大事,放于首篇、次篇,可见古人对定罪量刑的审慎。如果我们不是人为地去划分古代近代的区别,不是过分地将古代法与近代法对立,就不难发现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的相通之处,甚至可以在现代法律中注入古人的智慧,使现代法律的内涵更加合理与丰富。比如,通过学习古人的罪刑法定,我们可以为现代的罪刑法定注入新的内容,可以在制约权力的同时,强调法官的自身修养,因为哀矜勿喜的仁者之心与保护人权的罪刑法定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兼具更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检察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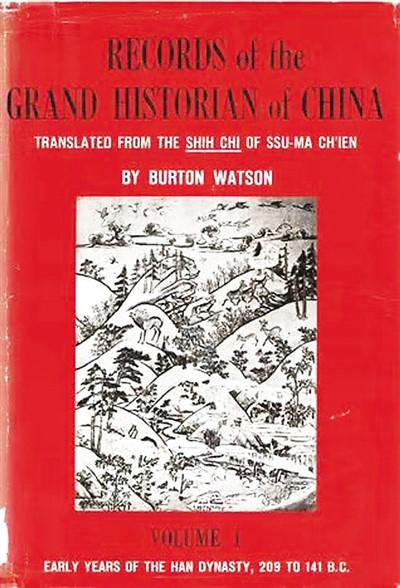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