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兴盛于宋代。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这是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鲁迅先生和胡士莹先生对此均有详细论述。但近年来,鲁迅、胡士莹等先生的观点受到质疑。如刘世德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即依据日本学者研究的成果,提出了话本就是故事的观点。问题是,宋元话本是否有更早的源头?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地认识话本的起源及指涉有重要意义。
其一,话本有更早的来源,仅仅把它视为宋元以后民间艺人即说话人的“底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现存的唐代敦煌写卷就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韩擒虎话本》结尾处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一语,“画”通“话”,“画本”就是“话本”。从语法结构上看,“韩擒虎”与“庐山远公”均为主语,同属称谓。“话”与“画(话)本”词义相同,可以互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以后。明瞿佑《剪灯新话》卷二《牡丹灯记》云:“伏念某青年弃世,白昼无邻,六魄虽离,一灵未泯。灯前月下,逢五百年欢喜冤家;世上民间,作千万人风流话本。”《剪灯新话》中的“话”与《牡丹灯记》中的“话本”同义。明代佚名《刘生觅莲记》云:“因至书坊,觅得话本,特持与生观之。见《天缘奇遇》,鄙之曰:‘兽心狗行,丧尽天真,为此话者,其无后乎?’见《荔枝奇逢》《怀春雅集》,留之。”“话本”与“话”同义,可以互换,即“话”是“话本”的省称。据此,“庐山远公话”实际上是“庐山远公话本”的省略语,在表述上与“韩擒虎话本”相同。这表明,唐代俗文学已有“话本”这一艺术门类。
其二,唐代文人有将“传”改称为“话”的做法,并直接参与到话本的创作之中。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诗句,这里的“话”是指《一枝花话》。元稹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尤未毕词也。”宋代罗烨指出:“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进士出身,著有传奇《李娃传》,据此可知,“话”与“传”通,“说《一枝花话》”是指复述白行简的《李娃传》,“话”与“传”为同义语,两者可以互换。关于“话”“传”可以互替,还可以从宋话本《杨温拦路虎传》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杨温拦路虎传》的语言结构与敦煌写卷《庐山远公话》相同,亦可知在唐传奇及宋话本中,有将“话”与“传”互换的现象。
其三,“话”与“语”同义,唐代时常交替使用。南朝刘义庆有《世说新语》,唐人刘肃有《大唐新语》、刘有《隋唐嘉话》,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收录唐人著述有赵璘的《因话录》、韦绚的《刘公嘉话录》,宋代李昉《太平广记》收录唐人著述时又有《大唐杂语》《唐语林》等。从语义上看,“话”与“语”同义,承担对象一致。从著述内容看,“新语”“嘉话”“话录”“杂语”“语林”表达的意义相同,旨在记载当代人的言行及事迹。
其四,追溯源头,“话本”称谓的出现与传播佛教有直接关系。据文献,“话本”一词最早出现在敦煌写卷中的变文里,直接以“话”“话本”名篇的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话本与佛教的关系,还可以从宋代普济《五灯会元》中得到明证。《五灯会元》卷三《六祖大鉴禅师法嗣·百丈怀海禅师》云:“时沩山在会下作典座。司马头陀举野狐话问典座:‘作么生?’座撼门扇三下。”百丈怀海禅师是马祖禅师的得意弟子,长期侍坐于门下。《五灯会元》卷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云:“(马祖禅师)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唐开元中,习禅定于衡岳山中,遇让和尚。同参六人,唯师密受心印……大历中,隶名于钟陵开元寺。时连帅路嗣恭聆风景慕,亲受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普济记载禅宗故事多有所本,《百丈怀海禅师》中所说的“野狐话”应盛行于唐代。其实,“野狐话”“远公话”“韩擒虎话本”都是为弘扬佛法讲述的宗教故事。从这样的角度看,话本与唐代佛教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其五,唐人眼中的话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话”指故事,与叙述历史人物、事件有直接的联系。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列传》:“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二是“本”有来源、依据之意。晚唐五代词人牛峤《灵怪录》云:“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其中的“本”就是来源之意。
其六,唐人话本继承了史学传统,“话”与“事”同。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郑朗列传》云:
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朕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诫丑言。”朗遂进之。朗转考功郎中。四年,迁谏议大夫。”
按,“故事”“闲话”上承“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即“史官所述,不隐善恶”的文化精神。
其七,唐代话本有文白并存的现象。白话可以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为代表,文言可以笔记为代表。如《大唐新语》《隋唐嘉话》《因话录》《刘公嘉话录》《大唐杂语》《唐语林》等多是引用的对象。又如后人注《旧唐书》《旧五代史·唐书》时多次引用王仁裕《玉堂闲话》。宋代薛居正《旧五代史·唐书》卷六十一《安金全列传》云:“弟重进,尤凶恶。事庄宗,以试剑杀人,奔淮南。”注引《玉堂闲话》:“安重进,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后携剑南驰,投于梁祖,梁祖壮之,俾隶淮之镇戍。复以射杀掌庾吏,逃窜江湖,淮帅得之,擢为裨将。”《玉堂闲话》的作者是晚唐五代王仁裕的笔记轶事小说集,散见于《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说郛》《永乐大典》等著述中。
综上所述,早在唐代已有话本,在唐人的眼中,话本或话所指甚多,一方面唐代话本与俗文学即变文、讲经等宗教故事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唐代文人有将话本与野史笔记等同起来的意识,话本在文人的眼中与野史笔记、传奇(小说)是同义词。厘清这一问题对于全面认识宋元话本及叙述方式和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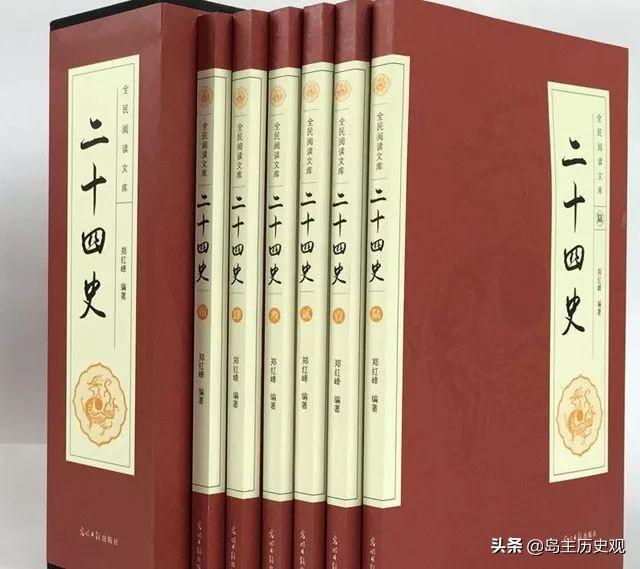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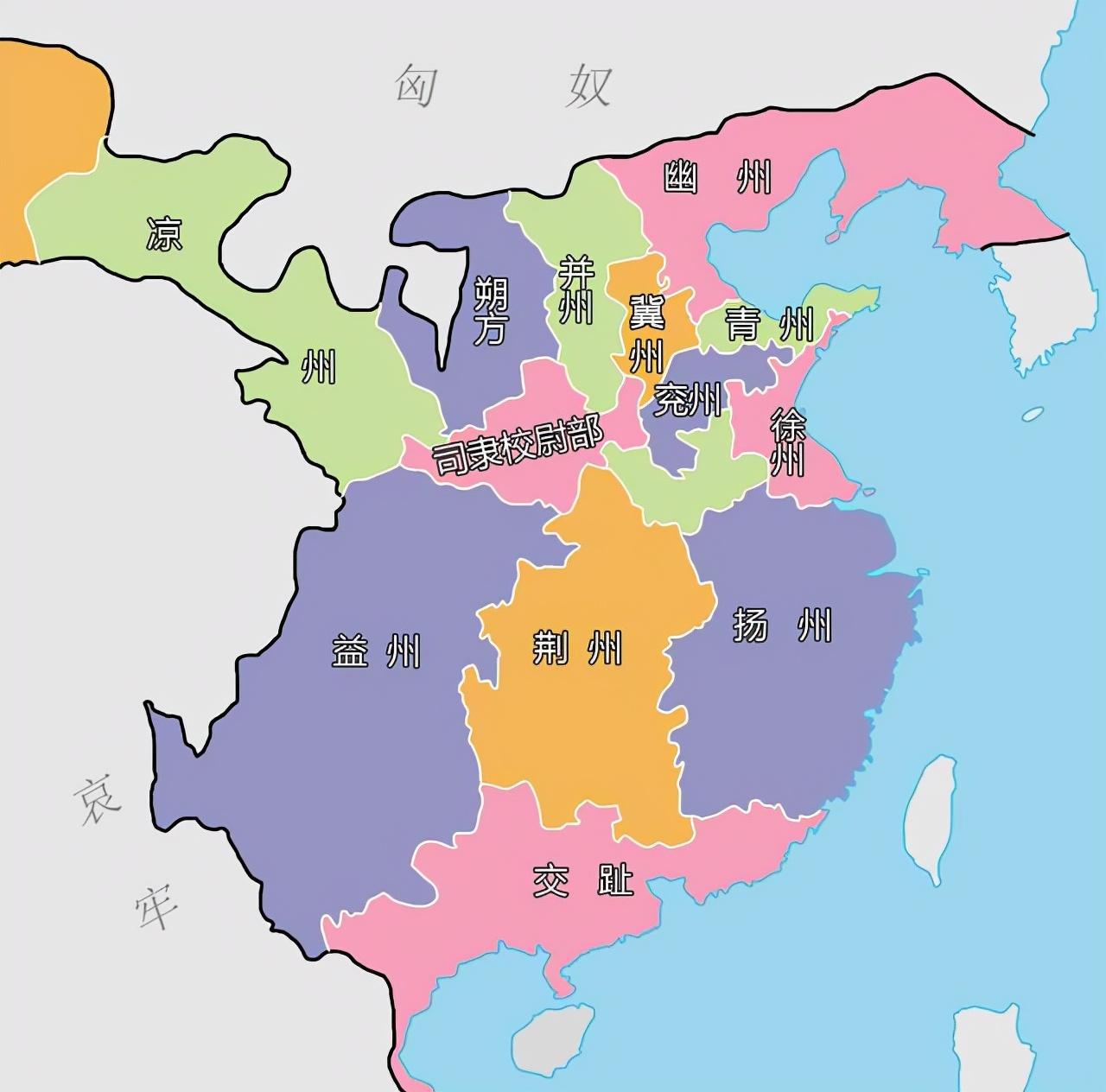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