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两大要素,“问题”的生发有赖于“材料”的运用和解读,“材料”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着“问题”的解释与探讨。陈寅恪先生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近几十年来的学术发展证明了“材料”与“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大量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北朝隋唐墓志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激发出众多新的学术议题,备受关注,成为推进秦汉至隋唐历史研究的一大新动能。自宋代以下,传世文献浩如烟海,随着大量典籍的影印出版与整理点校,加之计算机检索技术的应用推广,“材料”的不断“涌现”亦支撑着宋元明清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相较之下,在各断代史中,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素以史料匮乏著称,传世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出土石刻资料亦无法与隋唐碑志等量齐观。那么,新一代的辽金史学人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中精耕细作,进一步推进辽金史研究,便是很有价值的讨论议题。2018年3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青年史学工作坊第89期学术活动,以“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为主题,邀请青年辽金史学者进行漫谈式的研讨,有助于我们探索和反思辽金史研究中的“材料”问题。
此次漫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丽巍老师主持,邱靖嘉担任引言人,受邀与谈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康鹏、孙昊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博士。其他参与讨论的学者有包伟民教授、张帆教授以及胡恒、胡翔宇、周施廷、杜宣莹、张亦冰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青年教师。
本活动属于人大青年史学工作坊之“史料工作坊”系列。首先,古丽巍介绍了此次漫谈会的缘起和各位引言人、与谈人的学术背景,并向各位参会的老师、同学表示欢迎和感谢。

活动现场
随后,邱靖嘉作为引言人,对此次漫谈会的主题做了解释说明。在各断代史研究中,辽金史最为薄弱,尤其与前后相承的唐、宋、元史研究相比,更显萧条,造成该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料的缺乏。目前,研治辽金史主要依靠的还是《辽史》、《金史》两部元修正史,辽金时期的传世文献,确为辽代的仅有一部韵书《龙龛手镜》,金代尚有《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以及几部金人文集,数量少得可怜,出土石刻资料也不如唐宋丰富,而宋元文献有关辽金王朝的记载十分零散,不易搜检。虽自近代以来,几代辽金史学者利用有限的史料奋力开拓,已取得可观的学术成果。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材料”问题一直是制约辽金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约十年前,刘浦江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一文,曾谈及这一问题。据他粗略估计,“辽金史史料仅及宋代文献资料的三、四十分之一”,“尽管材料如此匮乏,但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传世文献资料仍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传统史学方法也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到极致”,并指出从辽金史研究对于史料的利用应从此前的“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那么我们该如何“精耕细作”呢?这就直接催生出本次漫谈会的主题“辽金史料的深翻与检讨”,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试作解题。
第一,大力发掘辽金史的新资料。辽金史料虽少,但若深入翻检、挖掘,其实仍可发现许多尚不为人知的新史料。刘浦江教授即已指明方向,提示应“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间”。近年来,已有一些青年学者循此路径,从宋元类书、明清方志等书中搜掘出一些新的辽金史料。此外,辽金石刻资料亦需进一步搜集与整理。
第二,对已有辽金史料的深入分析与研究。传世的辽金史料往往来源复杂,既有源出辽金官方记载者,也有宋元人的转辗讹传,需要从史源学的角度加以仔细辨析,去伪存真。如元修《辽史》、《金史》各部分史料来源不同,间有元朝史官的叙述,可信度有别;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载女真史料历来引用者甚多,孰不知此卷系徐梦莘杂采诸说剪裁拼接而成,其中颇多讹误,需提高警惕。另外,如《册府元龟》、《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大部头史籍记有许多辽金史事,虽略为人所知,但尚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和研究。
第三,对于辽金史料的批判与检讨。在明晰史料来源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其历史记载的文本是如何生成的,并将其置于当时的情境之中去加以解读,以期了解编撰者的心理和意图。这就牵涉到当下比较时髦的史事建构和历史书写问题,对于辽金史研究而言可谓是一个崭新的视角,通过批判、检讨既有史料,我们可能会生发出新的历史认知,甚至颠覆某些熟知的“历史常识”。比如今本《辽史》、《金史》的编纂过程十分复杂,若对其历史记载体系加以解构,或许可以看到辽金历史的另一面相。

邱靖嘉《纂修考》
其后,三位受邀嘉宾围绕上述主题,结合各自的研究心得,分别做了回应发言。孙昊最初因受博导杨军教授影响,研究《金史·世纪》而进入辽金史领域,对早期女真历史记述做过系统梳理和研究,出版《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书。他认为辽金史材料虽少,但并非已无可做的余地,需要结合上述三个方面加以深翻与检讨,也要重视理论“常识”的转变对于理解文献,尤其是民族史文献的重要意义。
孙昊认为对于传世女真文献资料的“深翻”,有赖于理论“常识”的转变。长期以来,一些“孤岛式”民族志理论在许多研究者观念中形成了先入为主的错误“常识”,影响到他们对文献史料的理解。正确的研究方式应从分析史料记述的社会语境入手,然后再与特定的理论观点对话,得出新知。他的《金史·世纪》研究就循此思路,首先梳理文献记载体现出的社会关系,厘清史料与史料之间、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系及其基本属性;其次,对女真各部族的分布情况做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地理空间层面扩展有限的资料,揭示出更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从这两方面出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通过地理位置能判定,《金史·世纪》记述的“完颜”仅是一个“部姓”而已,并不能像学界旧识那样,将之释做实然存在的血缘性的氏族、部落组织。通过仔细梳理各部族、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相关女真文资料,能够获知《金史》所载某某部、某某族、某某家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最后结果可以证明,学界传统旧说与女真人早期的社会观念不相符,那么就有必要对看似已经没有挖掘空间的常见文献资料进行重新认知。另外,要充分意识到文献的文类特征与编纂目的,把握其撰作的语境、目的。就民族史而言,应尤其重视古代民族志记述的文本语境对读者的影响。这一点从宋人关于女真的知识谱系的反思即可见到。孙昊在梳理《宋会要》、《辽史》、《三朝北盟会编》、《高丽史》诸书的女真记述时,发现各方记述的女真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和语境之中,遮蔽了女真自身的政治取向和族群分异实态,因此在运用此类文献时,应当辨明其文本形成之语境与知识来源,而不是简单引用,泛泛而谈。

孙昊《辽代女真族群与社会研究》
在对历史文献记载进行深入剖析和检讨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总结一些有益的思考。此前原始社会向早期国家发展的酋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北族王朝的研究。因为无论是酋邦,还是部落联盟,其预设前提都是这个民族在没有受到周边社会影响,处于一个独立的、缓慢的自我发展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符合中国北方社会多民族交融、相互影响的发展实际。近些年来流行的所谓“内陆欧亚”视角,与传统中国民族史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这些学者并不承认北方社会的原始性或落后性,而认为北方的内陆欧亚社会是具有历史独特性的社会发展主体,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历史发展逻辑,不能用“原始社会史”的观念来理解。内陆欧亚视野下的北方民族相互联动的观念,无疑为孙昊的女真史研究拓宽了出口和可能性。
孙昊现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工作,合作导师李锦绣研究员一直以内陆欧亚学作为本室学科建设的核心。受这种有利环境的影响,他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从事东北亚民族与内陆欧亚或内亚草原的关联性研究。他认为东北民族的发展与整个欧亚草原紧密相连。这一点并不仅体现在内亚文化的相似性,更多地体现在多族政治互动直接导致了东北民族的一些政治概念和政治关系的产生。美国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所著《危险的边疆》(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提到,东北民族往往是拾荒者,利用北方草原和南方农耕定居族群两败俱伤的机会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东北民族可以同时吸收南北两方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孙昊最近关注渤海国问题,也发现渤海王权的建构事实上凝聚了北方草原可汗正统性和唐代政治传统双重因素。因此,东北民族的发展可能较我们之前所了解的更为复杂。
理论不仅是一种视角和问题意识,还是挖掘史料新义涵的方法、工具。20世纪40年代政治人类学的“非洲经验”(参见[英]M.福蒂斯、E.E.埃文思·普里查德编《非洲的政治制度》,刘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促使后来的研究者意识到所谓亲属关系组织起来的社群,其实都是一种政治组织,这影响到此后研究问题意识的转向,并成为当代内陆欧亚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思考出发点(如[美]Lindner, “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4, Issue4,1982,在国内近年罗新老师亦大力倡导)。这是政治人类学社会“常识”之更替促使历史现象认知改变,进而影响我们对现有常见史料理解的典型例证。因此,我们应充分跟踪,采用多学科的“常识”,投入到我们自身的“田野”工作——文献解读过程之中,变“常识”为“工具”,与文献所记述之语境进行深入对话,也能够得出新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通过自身的“田野”经验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在一个共同关注的理论层面进行对话、相互借鉴。
最后,孙昊总结其研究心得,指出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含多民族语言的文献)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历史地理、阿尔泰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在此基础之上,理论“常识”的转变对于阐释史料是最为重要的,但前提是对于任何一种新的“常识”或理论,一定要像追溯史源一样地追究它们的知识源流,明确其终极问题趣旨,才能将其变为自己阐释与深翻史料的得力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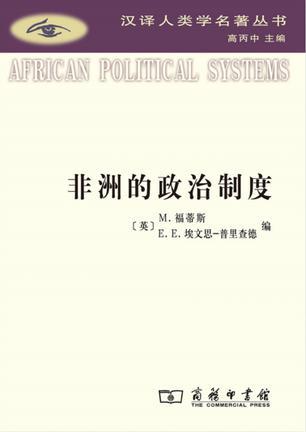
《非洲的政治制度》
苗润博将引言人所说的开拓新史料、对既有史料的深入考索和重新解读三方面问题概括为史料的“加法”与“减法”。在一般情况下的历史研究,或者说是积累阶段的历史研究,需要做的往往是史料的“加法”。就是多一条材料,我们的解释力似乎就多了一点;看到一个系统记载,就以其作为纲目,在此基础骨架上填充血肉,即搜罗更多材料证明已有的叙述和知识。这似乎是历史研究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所谓“深翻”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做“减法”。我们一方面可能会面对支离破碎的史料,另一方面还可能要面对史料背后透露出的整体叙述。一种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连续性越强,越容易被我们先入为主地接收,然而这样的历史叙述其实更加需要警惕。面对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应该是抽丝剥茧、正本清源,通过区分不同叙述主体、不同来源的史料,剔除干扰性因素,必要时需要以打破既有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方式来求得新的连续性。
以他研究的早期契丹史为例,“契丹”一名在公元4世纪末出现,直至公元10世纪初建立契丹王朝(即辽朝),建国前史大概有五百多年,以往我们讲述这段历史时,很多时候是以元修《辽史》关于这五百多年的历史叙述为依据,将其作为一种“常识”或者研究的基础。但如果深入分析这套历史叙述,不禁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辽朝契丹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建国以前的历史?元朝史官所总结的发展脉络是否符合辽朝当时人的历史记忆或曰历史叙述?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时,我们就要进行史源学的考索:元朝史官有关契丹早期历史的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实际上,这套历史叙述有两个不同的文献来源:首先是中原文献呈现了一套关于契丹早期历史的系统叙述,从《魏书》开始设置《契丹传》,到唐宋时期正史一直相沿不辍;其次是,元朝史官修《辽史》时尚能看到少量零星的辽朝人自身的历史叙述。出于一元线性历史叙述的思维习惯,元人理所当然地将辽朝文献和中原文献所记建国以前的契丹历史叙述进行了杂糅和拼接,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苗润博的研究首先就要将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进行拆分,做史料的“减法”,去除掉能够确定出自中原文献系统的记载以及元朝史官根据己见所做的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式的嫁接、粘合与改编。当把中原文献对契丹早期史的记载与元朝史官关于契丹早期史的想象剥除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或保留辽朝自身的历史叙述。这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辽朝自身的历史叙述居然与我们在《辽史》和中原文献中所见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减法”的作用。在层层剥离史料的过程中,传统史源学的追索与现代问题意识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苗润博还回应了民族史研究中的“汉化”命题。最近有学者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解释辽朝整个历史的发展,提出自辽太祖阿保机开始便采用全盘汉化的建国方略。但根据苗润博的研究,我们在《辽史》中看到的辽朝中前期历史其实经过了辽后期的改写和重塑。汉化渐深的后期史官有意对辽朝开国历史进行了伪造和建构,并重新书写了辽中前期的历史叙述。如果不加批判地采信这样一套叙述去研究阿保机时代及辽朝中前期的历史,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充当了辽朝后期史官的现代翻译者,而不是批判者。
苗润博总结道,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的许多领域纷纷超越传统精耕细作阶段,进入后现代的史学反思即思考历史书写这一层面的问题时,辽金史研究某种程度上还在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徘徊,在史料“加法”还未做好的情况下,同时要面临做“减法”的问题。不过,反过来说,辽金史研究也有后发优势,可以有意识地借鉴后现代或是比较成熟的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方式,立中有破,破中有立。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史料的“加法”而是“减法”,毕竟对于辽金史学者而言,史料的“加法”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史料的“减法”则是义不容辞的。

《辽史》
康鹏主要谈论了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对于深化辽金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契丹、女真王朝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前人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汉文的传世文献,无论是中原王朝的史书记载,还是辽金王朝编纂的国史,仅仅看汉文的历史书写往往是片面的,无法充分理解辽金王朝的某些特殊性,这就需要依靠契丹女真语言文字资料的解读与研究。例如,刘浦江老师研究的契丹父子连名制问题(《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此前研究者已意识到契丹人的第二名很特殊,但如果没有契丹文字资料,我们是无法知晓其规律性的。又如,从汉文记载来看,契丹人的姓氏只有耶律和萧两姓,但实际上,萧姓在契丹文字中是没有的,目前契丹大小字石刻记载的都是这些萧姓契丹人的具体部族名,如述律、拔里、乙室己等,由此看来,萧姓可能是对汉人的一种宣称,同时又是凝聚其他民族的一个工具,如奚人皆姓萧。再如,辽朝国号问题,汉文记载辽朝曾多次改国号为“辽”或“契丹”,但据契丹文墓志可知,辽朝始终实行双国号制,称“辽·契丹”或“契丹·辽”(刘凤翥《契丹文字中辽代双国号解读的历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以上这些例证表明,通过将汉文记载与契丹文字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契丹人独特的想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现存的契丹语言文字资料除了契丹大小字墓志以外,在域外文献中也有可能保存一些零星记载,如《马卫集》等阿拉伯文献。总之,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还有很大的深入挖掘空间,而且它们恰恰可以从契丹人的角度去理解辽朝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值得大家关注和利用。
在三位受邀嘉宾发言之中,进入自由讨论环节。张帆教授对于孙昊、苗润博从史料“减法”的批判视角来检讨辽金早期的民族发展线索、建国道路等问题表示赞赏和支持。按说有关辽金早期历史的资料很少,十分珍贵,但经过他们的批判和剥离之后,也许反而能呈现出比原来更加清晰的画面,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不一定对其他民族史研究也适用,比如蒙元的历史记载可能就不大容易进行剥离。由于辽朝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少,《辽史》成书很晚,在编纂过程中会加入许多错误的历史知识,甚至是史官的比附、猜测与想象,所以《辽史》叙述的契丹早期历史很可能与契丹人真实的历史不是一回事。《金史》情况稍好,但也有一些后世史官建构的成分。而元朝有成书很早的《蒙古秘史》,尚未受到中原王朝观念的影响,其记载相对比较可靠,恐怕暂时还无法对其加以批判和剥离,这有待于今后的学术发展。同时,张帆教授还提示应关注金朝作为中原历代王朝中的一环,如何与此前的唐宋及之后的元朝相接轨与过渡的问题,并深入体会和解读史料背后的历史信息。历史总是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有些问题看似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但如果深入考究之后,或许会完全颠覆我们的既有印象。另外,对于初涉史学者而言,史料批判、剥离式的研究方法需小心谨慎,应在充分读懂、理解史料的基础上再追求创新。
包伟民教授并不觉得史料的多寡是一个问题,对于同一个学者群而言,面对同样的材料,如何做出出类拔萃的研究才是关键,这也是一种考验。有的断代史资料太多也有自身的问题,学者研究往往会流于资料的排比,而疏于深入解读,比如宋史研究对资料的解读总体上不如唐史研究精心。关于民族早期历史的叙述多虚无缥缈,有较多后人建构的内容,其实这种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其他历史中也常常存在。以浙江龙泉民国司法档案所见为例,司法诉讼双方呈交的契约如何书写受到诉讼制度、法律条文、具体情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了解文本背后的书写目的。又如地方大族往往会有意地将捏造的本宗族、家族历史塞入地方志的编纂之中,等若干年后编修家谱时再从方志中抄出,这样私志摇身一变就成为官修“信史”。因此,在了解了某些通例和制度之后,再去谈史料的“减法”问题可能更为妥帖。包伟民教授还指出,以前我们往往会不假思索地接受前辈学者建构起来的说法,很少提出质疑,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以及研究条件、手段的进步,思考中国史学如何继续往前推进,除了开拓新领域之外,其实已到了对以往习以为常的成说进行检验和反思的地步。

刘浦江《宋辽金史论集》
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几位青年学者也参与了讨论。张亦冰介绍了宋史研究的资料状况,并结合宋代经济、制度史研究,指出宋代也有类似历史书写的问题。古丽巍对所谓史料的“加法”和“减法”问题做了回应,认为有时研究中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就“加法”而言,并非辽金史所独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历史早期不少都会出现所谓“层累造成的历史”、“英雄祖先”之类的现象,主要看讨论的对象如何灵活地运用史料。而“减掉”的史料也不一定是废料,或许换一个视角就是有用的材料,所谓“书写”更应该看成一种研究的多维视角。胡恒就辽金史料问题反观清史研究,清史的问题在于史料太多,除众多传世文献典籍外,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这种状况对于清代地方史研究带来的困扰是呈现出了很多的细节,并且以为它们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但其实如果仔细读《大清会典》会发现,其实我们此前并没有真正理解清代中央的制度规定,而误以为那些细节体现了什么地方性,因此清史研究也需要加以深翻。另外,清史研究如何避免碎片化的趋势,怎样在若干地方化、区域化的具体研究基础上提炼出一些更具解释力的框架,这也是清史研究面临的一个挑战。周施廷、杜宣莹从世界史的角度,分别介绍了欧洲宗教改革和英国史研究中的档案资料利用情况及其相关问题。现场同学也就新旧《五代史》中的契丹史料、辽金经济史研究、《高丽史》中的女真记述等问题纷纷提问,由在座老师一一作了解答。
此次漫谈会氛围轻松愉悦,各位发言人事先均未作周详准备,然而讨论时围绕主题各抒己见,多有精彩言论,颇具启发性,达到了良好的效果。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断代史学研讨会不计其数,但其中很少见到辽金史的身影,这也间接反映出目前辽金史研究的弱势状况。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以辽金史为主题的学术活动,在这方面青年学者理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