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各有特色各具风貌的人物形象,其中又以占据重要篇幅地位的女性形象最为夺目。这些人物形象无不反映着作者的内心观念、思维趋势,同时折射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蒲松龄同样也受到了前人创作的影响,并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

一、人性与妖性的对立统一
作为一本“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鬼狐故事为主,其中必然涉及大量身份为异类的重要人物。在这些人物的塑造上,蒲松龄充分汲取了古代志怪类叙事作品的营养。
鬼狐之事属于虚构,所能依仗的蓝本除传说、故事外就只有现实世界,而民间传说与志怪故事究其根本也是人类的创造。《聊斋志异》大体可以归结为借妖而写人、因人而创妖,鬼狐身上反映了人类的情感、智慧、美德与欲望,体现了人类对人性美的追求;文中的人类与异类互为表里、互为映衬,与其说是两个不同的种族,不如说是同一事物在镜子中的两面。
综观《聊斋志异》之前涉及仙妖鬼狐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异类人物的形象是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异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妖性/仙性/物性为主,这些故事中的异类形象都明显有着极为浓厚的神怪色彩,处在与人类对立的地位,几乎没有人性的表现,人类对于它们的态度也是敬畏与厌恶均有。

到了唐代,狐鬼形象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唐代日益发展的鬼怪小说中对鬼的描写与人没有太大区别,人鬼之间的距离是模糊的,冥界与人世间没有很大的差异。审美的需要导致异类身上被涂抹了世俗化色彩,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异类人物与人类逐渐亲近,异类身上人性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太平广记》、《广异记》以及唐传奇故事中涌现出大批富有人性的异类文学形象。
自唐代这一转变过渡以后,文学作品中的异类人物多半都是人性化了的异类,形象更为贴近真实生活,故事情节也更加感人。人性与妖性的结合,在蒲松龄笔下臻至顶峰。
《聊斋志异》中的异类是富有人性美的,王六郎的善良质朴、吕无病的聪慧谨慎、芳云的睿智狡黯、娇娜的美丽与医术、婴宁的天真与善笑、叶生的才华与困顿,无不有着现实的影子而又高于现实。《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同样也有着妖性,《黄英》中的陶姓少年与好友宴饮,醉倒之后“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贾儿》中的狐精“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后部”;《董生》中董生调戏狐女时“戏探下体,则毛尾修然”。

这些细节揭示了人物的异类本质又无损于人物的美好形象,也使得故事更具有灵异感与曲折感。像《任氏传》一样,《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常常生活在人类之中,与人类交好。如《狐谐》,旅店的客人们不但不害怕诙谐的狐女,更“数口必一来”与狐女说笑,被狐女讽刺了也并不生气;再如《狐妾》,被狐精救活以至行为“飘然若狐”的鬼女帮助刘洞九款待宾客治理家务,仆从对她也没有对妖鬼的恐惧,反而会私下议论“闻狐夫人稿赏优厚”。这些异类身上人性的部分已经大于了妖性,她们通常情况下的行为也跟人类区别不是很大。
更多的时候,《聊斋志异》中异类的妖性是隐蕴在人性中的。《绿衣女》中“绿衣长裙,婉妙无比”的少女“腰细殆不盈掬”,唱起歌来“声细如蝇”、“宛转滑烈,动耳摇心”,这些特质乍看是略经夸大的人类少女的特点,细读却又与篇末揭明的绿衣少女的真实身份一一一只绿蜂相呼应;《葛巾》中的葛巾“纤腰盈掬,吹气如兰”、“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其超出普通少女的纤弱和体香同样也呼应了葛巾牡丹花精的真实身份。
有的时候,蒲松龄笔下异类的人性甚至压倒了人类。《丑狐》中穆生害怕狐精,又厌恶狐女“颜色黑丑”,但在狐女拿出元宝声明“若相谐好,以此相赠”后便“悦而从之”,行为无异于出卖自身,后来狐女给的钱渐渐减少,穆生甚至请了术士来捉妖。一连串情节中穆生的贪财无情丧德辱行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反而是狐女在穆生破落之后还肯“以素巾裹五六金,遥掷之”,也接受了穆生之子的恳求不再对穆家作祟,狐女身上宽容和怜悯的人性美与穆生的贪财和绝情互相映衬,美者更显其美,而丑恶者更显其丑。

二、落魄书生的感怀与抱负
因其作者的身份,《聊斋志异》难免带上落魄文人独有的烙印。这样一种豪情与穷酸兼备、傲骨与自卑并存的特殊的思想痕迹,很长一段时间内充斥在于社会阶层中处于较低地位的文人的作品中。
反观《聊斋志异》。以最为典型的《叶生》一篇为例,开篇即介绍叶姓书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蹉跎于科考的叶生碰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一一县令丁乘鹤。丁乘鹤“见其文,奇之;召与语,大悦”,不但让叶生去衙门读书,还资助他钱粮供他养家,更“游扬于学使”帮助叶生获得了科试第一名。然而“文章憎命达”,叶生乡试再度落榜。
直到这里,叶生与蒲松龄的经历都是基本重合的,蒲松龄刚刚踏上科考路程时一样有一位前辈文人提携他,与宋琬并称清初诗坛“南施北宋”的山东学使施闰章对蒲松龄文章的评价是“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蒲松龄在施闰章手下县、府、道三试连捷,考取了秀才,随即乡试再三落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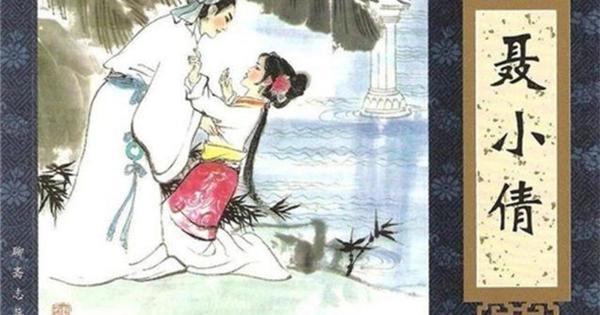
在这里,蒲松龄和叶生的经历发生了分歧。现实生活中的蒲松龄继续在科举的道路上挣扎,中间曾为人担任塾师多年;而叶生一病不起,鬼魂追随丁乘鹤而去,教导丁乘鹤的儿子考中举人,自己也应试中举,“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到文章的最后,叶生惊觉自己已死,“扑地而灭”、“衣冠履易如脱委焉”;而现实中的蒲松龄蹉跎考场直到五十余岁,终于放弃应举,两人的经历再度归结到一起一一功名不过一场空。
再如《司文郎》、《西湖主》等篇,《聊斋志异》中绝大部分的书生都有以下几个特点:才高、命并、屡试不第、常有担任幕僚或塾师的经历、最后都会得到知己(有时是前辈文人,更多的时候是红袖添香的异类才女)的赏识并获得一个平安幸福的生活。除最后一条之外,这些特点几乎都可以从蒲松龄身上找到影子。
从《聊斋志异》中书生形象的繁杂和类型的相似,以及书生们在人类世界时与蒲松龄本人高度重合的生命轨迹,可以推断出《聊斋志异》中大量的书生形象,某种程度上正是蒲松龄自身的写照,书生们离奇的经历和最终获得的幸福,也反映了蒲松龄梦想中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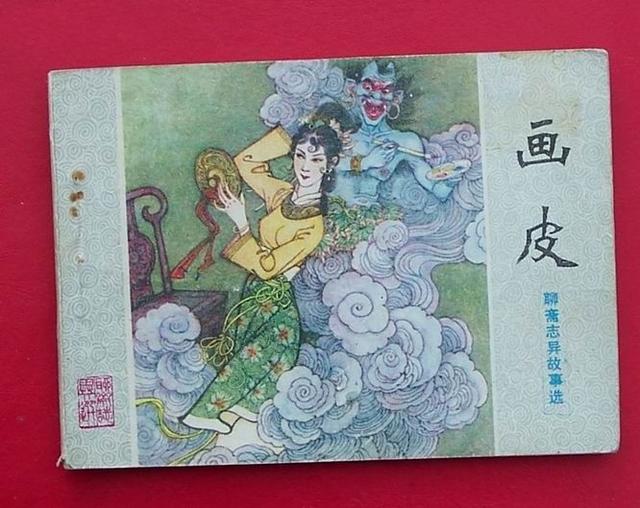
同时,以作者为代表的落魄文人对于“被拯救”的期冀,也时常在《聊斋志异》的字里行间显现出来。书生落难,小姐赠金,书生上京赶考蟾宫折桂,归来与小姐成亲好事成双一一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情节模式。追根溯源,这一模式大抵与宋代“榜下捉婿”的风气有关。
唐代不仅延续了汉魏六朝的门阀观念,在婚姻上更是极度讲求门阀,世家大族内部结姻的习俗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唐代中后期门第观念逐渐衰落,再经过五代的动荡,到了宋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门第观念淡薄,而且科举得中进士就可以直接任官迈入社会高层行列,豪门大族为了拉拢新晋人才扩大自身势力,因此出现了“榜下捉婿”这种对贫困书生而言一步登天双喜临门的风俗。
到了清代,虽然进士已经不能直接与任官和豪门婚姻挂钩,但“中状元=官职+佳人”这一思维模式仍在贫苦书生心中占据主流地位。但这毕竟是以科举得中为前提的,在中举之前又怎么办呢?千金小姐慧眼识英才,向落魄书生伸出援手的故事就成了书生们心中的一个梦一一虽然《李娃传》、《双烈记》等文学作品中也描写了妓女这种下层女性对落魄男性的赏识,而且事实上这种赏识要比深闺中的千金小姐的赏识来得更为可信,但妓女作为结姻对象是不符合书生心中的理想的。

《红楼梦》中曹雪芹就曾借贾母之口批驳那些下层文人不切实际的想象:“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鬓”。虽是反证,也可以间接解释明清时代通过作品抒发内心理想和愿望的书生的心理,即向往着被一位容貌、家世、品行、才学兼优的女性垂青并通过这种垂青一定程度上改变自身命运。
然而这种“陈腐旧套”却被蒲松龄写出了新意。在蒲松龄的设定中,那些赏识并拯救落魄书生的少女多半是异类,可以不必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不会陷入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境地;异类身份又使得她们可以比人类社会中的少女更为大胆热烈、无所顾忌,同时异类少女的法术异能又能更好的帮助男主角。
但是,《聊斋志异》中书生遇仙/遇妖的模式还是稍嫌陷入窠臼了。虽然异类少女们性格各异、出场方式各异、情节经历各异,但从男主角的角度来看,情节发展基本上都遵循了“落魄书生巧遇来路不明的美人一一书生得到少女的肯定与赏识,进一步得到生活上、科举上乃至情感上的帮助一一书生获得幸福”的模式。这种略显模式化的情节正反映了下层文人对于爱情和功名的期冀,这份期冀具现在故事中,就是一位对男主角担负起拯救超拔之责的少女。
三、女性人物形象的丰满与提升
《聊斋志异》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塑造了数百个风姿各异、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丰满的。把《聊斋志异》与此前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蒲松龄在塑造女性形象上走得比前人更远。《聊斋志异》共计四百九十余篇,其中包含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可以看作小说的有三百余篇,这三百余篇中又有超过一半对女性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从这些女性身上,读者可以看出蒲松龄对自然、对人性、对真善美的讴歌。
但最能反映《聊斋志异》女性形象进步的,是少女们的性格与行为。以《聊斋志异》中的两篇侠女复仇故事为例。侠女复仇题材历史渊源深远,唐传奇《谢小娥传》就是其中的代表和翘楚。到了《聊斋志异》,明显脱胎于《谢小娥传》的《聊斋志异·商三官》则又有不同。
同样是血亲大仇,同样是弱女子男装复仇,商三官较谢小娥更为冷静而清醒,她明确指出“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她看破了封建社会黑暗的官官相护钱权交易的官场,丝毫不抱有幻想,而是自己主动出击去报仇雪恨。

侠女复仇题材故事为数众多,但如商三官这样能够清醒看破世态的女性寥寥无几。再如《聊斋志异·侠女》,这篇故事同样脱胎于唐传奇。唐代薛用弱《集异记》中的《贾人妻》与皇甫氏所著的《崔慎思》大抵是《聊斋志异·侠女》的故事底本。
到了蒲松龄笔下,《侠女》中的侠女因为顾生资助她的老母而“出入堂中,操作如妇”,拒绝嫁娶却为报顾生之恩给他生子,又旷达的认为“枕席焉,提汲焉,非妇伊何也”,直到侠女大仇得报,故事情节主线都与唐传奇如出一辙,连侠女出外报仇,顾生晚上探望侠女发现室内无人“窃疑女有他约”也与崔慎思半夜发现妇人不见“惊之,意其有奸”的细节近似。
侠女也同贾人妻和崔慎思妻一样在报仇后翩然远去,但她不但没有杀害自己的孩子,还嘱咐顾生“善视之”,这一情节的变动使得侠女的性格较前面两位女性更接近“人”的范畴,形象也更加丰满,更加感人。

再一个反映《聊斋志异》女性人物形象的丰满的典型是《婴宁》。婴宁天真烂漫,爱花爱笑,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朝气,这样一个“狂而不损其媚”的少女是以往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稍嫌离经叛道的行为却显示了她独一无二的天然美好。再以《云翠仙》为例,云翠仙被无赖子弟梁有才骗娶,梁有才花尽她妆奋之后还要卖掉她,云翠仙却并没有悲泣绝望,而是巧计脱身还整治了梁有才一番,其慧黯动人的形象令人难忘。
另一个能反映《聊斋志异》女性形象进步的表现在于她们主体意识的觉醒。《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追求自主,她们敢于大胆的追求爱情,一旦发现感情破裂或所托非人也能坚强的主动切断关系;她们更扩大了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相夫教子,而是主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如卖花致富的黄英、易装科举的颜氏、开设琉璃厂的小二,作者对这些女性都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与肯定。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是只能依靠男性的附属品,她们美丽、聪敏、纯真而善良,她们的形象是立体的,丰满的,而不再是单调平板的。作者更在注重描写女性外貌美的同时着力刻画她们的心灵美,狐女阿绣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乔女的心地善良正直刚强、芳云姐妹的聪慧善辩、胡四娘的不念旧怨、宦娘对筝艺的痴迷、白秋练对文学的向往,内在的美丰富了她们的形象,更提升了故事的意境与思想,这些各色各样的美丽女性无不是文学长河中耀眼的浪花。
撰稿/书慧【读史品生活】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