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宋以降,蓬勃发展,明清以来,数量剧增,不下二三千种,由此引发关于野史的汇编刊刻屡有所出,成为史学发展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最近20年来,或重印旧编,或裒辑新集,或以野史名书,或以笔记题签,均时有所见,显示出中国人对于野史笔记的新的浓厚兴趣。
一
中国史书自唐初成书的《隋书·经籍志》(656年)分为13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至清乾隆时修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年)分史部书为15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秦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其间,相距1100余年,历代官府、私家所修目录之书,于史书分类上虽有所损益,然大致不脱离上述基本框架。在一般的文献目录书中,尽管见不到以“野史”为名的分类,但野史作为一个有广泛含义的概念与撰述范围却是早已存在的。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奉酬袭美苦雨见寄》,见《全唐诗》卷六三○)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终于龙纪,目曰《大和野史》。”(《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采撰二》;《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沙仲穆”作“公沙仲穆”)又有撰人不明的《野史甘露记》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以“野史”为名的著作。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一名《江南野录》)20卷,今存10卷,记述南唐史事;孔毅甫撰《野史》1卷,记北宋官员、学人40事(洪迈疑非孔氏所作,见《容斋随笔》卷一五“孔氏野史”条);《宋史·艺文志二》著录《新野史》10卷,《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野获编》8卷、《矇庵野钞》11卷、《三朝野史》7卷、《野记傃搜》12卷、《南诏野史》1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等。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撰述。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与杂史有密切的联系。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人所著《澹生堂藏书目》,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亦可证明野史与杂史的联系。《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小序,概述了杂史的面貌及其在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从整体面貌上看,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此其一;从作者身分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此其二;从体例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此其三;从所记内容来看,“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此其四。杂史的面貌及其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的表现。“杂”与“野”是有联系的。刘知几《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凡10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史通·杂述》篇失于过“杂”,不如《隋志》“杂史”类论列清晰),而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帝王之事”的范围了。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元初史家马端临指出:“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文献通考·经籍考》二二)这里包含着对“野史”的又一种界定,颇值得参考。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中《史志》篇分列史咏、子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野史”的内涵亦愈来愈宽。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条),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子部“小说”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类。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于“传记”类。可见,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见《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70~71页),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作出明确的界定。今人谢国桢则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明清野史笔记概述》,《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5期)。梁氏据传统文献分类立论,谢氏依官、私区别及作者身分裁定,均不无道理。然二说都有可商榷处。首先,“别史”立目,创于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南史》、《北史》等。《宋史·艺文志》因之,除《南史》、《北史》外,还著录元行冲《后魏国典》、孙甫《唐史记》、刘恕《十国纪年》、郑居中《崇宁圣政》及《圣政录》、郑樵《通志》、蔡幼学《宋编年政要》等各种体裁史书123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序称:别史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包罗既广,六体兼存”。据此,笼统地把“别史”纳入“野史”范围,似有未妥。仅从《宋史·艺文志》史部“别史”类著录来看,就必须区别对待。其次,“野史笔记”、“稗乘杂说”固然“不是官修的史籍”,但也并非皆出于“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之手;不少野史笔记的作者还是有官身的,只是多非史官罢了。要之,综合梁、谢二说并略加修正,于野史笔记之内涵,庶可得其大体。
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称作稗史。如明黄昌龄辑历代野史笔记40余种,刻为《稗乘》一书;明商濬编刻《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70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刻16种野史笔记,等等。其实,称野史为稗史是不确切的。《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由于人们忽略了师古注文,于是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第1版,上册第278页)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或“稗史”,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职责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过去;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则显然是不妥当的。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规律性的认识。第一,野史本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自唐以下,相沿至今。第二,野史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
二
一般说来,“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广弘明集》卷三载南朝梁人阮孝绪《七录序》及《七录目录》,其《七录目录》附录七种之二是:“《正史削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著录:“《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旧唐书·经籍志上》:“《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绪撰。”《新唐书·艺文志二》:“阮孝绪《正史削繁》十四卷”)。《正史削繁》可能是“正史”名称最早的由来。尽管《广弘明集》成书晚于《隋志》,但从它著录《正史削繁》一书详于《隋志》来看,其所据文献当早于《隋志》之所据。《隋书·经籍志二》分史部书为13类,以“正史”类为之首,著录历代纪传体皇朝史,并有小序概说其意。这是“正史”在历史文献分类上真正确立的标志。所谓“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之说,或许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况。《隋志》成书于七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是五世纪和六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含义,只有从《隋志》说起。《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几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含义与《隋志》并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几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记言、记事、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含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含义,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刘知几以下受其影响最突出者,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釐次,勒成一志。”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所列之书皆为明人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裁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几《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
《隋志》以下,《旧唐书·经籍志》承《隋志》体例,也于史部书首列正史,“以纪纪传表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因之。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其史部总序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史异也。”这是把“钦定”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的地位。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自是,近200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皇朝史而言,一是指官修史书而言。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宽泛。本世纪以来,尽管这两种说法都有影响,但从主要倾向来看,所谓“正史”,即专指作为纪传体皇朝史的《二十四史》。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即“正史”的概念,千余年中,其含义或宽或狭,几经变化,最后以专称《二十四史》作为最有影响的确定的概念。近人先后增《新元史》而成《二十五史》,再增《清史稿》而成《二十六史》,只是姑妄言之罢了。1935年,顾颉则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写道:“《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高度评价了历代正史的史学价值。
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问题在于,人们应当怎样对待它们,尤其是应当怎样看待野史的撰述及其价值。
在史学史上,自唐宋迄于明清,野史笔记为许多史学名家所重视。关于对野史之价值的评价,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说,宋人洪迈是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学人。他曾举魏泰《东轩录》、沈括《梦溪笔谈》二书所记真宗朝史事中的三事有误,乃断言“野史不可信”(《容斋随笔》卷四)。此外,他又指出陈无己《谈丛》“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并举出四例证之(《容斋随笔》卷八)。他还指出孔毅甫《野史》一书所记本朝事多有不确处,疑其为魏泰所作(《容斋随笔》卷一五)。可见洪迈对野史是很关注的,他的批评也是很认真的。然其所谓“野史不可信”的断语却失之于偏颇。宋人高似孙提出另一种见解,他详考《资治通鉴》所参考的文献“二百二十余家”,除诸正史外,采用野史笔记甚多,并举例说明所记“皆本末粲然”,认为:“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元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讲到《资治通鉴考异》时指出:“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老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资治通鉴》卷二五○懿宗咸通元年七月,胡三省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野史笔记的真正价值。明末人喻应益也是推崇野史的,他甚至认为西汉以后“安冀国有信史,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同时,他也指出:野史之作,“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记载或失之路”(《国榷》喻序)。这是推崇野史而又认识到野史的缺陷。清人昭梿论金、元史云:“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騢录》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归田录》、《中州集》等书,史官赖以成编;元代惟《辍耕录》一书,所载又多系猥鄙之词,故宋(濂)、王(祎)诸公不得不取材诸碑版、行状等词,其事颇多溢美。”(《啸亭杂录》卷二“金元史”条)昭lián梿认为,众多野史可以作为撰述正史的材料来源之一。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持这种见解。他还举出若干史例,证成其说。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对的;但是,他把野史过分抬高,以至认为“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竟可与《史记》、《汉书》“作等夷视也”,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我们在对待野史、野史和正史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应比前人有更多的理性认识:一是应有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二是应有历史主义的观点,三是应有批判继承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些观点,前人也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些思想资料多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关于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得失阐述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弇山堂别集》卷二○《史乘考误》引言)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偏颇和缺陷及其在史学上毕竟又都各有长处而“不可废”的道理,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史上的确论。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有关概念,具有值得重视的理论、方法论意义。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所谓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一是对正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应作综合的评价,不应作孤立以至于对立的看待;二是对野史本身的长短应作辩证的看待,以避免陷于偏颇的误区;三是由此而及于全部史学遗产,亦应作如是观。
关于历史主义的观点。不论是对野史、正史,还是如王世贞所说的国史、野史、家史,都应作历史主义的看待。在这个问题上,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写道:“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文史通义·文德》)章学诚讲的“文德”,是文史批评的原则之一,所举的《三国志》、《汉晋春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及其作者对“天统”、“纪传”的认识与处理,都从时代及作者“身之所处”予以说明,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今天我们对待“正史”、“野史”及一切史学遗产,不论是从全局上看,还是就个别的著作及作者来说,都应采取这种方法论原则。
关于批判继承的观点。“批判继承”是今人的观念,但并非古人没有这种思想因素。《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一方面指出野史“非史策之正”,一方面又强调“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卷末写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事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说野史,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中毕竟有“要”可“酌”,有“善”可“择”,因而受到“通人君子”、博闻学者们的重视。这些认识,包含了鲜明的批判继承思想因素,值得今人借鉴。
四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地来说明野史的史学价值了。它主要表现在:
--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历史感,历来重视治史。这一方面表现在官府对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重视,因而建立起完备的史官制度和修史制度;另一方面又表现在私家撰史的发展,而野史笔记的兴起也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之一,它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唐人李肇撰《唐国史补》(一作《国史补》),自序其书撰述旨趣说:“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可见,李肇是为续刘餗《传记》(即《隋唐嘉话》)而作此书,其主旨是“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这也是诸多野史笔记著者的共同旨趣。李肇以“国史补”名书,其意甚明;而唐僖宗时进士林恩著有《补国史》10卷(《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亦同此意。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旨在“以备史官之阙”,“惧其失传”(《次柳氏旧闻》序)。宋人王辟之《渑水燕录》序说:“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欧阳修《归田录》自序也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他们都特意指出,其书所录与史官所书、所记的区别;而所谓“可取者”、“可录者”,自也包含“以补史氏”之意。
--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野史笔记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这里,我们不妨以唐、五代的有关著作为例略作说明。唐及五代的野史笔记,因其作者的身份、见识、兴趣、视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但这些书说人物,论事件,讲制度,旁及学术文化、生产技艺、社会风情、时尚所好等等,都或多或少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历史的面貌。在现存的唐、五代野史笔记中,张鷟的《朝野佥载》(6卷,原系20卷)、刘餗的《隋唐嘉话》(3卷,亦称《传记》、《国朝传记》、《国史异纂》)、刘肃的《大唐新语》(13卷,亦作《大唐世说新语》)、封演的《封氏闻见记》(10卷)、李肇的《国史补》(3卷,亦称《唐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1卷)、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1卷)、郑处诲的《明皇杂录》(2卷)、赵lín(11)的《因话录》(6卷)、李绰的《尚书故实》(1卷)、张固的《幽闲鼓吹》(1卷)、范摅的《云溪友议》(3卷,一作12卷)、郑綮的《开天传信记》(1卷)、高彦休的《唐阙史》(2卷)等,以上为唐人撰述;以及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2卷,一作4卷)、王定保的《唐摭言》(15卷)、孙光宪的《北梦琐言》(20卷)等,以上为五代人撰述。这些野史笔记,除少数外,大多是唐人或唐末、五代人记唐事,比较真切。如《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开元间事;《朝野佥载》主要记唐初开元时事,而以记武则天时事最多;《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年间事;《因话录》记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闲鼓吹》、《云溪友议》、《唐阙史》、《北梦琐言》记唐末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
应当指出,野史笔记中,有的尚未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及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虽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一些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
两宋以下,有些野史笔记的作者在考证史事方面用力甚勤。如宋人张世南著《游宦纪闻》,被称赞为“修史校书,它日或有采证,岂小补云乎哉”(《遊宦纪闻》李发先跋)。又如宋人李心传所著《旧闻证误》一书,对宋初以来各家所载朝章典制详加辨正,证其讹误,被人誉为“良史才”(《旧闻证误》李调元序)。野史笔记在这方面的价值,也是很重要的。
--活泼了历史撰述的形式。《隋书·经籍志二》说“杂史”的特点之一是“体制不经”,是指它在体裁上不像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那样规范,即是其“杂”的一个方面。刘知几《史通·杂述》篇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所谓“自成一家”,一指内容而言,一指体裁而言。清人浦起龙解释《杂述》篇的要旨说:“杂述,谓史流之杂著。”这也应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层含义。正是这种“体制不经”的“史流之杂著”,使其得以用活泼的形式来撰述史事:有分卷而无标目者,有分卷而有标目者,有事后追记者,有当时所记者,有分类编次者,有依时编次者,等等。这种撰述形式的“杂”,确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规范的体裁、体例迥异;但也正是这种撰述形式的“杂”及其多彩多姿,极大地活泼了中国古代史书的编撰形式,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有利于历史记载领域的开拓,有利于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这是唐宋以后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野史笔记在思想上、内容上和体裁上,都有值得重视、借鉴之处。不论是在研究、撰写中国历史方面,还是在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方面,野史笔记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的史学宝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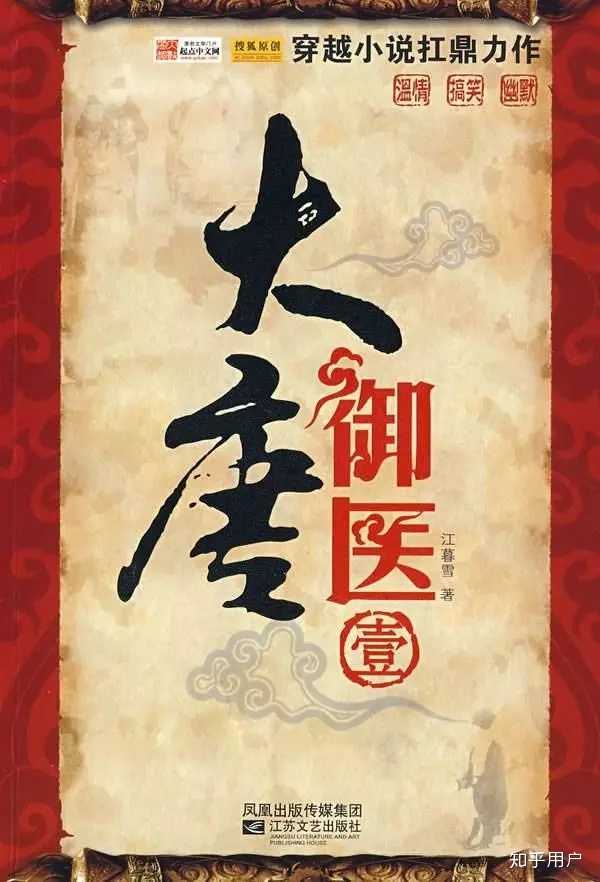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