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野史”,似乎给人们以“野性不羁”的印象,不登历史学大雅之堂。究其原因,既是历史家对史学的功能存在片面性的理解,又有封建意识在史学家头脑里作崇的缘故。若从中国传统史学及世界史学发展的水平考量,既要给野史正名,又要正视野史的不足。实事求是地对待野史乃是研究历史学的科学态度。
传说我国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商朝的史官,称为“作册”、“史”、“尹”,担负记录先王世系与商王的言行及国家大事。从广义上讲,《尚书》是中国的“正史”。西周的《逸周书》可算是中国最早的野史。是书记述较为混杂,既存留西周的文献,又记述武王伐纣,周初社会矛盾斗争的史事。东汉学者视其为“逸篇”。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称该书的“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就是说《逸周书》不那么正规严整,不那么阔谈宏论,而是时有浅薄之见,甚至间杂许多滓秽不雅之史事。然而这些却给后代研究历史的稽好故事的人带来裨益。这就是“野性”写照,体现“野史”性格与特征。继《逸周书》之后,各朝代都有野史出现。到唐代,史馆设立,官修制度形成。正史更趋规范化、制度化。野史遂沦为名副其实的在野之作。“正史”与“野史”的鸿沟愈益鲜明。正史成了正统的中国史著,而野史形同污秽小品。正史是累世不断,而野史也是源源不绝。降及清代,野史满山遍野,保留下来的书名就多达百余篇。野史不仅在内容上成为“正史”的补充,而且在思想上、风格上为史学添彩。中国野史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成为史学的一个方面军。
正史无疑是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无庸讳言,正史存在许多落后面与弊端。尤其在史学思想方面,长期滞留在“忠君”、“鉴戒”、“天命”、“资治”上。内容囿于朝廷政治史,疏于关注社会各个层面。醉心于治国安邦为著史宗旨,不屑于规律性探讨与理论建树。几千年的封建史学陈陈相因,无甚长进。野史却以特有的野性风格冲破封建史学羁绊,创造了中国史学的新业绩。在文化百花园里绽开一朵绚丽的鲜花。
中国野史较之正史有许多长处,以清朝野史为例可窥之。首先,敢于非议皇帝,揭露宫廷倾轧。中国传统史著“正史”一般都以“忠君”,为帝王歌功颂德为要务。清朝修撰的《明史》不遗余力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吹捧帝王的“至圣至明”,鼓吹君主集权。清朝野史固然也有忠君的遗传基因,但作为野史,却有“放诞不羁”的一面,敢于非议皇帝,揭露清朝的宫廷倾轧丑事。众所周知,清雍正皇帝不是个好君王,但正统史书对他却百般阿谀。可是,《清朝野史大观》却说雍正“少年无赖,好饮酒击剑”,刻薄多疑,暗害诸兄弟,骨肉相残,派人毒死胞弟允等等。尽管处于清封建统治的专制高压下,野史却发挥了私撰史书的长处,摆脱官修的羁束,显露出敢言直书的求实精神。
次则,摈弃了朝廷政治史的架构,着眼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野史内容涉及社会的五花八门题材,诸如风土人情、秘事奇闻、九流三教、文庙祀典、诗文书画、人物逸事、好勇武功等等。野史远远打破了正史的政治史传统,视线从宫廷移向整个社会。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思想活跃,妙趣横生。去掉了正史的官气,散发民俗土气的清香。野史不拘于封建社会著史的清规戒律,着眼于民众的、社会的俗世凡事,开创民众史学的风范。是故野史的人民性也表现于斯。
再次,记述“文字狱”迫害,触及时政痛处。为维护封建反动统治,清政府在思想文化上加强控制与迫害。许多知识分子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丢官、流放、处死、灭族、挖尸惩办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对于清政府这种文化专制主义,许多知识分子毛骨悚然,战战兢兢,不敢轻易下笔,生怕飞来横祸,更不敢触及“文字狱”问题,噤若寒蝉。可是清朝野史却公然直书当世的“文字狱”迫害,说“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清朝野史大观》卷三,第65页)这种大量记述“文字狱”的文字,触及清代统治者的敏感问题,触及时政之弊,显露出野史的野性不羁的思想解放特色。
然而应当看到,野史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茁长起来的野花。野史作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史学,不可避免地残存封建史学的某些恶习。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固然共同特点都是私修私撰,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里发挥作者的独立思想,传统约束力有所弱化。但中国野史与西方私修史著相比,在思维方法与著史宗旨上都有迥异。既形成中外私修史著的彼此风韵与个性特点,又显露中国史学的落后负面。
首先在思维方法上,由于中外思维方法上不同,中国习惯于在封建专制与儒家学说的框架内进行形而上学思维;外国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进行探索性思维。由是中国文人脑子里存在根深蒂固的忠君、崇儒思想,西方学者致力于历史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之类问题的探索。清朝野史虽然不是“正尔巴经”的论赞帝王丰功伟绩,但也以轻盈的笔调,美誉皇帝。同样,野史也流露出崇尚孔子儒家思想的情感,辄称儒家学说为“圣贤之学”,孔子庙为“先师庙”。所以,在思维方法上,中国文人受“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毒害,思想上摆脱不了“忠君”与“崇儒”范式的束缚。专制阴影与僵化思维方式在野史中不时反映出来。此时,与有清一代同时的欧洲是“理性时代”,社会开展思想大解放运动。用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历史学家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生理学、胚胎学、古生物学启迪历史学家的思维,社会是遵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路线,社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以新的思想、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研究历史。启蒙运动开创了新的理性主义思维方法,由是理论不断刷新。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兴起,资产阶级历史家提出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在思维方法上,欧洲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辩证求新的思维方法与中国清代忠君、崇儒的僵化思维方法形成鲜明对照。野史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著史的宗旨上,野史作家虽然不象正史那样抱定为“资治”、“垂鉴”、“治国安邦”而撰史,但却以保存趣闻逸事为目的。这些可以从留传下来一百多部清代野史的书名得以佐证。诸如《皇朝开国方略》、《圣武记》、《皇华纪闻》、《清代轶闻》、《清季野史》、《闻见偶录》等等。显然,这些都是以笔记、诗话、随笔、漫钞、纪闻、杂录等形式,把民间传闻记录下来,留传于后,以免这些逸事因年久日深而淡忘。所以野史作家是为保存史料而作史,不重历史理论的研究。野史的著史宗旨是低格的。西方撰史则不然,他们以探讨人类社会共同性的一般规律为史学研究的目的。象维科《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杜谷《人类精神的历史进展》、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诸如此类的大题材的史著,提出比较系统的史学理论。马克思称赞维科的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由此可见,西方历史学家是以探讨历史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为著史目的。中外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野史的作史宗旨不及欧洲私修史著那样高瞻与重任。中外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有不同的志趣、风格与效用。应该说,在史学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上,同时代的外国史著比中国野史略胜一筹。
野史是一种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衍生物,也是民间史学文化的一种形式。野史内容十分丰富,蕴含巨大潜能,只是历史学家还没有正确认识与运用。我们应开发野史资料,弃其糟粕,扬其精华,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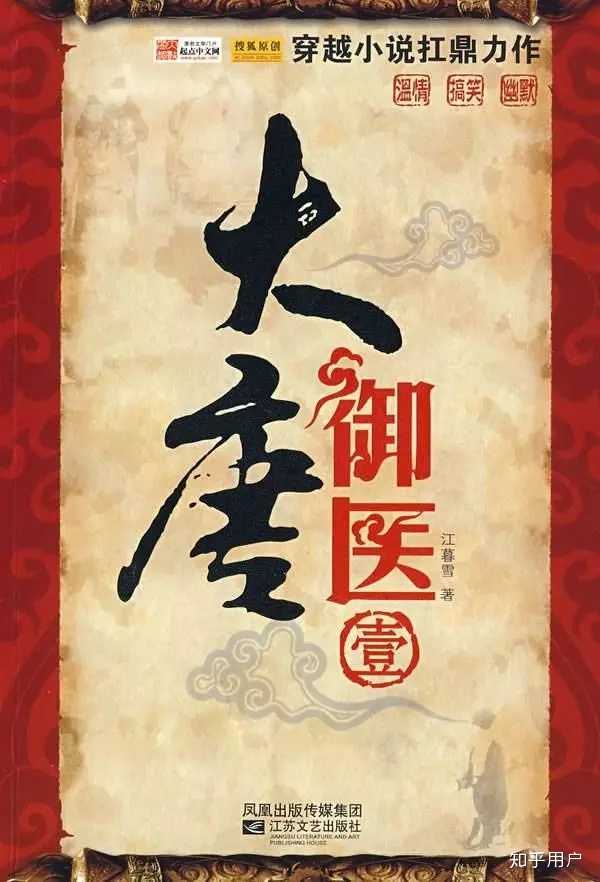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