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南诏传》《南蛮传》,宋祁撰
《新唐书•南诏传》在贞元以前采《旧唐传》之文,字句省略,事迹加详。《旧唐书•南诏传》仅二千三百余字,《新书》多至一万数百字。所增者即采录自众书也。其中如异牟寻致韦皋书,南诏与西川商议共击吐蕃,为重要史料,独具于《新书》。更重要者,南诏风土、制度,杂载于史事之中。传文载六诏名号,又载南诏世系,两段略与《旧唐书》同。其间有一千一百四十字记社会经济文化,为《旧书》所无者,即录自地志之书所载。兹取樊绰《云南志》校之:自“凡调发,下文书众邑,必占其期”,至“外算官记王处分以付六曹”,约三百字,见樊《志》卷九(其中有望苴蛮一段二十六字见卷四)。又“祁鲜山之西”至“日驰数百里”约一百七十字,见樊《志》卷六末条及卷七。又“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至“号鹅阙”约一百二十字,见樊《志》卷八。此三处摘录樊《志》各条之文,次序不乱,显知编录《南诏传》时,录自樊《志》。此外摘录樊《志》卷九与卷六七之间,传文载:“六节度、二都督、十赕”地名,虽多见于樊《志》,然区划不同。又传文摘录樊《志》卷九之前,有南诏疆界、臣属称谓及设官名号,约三百字不见于樊《志》。又摘录卷八之后,传文载吹笙劝酒,用贝为币,出师严法及犁田徭役约一百字,亦不见于樊《志》。此数处出自何书?已不能详。就所可考有关云南著作记载风土者,尚有韦齐休《云南行记》,徐云虔《南诏录》。二书宋时尚存,但韦书不见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是作《新书》时未见及此。《新书•艺文志》著录徐云虔《南诏录》,又于《南诏传》载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徐云虔出使南诏至善阐府之事迹,即出自《南诏录》。考《南诏录》凡三卷,上卷记山川风土,余二卷纪行程及出使事,疑《南诏传》所载南诏风土制度之四段,即录自徐云虔书,为其在南诏访问所得者。从此四段所载事迹观之,即不出自徐云虔书,亦当为南诏晚期之记载。
《南诏传》自南诏世系以下事迹,随文纪种族风俗,如寻传蛮、裸蛮、独锦蛮、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并摘录自樊《志》第四卷者。故疑《新书•南诏传》之文,除录自史籍以外,所载风土制度,以采自樊绰《云南志》与徐云虔《南诏录》二书为多。
《新唐书•南蛮传》分上、中、下三卷,前两卷为《南诏传》,其下卷之“两爨蛮”“昆明蛮”“松外蛮”“西洱河蛮”“姚州蛮”“扑子蛮”“望蛮”“黑齿蛮”“三濮蛮”诸条,其地并在云南,并据档册及杂着所纪种族风土之文录也。以名称汇辑,故多错杂,兹略为疏说:
“两爨蛮”条已录樊《志》卷四之文,插入约五百四十字,为樊《志》所无。其中“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以下至唐高祖时事,已见《通典》卷一八七及《唐会要》卷九十八。太宗时徙莫祗蛮事,亦见《地理志》,盖据《实录》。高宗时白水蛮事,当据《赵孝袓奏》。此数事并有参酌他书之文。传文录樊《志》以后,又载七部落,即本樊《志》卷一卷四所载,而今本樊《志》有缺佚,适可用传文补苴。
“昆明蛮”条开首一段当据武德四年吉宏伟奏疏,以下牂牁、昆明十四姓,其地不在西洱河当与分别,其中有见于《旧唐书•牂牁蛮传》之文。此条以昆明名称汇辑,而昆明不止一处,当以地区分别之。
“松外蛮”条所载风土,亦见《通典》卷一八七,文较省约。惟除《通典》之外,有两段约七十字,显知非录自《通典》,而与《通典》同出一源。疑原本即贞观二十一年《梁建方奏疏》。又“西洱河蛮”条亦当据《梁建方奏疏》,以名称不同而别为一条。实则所谓松外蛮,即指西洱河蛮也。又“姚州蛮”条,亦西洱河蛮,由于所见名称不同,别为一条也。
又“扑子蛮”“望蛮”“黑齿蛮”“长鬃蛮”数条,并出樊《志》卷四。樊《志》所载种族,《新书》多已摘录在《南诏传》,尚余此数条,后录于此。
又三濮记录,已见《广志》,《通典》亦载之。《新书》摘录文面、赤口、黑僰三濮之文,然谓龙翔中朝贡,未必有其事,当以其他同名之地名而误。
《旧唐书•南蛮传》有“东谢”“南谢”“西赵”“牂牁”诸条,《新书》亦载之,有增删处,其地主要在今贵州。
南诏统治家族自始依附于唐王朝以自重。由于历史发展,可分几个阶段:即授细奴罗为阳瓜州刺史,授皮罗阁为云南王,授异牟寻为南诏,其名号不同,而关系之实质一致;且自来相互利用又相争扰,时有战事而朝贡往来不绝。至蒙世隆时,与唐朝关系严重恶化,对后来之影响亦最大。《新唐书•南诏传》历叙细奴罗至南诏亡约二百五十年之事迹,世隆时十七年占全文之半数,即因连年战争,为最混乱时期。
《新唐书•南诏传》曰:“坦绰酋龙立,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此咸通元年(公元八六〇年)事。又曰:“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成辞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敌国礼见,福不许”。此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事,以至连年争战。卢携说南诏“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新唐传》引),即世隆时寇扰,为唐大患,以至
骚动全国,虚耗人力物力,激发农民反抗战争。故宋祁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即唐为防南诏,遣兵戍桂林,发生龎勋造反,导致黄巢起义,而唐室覆灭。宋人议论唐亡由于南诏,拒绝与大理交通,即以世隆寇扰为殷鉴也。
世隆所以与唐为敌,实由于唐朝对边境政策之错误,可以数事说之:
一、唐朝坚持避帝王名讳,拒绝册封世隆,为世隆反唐之起因。自贞元十年,唐封异牟寻为“南诏”以后,每当南诏统治家族更替,照例遣使册封“南诏”称号,至世隆立而被拒绝。《新唐书•南诏传》说:“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通鉴》说:“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按唐太宗名世民,玄宗名隆基,则世隆二字并犯帝讳。依儒家之说,嫌讳应改名,《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即王者之名祀于宗庙,称为庙讳。秦、汉以后功令,帝王之名,民间避而不用,犯帝王名讳者论罪,历代如此。唐、宋更为严格(《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一册帝讳成专篇)。唐因守儒家礼制,尊帝王,避庙讳。世隆之名犯讳,不行册封,拒绝朝贡,因不失礼而不惜与南诏决裂;故唐朝官书不写世隆之名,而恶意称为“酋龙”。见于新、旧《唐书》及通鉴诸书者只称“酋龙”,间作坦绰或骠信而不称世隆。世隆因被唐朝拒绝而反唐。《通鉴》咸通二年引《杜琮上书》:“以新主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册命,庶全大体。上从之”。王谠《唐语林》卷二亦载此事。乃遣使已行,而南诏发兵破越嶲、攻邛崃关也。
二、唐朝在西川、安南边事处置失宜,结引南诏宼扰。寇扰事迹,《新唐书•南诏传》及《通鉴》诸书载之。其原因,由于西川、安南边民反唐,引南诏兵侵扰。《新唐书•南诏传》曰:“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夷人不堪,结南诏陷安南都护府”。按樊绰《云南志》卷一、卷四并载安南川洞离心,且说“罪在都护失职”,故内应外合,安南不及设防,而南诏之兵已至城下也。又南诏宼西川,先攻嶲州。《南诏传》曰:“刺史喻士珍贪狯,阴掠两林东蛮口缚卖之,以易蛮金,故开门降南诏”(亦载《通鉴》)。继攻黎、雅,扰成都。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记南诏入寇事曰:“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蛮旗才举,望风而溃。咸通中,长驱直抵府城”。则非南诏强大,而因疆吏虐民,士不用命,有以致之。是时唐王朝统治者腐朽没落,疆吏残暴,而措置乖戾,此所以南诏横行无忌也。
三、南诏反唐未改正朔。南诏受唐封号,奉唐正朔,袁滋册封异牟寻,授历日(见樊绰《云南志》附录),此为常规。自世隆反唐以后,当无颁日历之事,惟用唐历不改。咸通七年,南诏使者至西川说:“皇帝(世隆)奉天命改正朔”,并非事实,有实物可证。大理崇圣寺《鸿钟铭文》曰:“维建极十二年,岁次辛卯三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建铸”。又弥渡《铁柱铭文》曰:“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按建极为世隆年号,始称于咸通元年,所记干支,悉与唐历相合,则世隆时虽建号,而未改正朔也。袁嘉榖《滇绎》卷二“星回节”条曰:“滇土人有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岁首者,亦有用二十五日者。《骠信诗》:‘不觉岁云暮,感激星回节’,盖即言旧之岁暮也”。此说未明确,惟疑南诏历法与唐不同者非也。按《骠信诗》盖为世隆子隆舜所作。袁氏以为寻阁劝者非是。诗见《玉溪编事》(《说郛》卷十七),亦载《太平广记》(卷四八三)说:“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明、清志书记云南风俗,以六月二十六日为火把节,亦称星回节。又《弘治贵州通志》卷十《普安府风俗》:“火炬二节”说:“《州志》,每岁以冬夏二季月之二十四日为火把节”。盖早期有二节日,后惟夏季过节,且非岁首,袁氏不审也。
至于岁首,樊绰《云南志》曰:“改年用建寅之月”(此贞元年间记录);《新唐书•南诏传》曰:“俗以寅为正”(此乾符年间之记录)。南诏历法遵唐历,世隆时亦未改,此可知也。
四、世隆反唐由于疆吏离间。《新唐书•南诏传》:“咸通十四年,坦绰复宼蜀,絙舟大渡河以济。仆旗息鼓请曰:‘坦绰欲上书天子白冤事。……’坦绰遣使斋骠信书遗节度使牛丛,欲假道入朝,请憇蜀王故殿”。按《通鉴》引坦绰与牛丛书曰:“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寃抑之事。傥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隣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据《考异》,此文盖出自《锦里耆旧传》,当时之纪录也。世隆此书,表明心迹,亦可概见经历十数年战祸之根源,而至此西川疆吏犹不省。《通鉴》说:“牛丛素懦怯,欲许之,黄庆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新唐书•南诏传》说:“牛丛犹火郊民室庐观阁,严矣为固守计”。又说:“坦绰至新津而还”。此后《新唐书•本纪》:“乾符二年正月,南蛮骠信遣使乞盟,许之”(亦载《旧唐书•本纪》。事详《新唐书•南诏传》及《通鉴》,乃议和亲,改变战争局面。
自咸通元年唐王朝,以南诏主触犯帝王名讳,拒绝册封及入贡;时疆吏肆虐,边民不堪,南诏贵族乘机宼扰西川、黔中、邕管、安南,以至地方残破,骚动全国至十五年之久。唐以此虚耗,更加重对人民剥削压迫,引起农民反抗战争,而南诏亦疲蔽不堪。此儒家礼教流毒,影响及于民族关系者。陈垣先生撰《史讳举例》(载《燕京学报》第四期,有单刊本)凡八篇八十二例,举避讳改字对于史书之影响,读书者当留意。而在封建统治时期,避讳成为功令,显示帝王之尊严,作为维护反动统治之一种手段。流毒所至,不仅史书遭受破坏,臣民偶有触犯,亦继之以镇压屠杀,考究史事当致意者。
《新唐书•南诏传》文多录自档册,亦有采自众书,保存史料;而《通鉴》及《册府元龟》诸书所载,为《新唐书》所无者往往有之,其有错误者亦不免也。
附说《通典•边防典》,杜佑撰
唐开元间,刘秩(刘知几之子)撰《政典》三十五卷,贞元间,杜佑据之重编,分为八门,统括前代史志,作《通典》二百卷。上自远古迄于天宝之末。其《边防典》有关于云南者,录《史、汉•西南夷传》之外,纪唐代事迹,有“哀牢”“西爨”、昆明”“松外蛮”诸条,即据档册录文。就中“松外蛮”条应为贞观二十二年梁建方出兵至西洱河时期之记录,载洱海以南部落社会生活,对于研究初唐时期洱海区域经济文化以及部族之发展,为重要史料;其余诸条,亦可资考证。《唐会要》《太平寰宇记》诸书已采录《通典》之文。
附说《唐会要》,王溥撰
唐代官修《会要》,自开国至大中年间,已有成本。王溥摭拾晚唐事迹,纂为《唐会要》—百卷,分五百余目。其有关边事者,卷九十九之“南诏蛮”条,与《旧唐书•南诏传》校之,太和以前互有详略,以后则《会要》稍详,止于乾符五年,然非如《新唐书•南诏传》之详备。又卷九十八之“西爨条”及“昆明条”较《通典》为详。又《通典》之“松外蛮条”,《会要》附在“昆明”条之下而多省略。《通典》之“哀牢”条,《会要》载于卷七十三“姚州都督府”条。此外如《会要》卷三十三之“南蛮乐”,卷七十一之“剑南道”,卷七十八之“节度使”,卷八十六、七之“军务”,并载有关云南之史料。
摘自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1—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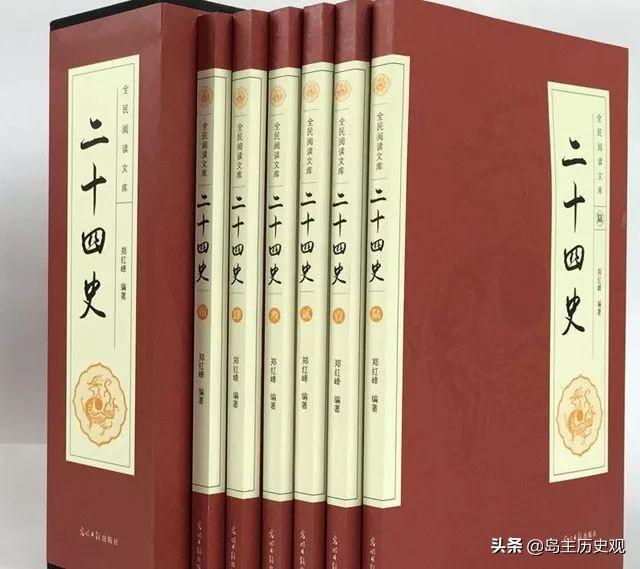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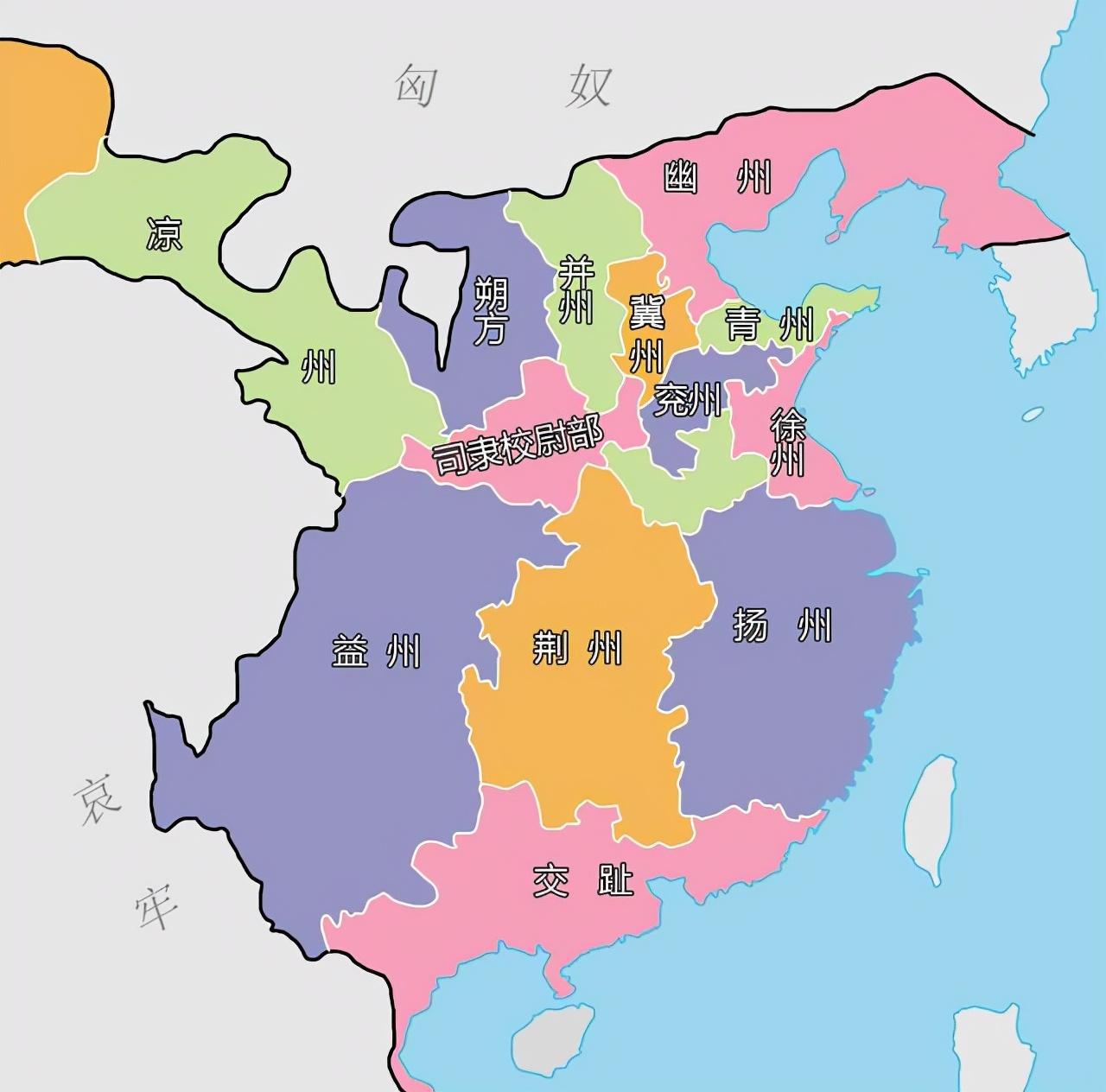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