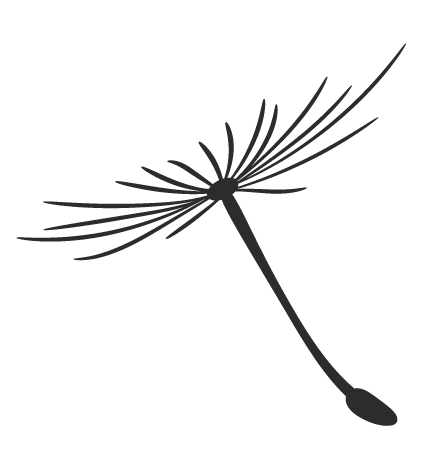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刘开军,男,1981年出生,安徽省宿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至2004年就读于淮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年至201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1年至2013年,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0年7月至今,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史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讲授《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史源学实习》、《中国传统文化原典导读》《史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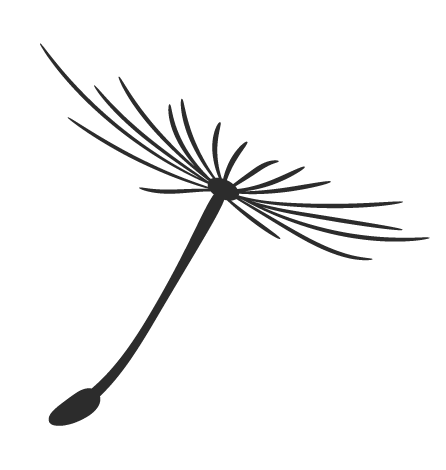
摘要:学术论著被引用情况,关乎一位学者的思想有没有参与到知识的再生产和学术的再出发中。民国时期,张舜徽征引了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和《〈史通〉驳议》,称赞刘咸炘为“知幾诤友”,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史学知识与思想延伸的链条。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引述刘咸炘的论述多达五十余处,彰显了“推十学”的魅力。柳诒徵《国史要义》援引刘咸炘的《治史绪论》,营造出一种同声相应的学术氛围。民国时期史家对《推十书》的引用体现出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学术上的认同,这种认同的纽带是基于对传统史学的温情、敬意与传承。
关键词:刘咸炘;柳诒徵;叶瑛;张舜徽
《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刘咸炘(1896—1932)据以将书斋名为“推十斋”,著述总集合为《推十书》。时人因此称刘咸炘的学问为“推十学”。至于“推十”之意,今人也有论说,刘咸炘“把‘推十合一’作为治学的原则和理想,就是推得出去,合得拢来,把自己的一整套学问形成有机体一样。”在今人的视野中,刘咸炘只是一位生前僻处蜀地,身后被边缘化的学者。然而,学者声名的显晦并非一成不变,一些在学术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学者,虽可能被一时遗忘,但又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现。刘咸炘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评估一位学者的影响固然有多项指标,比如时贤或后人的评论、读者群的广泛性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即论著被引用的情况。这关乎一位学者的学问、思想有没有参与到知识的再生产和学术的再出发中。循此思路,则会发现民国时期史家对《推十书》多有引用和接受。这里选取三个典型,估量刘咸炘的学术影响,或许不失为一条路径。
一、知幾诤友:张舜徽对刘咸炘的评价
1929年,刘咸炘撰成《〈史通〉驳议》。此外,《刘知幾家学考》《太史公书知意》等也反映出刘咸炘对《史通》的研究。这些论著早在民国时期即引起张舜徽的关注。张舜徽重视《史通》《通志》和《文史通义》,故于“三书”均有“平议”,汇成一书曰《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成书于1948年,是民国《史通》研究中有分量的一部书。通检《史通平议》,张舜徽引用了刘咸炘的《〈史通〉驳议》和《太史公书知意》,表现出对“推十学”的高度认可。
关于《史记》列传的编次,刘知幾提出过批评:“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 意思是说《史记》中的《龟策列传》不当入传,因为《史记》中的列传是记人的,根据《龟策列传》的内容,应将之归入“八书”一类,这样体例才更规范。张舜徽不同意刘知幾的观点,在列出刘知幾的这段文字后,便直接引用了刘咸炘的论述: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卷六曰:“传非专主于记人。龟策者,一术之称,与日者、货殖、游侠相同。不类象形之言,与儿童之见何异。凡传皆以事为经,人为纬。今本之无人名,乃非元本耳。若谓当与八书齐列,则日者、扁仓,皆当 为 书 乎?”刘 氏 此 言 甚 允,足 为 知 幾诤友。
列传非专记人物,这是刘咸炘一贯的主张。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专门品评《史记》之意,对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有独到的见解。张舜徽接受了刘咸炘的论断,并加以发挥:“大抵史公列传,所苞滋广。论其编次有专传,有合传,有类传。而标目之例,或以姓名;或以术业;或以行事;或以地域;则凡叙述所及,本不限于一端。知幾所云唯人而已者,特取其多者论之,未足以尽史公列传之例也。”刘知幾以例论史,有所自得,但也因此落入窠臼。刘咸炘批驳在前,张舜徽响应于后,在民国史学史上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史学知识与思想延伸的链条。
在《史通·叙事》中,刘知幾提出:“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共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举《史记》和《汉书》为例说:“《史记》之《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太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又《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也。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道哉!”由此,“必时乏异闻,世无奇事,英雄不作,贤俊不生,区区碌碌,抑惟恒理,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申其微婉之才,盖亦难矣。”乍看上去,刘知幾所言颇有几分道理。然而,刘咸炘却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此皆知幾以一己之见高下之。苏、张《传》皆本《国策》,陈、项《纪》(按,当作《传》)本于迁史,非迁、固之所造,不足见迁、固之工。《三》《五本纪》,采掇古书,日者、仓公、龟策诸《传》,多叙术 数,淮南、司马、东方《传》,多载文词,亦知幾所不喜,不知史以述为主,不以作为长也。马、班书佳篇甚多,知幾皆不举而独举此,浦氏以为僻,信矣。
刘咸炘从史源上考索,指出《史记》的《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源出《战国策》,《汉书·陈胜项籍传》本于《史记》,根据这些篇章评骘司马迁和班固的史才是不妥的。《史记》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东方朔传》或“叙术数”,或“载文词”,非刘知幾之喜好,故被认为乏善可陈。总之,刘知幾举例不当,论断偏颇。张舜徽评价刘咸炘“切中知幾持论偏激之病。全书中往往有此,皆当分别观之,未足视为定评。”张舜徽认为刘咸炘的批判击中刘知幾“偏激之病”,应格外留意。
在关于《史通·品藻》的平议中,张舜徽也引用了《〈史通〉驳议》。《史通·品藻》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之意,批评史书类传铨配之失:“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相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张舜徽于按语中写道:“《〈史通〉驳议》曰:‘此足见知幾于史家铨配列传之法所见甚浅。老、韩同传,明道法之源流。董、袁合篇,著争裂之原起。岂止如知幾所言而已乎?若知幾言,则诸史英雄同时者多矣。何不皆合之耶?’”刘咸炘“指斥知幾轻于立论之失,深中肯綮。……知幾之病,恒喜自作一例,以上衡古人,此其所以乖舛。”张舜徽针砭“知幾之病”,不能说没有刘咸炘的启发。总的来看,张舜徽在《史通平议》中引用刘咸炘的观点,持赞叹之意,而“知幾诤友”之评也是十分允当的。
民国时期研究《史通》之风甚盛,举凡评论、考订、校释、补续均有多家。耐人寻味的是,《史通平议》仅征引了刘咸炘的《〈史通〉驳议》和吕思勉的《史通评》(仅引用一次)两家,而对于当时名气很大的何炳松等人的《史通》研究论著却只字未提。这里面是否表现出某种学术上的认同,耐人寻味。
二、实斋传人:叶瑛对刘咸炘的推崇
叶瑛字石甫,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叶瑛自1929年校注《文史通义》,“惩空言之无裨,慨学术之弗章,课暇辄取 《通义》疏注 之”,1948年完成。尽管《文史通义校注》出版、流布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但它成书于民国时期,仍然显示出“推十学”在民国史学界所具有的魅力。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注文采自时贤者,必一一注明”。叶瑛采择的“时贤”有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钱穆、金毓黻和刘咸炘等。对今人而言,上述数人中除刘咸炘外,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学者。有意思的是,叶瑛引用最多的恰是刘咸炘,明确标识的就多达五十余处。这为考察“推十学”在民国史学界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有力证据。
《文史通义校注》第一次援引刘咸炘的论著,见于《文史通义》第一篇《易教上》的第四条注文。“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通义》全书以三教篇为纲,三篇又以此篇首三句为纲。’”所谓“三教篇”是指《易教》《书教》《诗教》,而“此篇首三句”则指《文史通义·易教上》的“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叶瑛引用这句话,提纲挈领地指示这几篇文章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的核心地位。这说明,叶瑛认为刘咸炘关于《文史通义》著述体系的认识是有价值的。叶瑛校注不仅考订人物、语句的出处,引经据典以呼应实斋,且“于其书要旨所在,亦略为引发,以期不至晦其原意” 。在“引发”实斋“要旨”时,叶瑛常引刘咸炘以为同道。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叶瑛直接引用刘咸炘的说法以代己立言,或吸收刘咸炘的观点丰富己说。刘咸炘评价《文史通义·释通》“专论史法,乃先生之大计。不可通者,各归其分;可通者,归于大原。不可通者,勿强通;可通者,勿自蔽。此即吾所谓分合,乃先生学说之大本,亦即此书之所以名为《通义》也。”叶瑛校注《释通》篇时就全部征引了这段话。《文史通义·砭异》叶注吸收刘咸炘的思想:
此盖承上篇而为言。好名之人,往往喜自立异,以为名高,实斋特著论砭之。“内不足,不得不矜于外。实不至,不得不骛于名。”二语抉其病根之所在。刘咸炘《识语》云:“此篇亦《原道》之余义。先生由校雠而得共由之义,又由共由而得平常之义。”亦有所见。
同样,叶瑛疏通《文史通义·博约上》篇的史意时,也藉刘咸炘之说立论,“实斋论学,以为必习于事而后乃能经世而致用。然博综须归乎自得,从入多本于情性,性有所偏,则所长不能兼备,极其所致,则以专家为归,故曰‘道欲通方,而业归专一’,此《博约》所为作也。刘咸炘《识语》曰:‘章炳麟谓“《文史通义》遗害甚大,后生读之,但知扺掌谈六艺诸子,翻阅书录而无所归宿。”此弊诚有之,但坐不读《博约》篇耳。’语颇有见。”“亦有所见”和 “语颇有见”,二语足见叶瑛对“推十学”的推崇。
第二,叶瑛在接受刘咸炘的观点后,有时也作引申,如《书教下》“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句下,叶瑛注道:“刘氏《识语》:‘马书初变编年之传为分篇之传,而一气卷舒,多因事附见,未严类例,故曰去左氏近,得《尚书》之遗,不甚拘拘于题目,故传少而事该。’《史记》之传无一定写法,变化多;《汉书》之传写法比较接近,变化少。” 叶瑛论史、汉列传写法的不同,与刘咸炘的论述相通。
第三,当刘咸炘与他人观点分歧甚至对立时,叶瑛支持刘咸炘。在对《文德》的理解上,刘咸炘和章太炎的看法迥异。叶瑛在《文德》的第一条校注中写道:
章太炎先生云:“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原注:《论衡·佚文》篇:‘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吏为私,无为主者。’)杨彦遵依用之,(原注:《魏书·文苑传》:‘杨彦遵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惟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刘咸炘则谓:“按北齐杨愔已有《文德论》,岂但仲任一语?然未倡之,先生已自言之矣,未尝于才、学、识之外言德也。刘勰乃昌论文心,文心之论,则始于陆机也。苏辙乃昌论文气,文气之论,则始于曹子桓也。然则论文德自先生始耳,何必以前此已有,为讥议之论哉?”(《识语》)按实斋所论文德,专指作者态度而不涉及修养,旨固殊乎前人;而阐发幽微,独参胜义,情有异乎窃取。刘氏平反章说,颇为得之。
章太炎认为“文德”说源于《论衡》,据《魏书·文苑传》,杨愔也撰写过一篇《文德论》,所以,《文史通义·文德》属于“窃”。刘咸炘则认为王充、杨愔虽更早提到“文德”,但论述不够;实斋“文德”之论较之王、杨之“文德”不可同日而语,真正讨论文德是从章学诚开始的。章太炎认为实斋是“窃”,刘咸炘坚持实斋功不可没。叶瑛不是回避争议,而是明确赞成刘咸炘,认为实斋的“文德”宗旨“殊乎前人”,是“命意有别”,并且阐释深刻,不可视为“窃取”。一种观念的流行,虽有源头,也有演变和递进。源头固然重要,但不能抹杀演进的重要性。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章学诚已明言“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可见,实斋论“文德”,揭示“敬”“恕”二字,确有新意。章太炎以“窃”字论之,不能算是恰如其分的。
三、旧史余音:柳诒徵对刘咸炘的认同
1942年,柳诒徵于抗战炮火中执教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讲授史学理论与方法,撰成《国史要义》。书中,柳诒徵不止一处援引刘咸炘的著述,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却由此营造出一种同声相应的学术氛围。
第一处是关于“史德”的讨论。柳诒徵认为“世之诵习章氏之学者,似皆未悟其所指。”接着,柳氏特别提到了刘咸炘,说:“刘咸炘虽谓《史德》一篇最为精深,其所举敬恕二义,颇不易晓,敬即慎于褒贬,恕即曲尽其事情。然未尝切究章氏所谓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诸语。”引用不一定完全赞同,但唯有被认为有价值的论断,才会引起学术对话。需要强调的是,柳诒徵于“世之诵习章氏之学者”中,仅提到刘咸炘和梁启超。相较于同刘咸炘的温和商榷,柳诒徵对梁启超的批判可谓激烈:“陈义甚高,第似未甚虚心体察章氏之意”,“根本实相左也” 。在柳诒徵看来,与刘咸炘相比,梁启超关于“史德”的阐释偏离得太远了。
第二处是关于“史识”的讨论。柳诒徵认为刘知幾最重史识,“章实斋申之而论史德,梁启超、刘咸炘又申论之。皆各述所见,与刘氏原旨不符。”若遽然将“与刘氏原旨不符”一语作为柳诒徵否定刘咸炘的例证,则难免沦为皮相之谈,因为柳诒徵还有更丰富的阐述:
梁氏意主革新,谓史识是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又标四义,曰由全部至局部,曰由局部至全部,曰勿为传统思想所蔽,曰勿为成见所蔽。盖示人读旧史而创新史,非知幾所论修史之宗旨也。刘咸炘氏则以观史迹之风势为史识,又曰:作者有识,乃成其法,读者因法而生其识,虽二实一。又曰:读史本为求识,所以必读纪传书。又曰:吾辈非有作史之责,而必斤斤讲史法者,正以史法明史识乃生也。是其所谓观史迹者,虽与梁氏所谓观察力者同,而斤斤讲旧史之法,兼读史与作史而言,又非如梁氏之斥传统思想也。
柳诒徵紧接着引用了刘咸炘《治史绪论》约四百字。他比较刘咸炘与梁启超的学说,言明二人之不同在于梁启超“意主革新”,排拒传统,而刘咸炘“讲旧史之法”,继承传统。由今观之,梁启超多引域外学说以改造旧史,而刘咸炘则取法旧史,益以新知,二者确有不同。柳诒徵对待梁启超和刘咸炘这两种迥异的治学取向又持怎样的态度呢?他赞同刘咸炘的理路,认为章学诚“谓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所以补充刘氏之说者,要自有见,第未推原道德观念实出于史耳。刘咸炘谓读史本为求识,义亦犹是。”意思是说,刘咸炘如同章学诚一样可补刘知幾之未备,章学诚和刘咸炘的为史之义是一致的。如同上述关于 “史德”的讨论一 样,柳 诒 徵 再 次 讥 讽 梁启超:
学者识力,大都出于读史。苟屏前史,一切不信,妄谓吾之识力能破传统观念之藩,则事实所不可能也。或袭近人之言,或采异域之说,亦即秉遐迩之史,以为创新之识,隐有其传,非能舍史而得识也。语曰:温故而知新。苟非以故谷为种,何能产新禾之苗乎?
文中虽没有出现梁启超的名字,但其实是在回击梁启超“勿为传统思想所蔽”的观点,认为此论根本行不通。这样说当不至于违背柳诒徵之本意,因为柳氏接着就提到了梁启超,说刘知幾的“史识”思想,“在《书事》篇中言之最详。《书事》篇专论史法,即刘咸炘所谓作者有识乃成其法,亦即梁氏所谓传统思想。学者宜熟复之,乃知吾史书之别于史料。近人恒谓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者,坐不知吾史相传之义法也” 。言下之意,刘咸炘是深谙“吾史相传之义法”的,而梁启超则不然。
需要强调的是,柳诒徵论史识,于刘知幾之后,只提了三个人:章学诚、梁启超和刘咸炘。章学诚自不待言,生前已有人将他比作刘知幾。梁启超在清末史学界居于中心地位,此处突出梁启超也不难理解。倒是柳诒徵援引刘咸炘,多少有些出人意表,但细思之则又在情理之中。《国史要义》中将梁启超和刘咸炘的学说合而观之,较量高下,每有贬低梁启超之意味。如果说柳诒徵对梁启超的评论已经表现出一种学术思想的分野,那么他关于刘咸炘的接受则暗含着一种学术上的共鸣。
此外,在关于“进化论”的讨论中,柳诒徵也注意吸收刘咸炘的观点,认为进化论“可以益人神智”。但“吾人治中国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 。这也显示出柳诒徵与刘咸炘在学术倾向上的一致性。《国史要义》是一部从中国学术传统出发讨论史学要义的著作,重在表彰“吾史之美”。至于那些西化重于延续传统的言行,不过是“徒震于晚近之强弱,遂拾其新说,病吾往史,则论世之未得其平也。”与其说这是文化保守,不如说是对于传统的理性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新旧学者交锋、中西学说碰撞的背景下,柳诒徵对于《推十书》的引用具有阵营对垒的意义。
柳诒徵、叶瑛、张舜徽对刘咸炘著述的引用,从一个具体的层面展示了刘咸炘的思想与学问在民国史学界的传播。它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推十书》在民国时期渐次流传,已然超出四川的地域空间,而具有全国影响,并藉《国史要义》等名著的流布融入到了民国学术史研究的血脉中。民国史家对《推十书》的引用也形塑了刘咸炘的史学形象———刘知幾、章学诚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理论的衣钵传人。进而言之,柳诒徵、张舜徽、叶瑛等人与刘咸炘之间存在一种学术上的认同感,这种认同的纽带正是对于传统史学的温情、敬意和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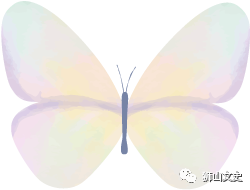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总第270期)。狮山文史公众号文章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稿件联系:不厌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