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郑庄公热脸贴了冷屁股
善恶析辨,陈五父善言吃了闭门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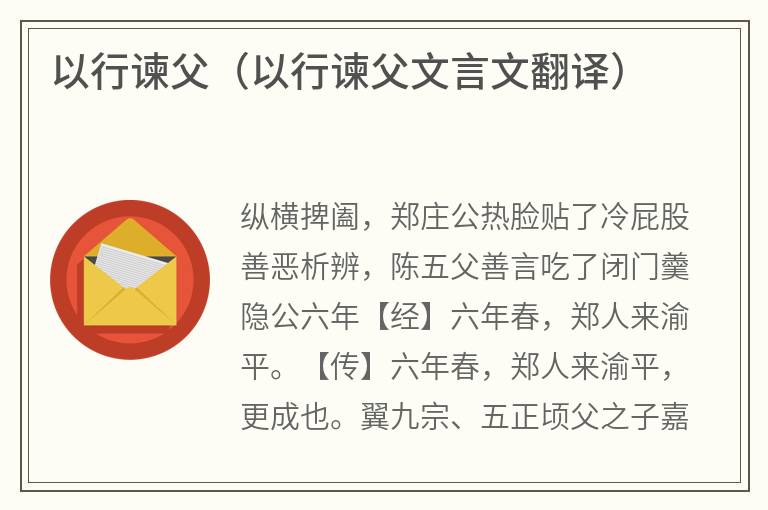
以行谏父(以行谏父文言文翻译)
隐公六年
【经】六年春,郑人来渝平。
【传】六年春,郑人来渝平,更成也。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
六年春天,《经》中说了一件事,就是郑国来和鲁国结交。而《传》中又补充了晋国的一件事,就是晋都城翼的嘉父又从随把翼侯接了回来,放在了鄂地,叫做鄂侯,这样晋国就有了两位侯,一个是去年天王明知翼侯还活着就立了一个哀侯,说白了就是废了翼侯。但大宗之人又把翼侯接了回来,那就不能再称翼侯了,干脆在鄂就叫鄂侯。本来大小宗分裂,现在大宗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弃旧怨结新好为渝平,渝为改变之意。坚贞不渝,矢志不渝的渝都是改变之意。成即和好,讲和之意。那么弃旧怨就是有旧怨啦,这里隐含了一个故事。当隐公为公子时与郑国在狐壤打了一仗,结果被郑人所俘,后来又逃了回来,就此有了怨恨。此次郑庄公的政治嗅觉多么的灵敏,一看隐公不去援救宋国,马上来拉拢鲁国。而隐公也放弃了旧怨,结了这个势头正盛的新欢。更成是解释渝平的,一个意思。
这里补充一个大小宗的常识,西周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保持严格的等级关系,它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大宗小宗是为了处理嫡长子和他的庶兄弟之间的关系而立正妻所生的长子为嫡子,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因此,周天子既是天下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享有主祭的权利。被分封的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为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其权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庶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士,士的长子为士,庶子为平民。
那么在晋国翼为大宗,山东省曲沃为小宗,这出戏是小宗对大宗发起的挑战。周王室姬林开始受了曲沃的好处,支持小宗,后来曲沃背叛了自己,又支持大宗。周桓王自己破坏了规矩,王室也就更得不到尊重。按理说周王室应该维护大宗的地位,要不自己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挑战。最后翼侯跑了,他就立了一个哀侯,实则又给晋国埋了一颗雷,表面上是为了晋国,实则也是包藏了祸心的。
晋国的事还没完,以后会越来越精彩。
【经】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传】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五月庚申,郑伯侵陈,大获。
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这年夏天,同样是经中说了一件事,在五月鲁侯和齐侯在艾地会盟。而传中又补充了郑国了陈国的故事。
先说第一件事,鲁和齐的会盟。鲁国和齐国在春秋前是不交好的。因为郑国被四国联盟遏制崛起,所以郑国在隐公三年时和齐国结盟,为此成功郑庄公高兴得出了车祸。现在鲁国又被郑国拉来入伙,自然也就与齐国结盟,形成了三国联盟,用来对抗四国联盟。此时春秋形成了两大对抗集团。宋卫陈蔡为一派,宋卫为首。郑齐鲁为一派,郑为首。所以郑国有春秋前期“春秋小霸王”之称。隐公五年时间,一直不掺合国与国之间的争夺,保持中立。但一个不小心,得罪了宋国,不得已参与了争夺。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版的世界大战,最后都得选边站,有点身不由已。可以说鲁国的加入标志着两大阵营的正式确立。
第二件事,郑国侵陈。同样是在五月,也就是鲁国了齐国结盟没几天,郑国就开打了,而且大获全胜。左传还补充了一段陈侯和郑伯的一段往事。前几年,郑伯为了破坏四国联盟,曾请求和陈国讲和,陈侯正在享受人众势众欺侮人的乐趣,同时前文石碏借陈国之手大义灭亲时提到陈国受天王的亲睐,所以陈褒哪里肯听。当时陈国有个五父的人就是公子佗,陈桓公的弟弟,叫他陈佗就行。陈佗劝谏陈桓公说,亲近善人,友睦邻国,这是治国的法宝。你应该答应郑庄公。陈侯说,宋和卫两个国家要给郑国制造麻烦,像郑国这样的小国又怎能为害我呢。言外之意,我们跟着宋卫踩它,怕什么呢,踩了也白踩,白踩谁不踩?有便宜不占,那是王八蛋。于是没有理睬陈佗。
这里左传借君子之口,评论这件事,说了一句名言“善不可失,恶不可长”,意思是与人为善之机会是不可失掉的,与人为恶的行为是不可助长的。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啊。接着又是一句金句“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意思是助长罪恶而不能改正,将会自遭祸殃,那时即使想挽救它,又怎能办得到呢?
君子还引用《商书》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商书》说“恶行是很容易滋长的,就佼燎原的烈火一样,不可以靠近,难道还能够扑灭吗?”还有周大夫周任也说过:“治理国家的人,遇见恶事就应该像农夫必须铲除田中野草一样除掉它,农夫把野草除掉积聚起来,还要灭绝它的根,不让它复生繁殖,治国的人能这样对待恶事,善事就能得到伸展了。”这里有两个成语源于此,一个是“见恶务去”,一个是“燎原之火”。原文中的“芟”是割“夷”是灭之意,“蕰”是积“崇”是聚之意。“信”同“伸”。
此一段岂止是治国之策,也是这们为人之道啊。
【经】秋七月。
【经】冬,宋人取长葛。
【传】秋,宋人取长葛。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
这里秋冬之事《经》和《传》有出入,《经》中是“秋七月,冬,宋人取长葛”。《传》中说“秋,宋人取长葛”。应是《传》中有误。《经》中就一句“秋七月”在《公羊传》中传此三字为“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意思是春秋是编年体史书,春夏秋冬四时必具,然后才能称为编年体。即便是秋季无事,也得写上“秋七月”三字。所以秋冬是分开写的,明确冬天宋人占领了郑国的长葛,五年冬十二月围长葛,历经近一年,才占领了。
这年冬,传中还写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周王室派人来鲁国报告饥荒,明显是来要粮的,鲁国没办法,到处给王室购粮,此时不但去了齐郑,也去了宋卫,两个阵营都去了,而且他们也都卖给了鲁国,说明当时每个国家虽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但谁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
还有一件事是郑伯去周朝拜周桓王,这里用了一个“始”,可见郑和周在繻葛之战闹掰之后,尤其在隐公五年繻葛之战中天王还中了一箭,两下结怨。所以一直没来朝拜,现在周室饥荒,来慰问一下,同时改善一下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挟天子令诸侯,不能不说,郑庄公确是打政治算盘的高手。但他没想到,周室被他伤的太深,周王放不下架子,对他爱搭不理的。当时周桓公,注意是周桓公对周桓王进行劝谏,他俩谥号都是“桓”,周桓公就是周公黑肩,周公黑肩说:“我们东迁的时候,是依靠人家晋国和郑国才得以延续,如果我们对郑国表示善意,就可以鼓励其它诸侯,这样做还怕人家不来,现在倒好,不仅不表示善意,而且还对它无礼,郑国再也不会来喽。”
弹词南乡子陈桓公成宙评
恶善最难分,种下因缘见辱荣。追随宋卫凌欺郑,无功,不纳良言愈平庸。
芟草烈阳烘,杜绝繁殖怕绝根。一朝点燃燎原火,留神,无数楼宇俱销熔。
弹词南乡子周桓王成宙评
无礼对庄公,不计当年落难东。当面谁屈人笑脸,智惛,社稷江山夕照中。
两次涉晋争,先助小宗后大宗。满腹雄心难预料,途穷,大漠驼铃旷野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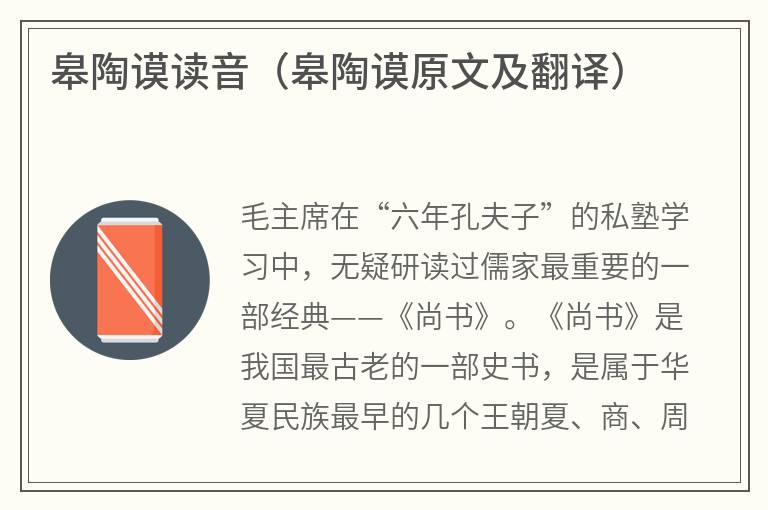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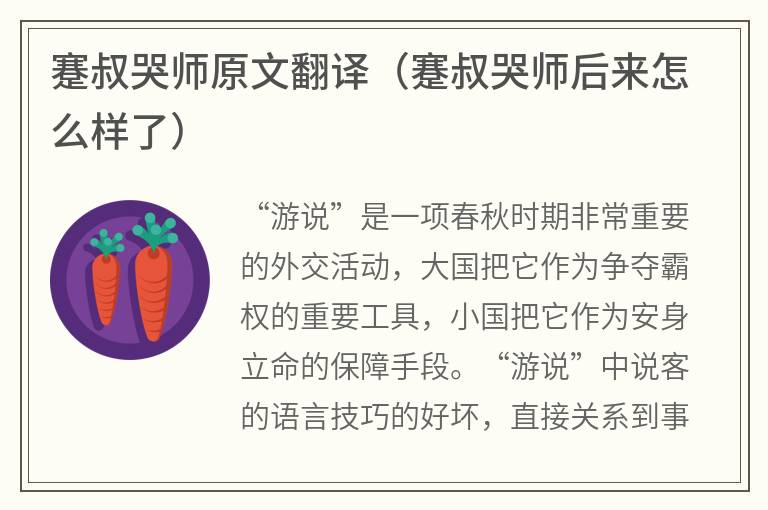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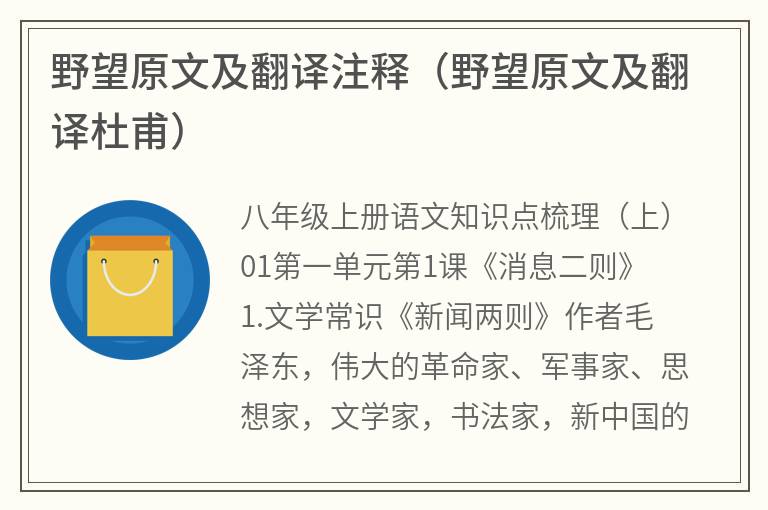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