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是一项春秋时期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大国把它作为争夺霸权的重要工具,小国把它作为安身立命的保障手段。“游说”中说客的语言技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事情的成败,甚至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
如果把“游说”这项外交活动,看成是一场“擂台争霸赛”,那么秦穆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擂主”。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有了两场精彩的“游说”——“烛之武退秦师”与“蹇叔哭师”。
《东周列国·春秋篇》秦穆公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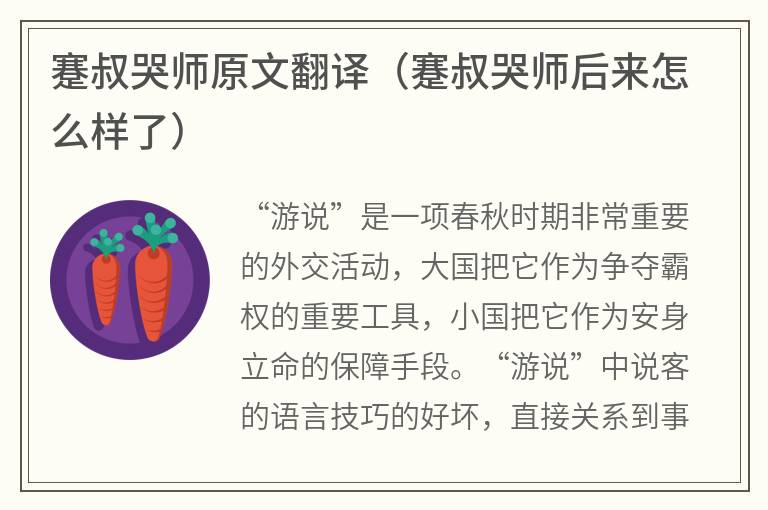
蹇叔哭师原文翻译(蹇叔哭师后来怎么样了)
从“对擂”的结果来看,秦穆公输了第一场,赢了第二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穆公两场皆输。
“烛之武退秦师”的结果是,秦国放弃和晋国一同围郑的计划,放了郑国一条生路。之所以说秦穆公在这场“游说”中失败,是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失掉了灭郑而分一杯羹的好机会,另一方面使“秦晋之好”名存实亡,为其后的秦晋“崤之战”埋下了隐患。
“蹇叔哭师”的结果是,秦穆公顺利出兵攻郑。表面上看,蹇叔没有说服成功,是秦穆公胜了一筹,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这次秦穆公的贸然出击,才导致秦国兵败“崤之战”,主力军队被晋国尽数歼灭,也自此失去了逐鹿中原的实力。
那么,为何同样是“游说”秦穆公,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在笔者看来,是二人“渐进”与“激进”的语言方式导致的。
眼见郑国灭亡在即,烛之武竟能冷静地以“渐进”的语言艺术说服秦穆公,可见他的胆识过人,亦可见他的话术精妙。
《东周列国·春秋篇》烛之武剧照
那么,究竟如何在与敌人的谈判中取得胜利呢?笔者用猎人“狩猎”作为类比,来分析“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渐进”艺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猎人面对猎物,要先卸掉猎物的防备心。
烛之武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拄拐老人,面对秦穆公抛出“郑既知亡矣”的论调,无论是个人形象还是语调与用词,看起来都没有丝毫的攻击性,这也是烛之武“渐进”艺术的第一步。众所周知,如果想要跳起来蹦得高,屈身弯膝的准备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二、猎人布下诱饵,静待猎物一步步踏入陷阱。
烛之武以“敢以烦执事”打开了话匣子,也由此开启了秦穆公聆听的契机。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秦晋围郑”,本就是源自于晋文公与郑国国君的个人恩怨,这与秦国有什么关系?何必让别人当枪使?这个道理大家都心知肚明,烛之武也就没有必要一一点破了。而现在最重要的“诱饵”,就是“有益于君”,烛之武把这块肉放在这里,不信秦穆公不来咬。
三、猎人设置诱饵和陷阱的地点,一定要出其不意。
要保证秦穆公来吃“诱饵”,就要突破秦穆公的既定思维——在秦穆公看来,只要攻灭郑国就可以捞到好处。在人们都以为烛之武会把话题引到“灭郑对秦国没有好处”的时候,烛之武却话锋一转,把晋国拉了进来——“焉用亡郑以陪邻”。这种出其不意的精妙话术,不仅减少了“灭郑”这种心理暗示,更增加了秦穆公的好奇心,
四、猎人收网时要掌握“平衡”之力。
烛之武深知秦、晋两国的力量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就好像是一个处在“平衡”状态的天秤,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实质上两方的目标都是称霸中原。一旦两者拔剑相争,什么友谊、联姻、亲情,皆可在一朝之内化为泡影。而平衡被破坏的起点,就是“邻之厚,君之薄也”。
五、猎人要安抚猎物,使其放弃挣扎。
由于秦穆公心中的平衡被烛之武一语道破,他自然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和抵触。此时就应该进行安抚动作——“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此时一个画面浮现在我们眼前:烛之武一边勾着秦穆公的肩膀,一边以“同理心”安慰他,我们是亲密的战友,我做什么都是为你而考虑的。可见,此时秦穆公的心理防线已经被彻底攻破了。
六、猎人给猎物的最后一刀,要又快又准。
烛之武一共说了一百五十二个字,他用其中七十个字给了秦穆公这“最后一刀”。说他“快”是因为,他一口气就说完了晋国背信弃义、贪得无厌的事,我们都知道,愤怒的情绪是短暂的,经过思考可以消解愤怒,然而,烛之武却没有给秦穆公思考的机会;说他“准”是因为,他抓住了秦穆公内心最痛的一点——“许君焦、瑕”,而这两个地方正是秦穆公梦寐以求逐鹿中原的“桥头堡”,由于晋国背信弃义,导致秦穆公失去了这两座城池,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这又快又准的“一刀”,终于让秦穆公屈服了。
这样“渐进”的语言艺术,宛如猎人与猎物之间的攻防和周旋,精妙至极,不仅卸下了秦穆公的自我防备,也扭转了春秋历史的发展。
在两年之后的秦国国内,有一场与“烛之武退秦师”一样精彩,却又不同形式的“游说”,面对的也是同一个对象——秦穆公。
《东周列国·春秋篇》秦穆公剧照
身为辅臣的蹇叔,不惜“哭师”,但却没有成功。蹇叔一开口就惹恼了秦穆公:“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一举动对即将出征的秦军而言,无异于是用哀乐和挽歌送别。蹇叔大肆疾呼的谏言,对秦军军心造成了多么不详且负面的影响。
笔者猜测,蹇叔看到秦军出征的大势已定,本想用这一步“险招”,来强行阻止秦军东进,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激发了秦穆公的抵触情绪。不仅如此,蹇叔“激进”的劝说方式,还遭到秦穆公“尔墓之木拱”的强势反击。
笔者认为,臣以“直言”游说君主,成败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有“纳忠言”的雅量,如唐太宗能纳魏征的直言,则君臣互蒙其利;否则以逆耳之言谏昏君,如项羽不听范增言,则君臣必受其害。君不见,“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因为忠谏而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而蹇叔能侥幸逃过一死,实乃不幸中的大幸。
如此看来,蹇叔输在了起跑线上,但其之后的一番“激进”之词,却甚为高明。他列举出秦军有“袭远”、“力竭”、“悖心”三个难题无法解决。
在笔者看来,蹇叔提出的这三点问题确实都是秦国的弊端。首先,秦、郑两国并非毗邻而居,而是相距甚远,中间还夹着强国晋国,如此一来秦军东进,必然要长途奔袭。其次,秦军孤军出兵,途中是完全没有友军支援的,也就是说,秦国军队的损耗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补充。最后,军队远出国门,士兵思乡心切,军心肯定容易涣散。总的来看,蹇叔这一番着重强调的“激进”话术,句句掷地有声,内里包含的皆是他的真知灼见,只可惜,秦穆公不为所动,所以,秦国兵败在所难免。
《东周列国·春秋篇》蹇叔剧照
?然而,笔者认为,蹇叔虽然指出了“秦害”,却忽视了“秦利”。而“利”与“害”就好像一把剪刀上的双刃一样,必须同时运作,剪刀才能发挥效果。蹇叔未指出“秦利”,怎么能使上力道呢?
试想,如果蹇叔能够以“晋文公新丧”为由来劝说秦穆公,未必就不能成功。要知道,春秋时期各诸侯大多都不重视“礼法”,以致“礼崩乐坏”,如果此时秦穆公趁“晋文公新丧”的机会,一方面抚恤晋国新君,另一方面继续培育秦国在晋国的势力,不仅能树立“仁德”之名,一旦抓住机会还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笔者觉得,蹇叔之所以使用“激进”的话术,是因为他已经洞悉了秦穆公决意攻郑的心意,而且当时秦军已经整军待发、箭在弦上,他迫于这种高度紧张的情况,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激进”劝说。可见,蹇叔明明自知“不可为”,却以“哭师”的形式为之,他不惧杀身之祸的直谏,实乃大丈夫之所为。
综合烛之武和蹇叔的“游说”来看,他们采用了不同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烛之武“一夫当关”,使用“狩猎”之策成功说退秦师,不仅为郑国争取到了一线生机,也成功树立了自己在外交领域的光辉形象。与此同时,也证明了郑国并非是“无才可用”,它逐步走向衰弱,是由于其君主“有才不用”之咎由自取。
蹇叔表面看是失败了,但是结合历史的事实来看,蹇叔当时受制于秦穆公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就算舌灿莲花,确实也已无法扭转局面。对于蹇叔自身来说,他以“哭师”一事千古留名,确实获得了后人赞扬,但笔者相信,如果蹇叔可以选择的话,他会毫不犹疑地,用自己的千古留名去换取秦国的千秋伟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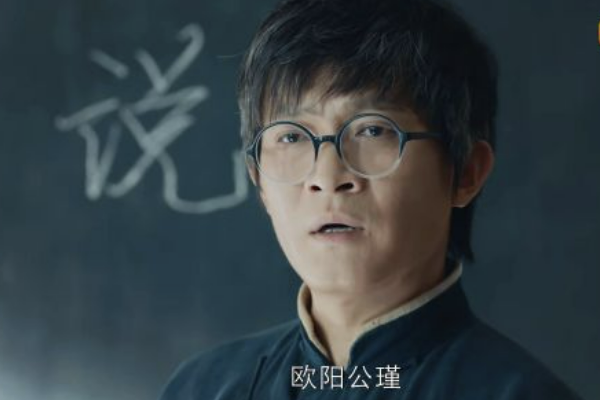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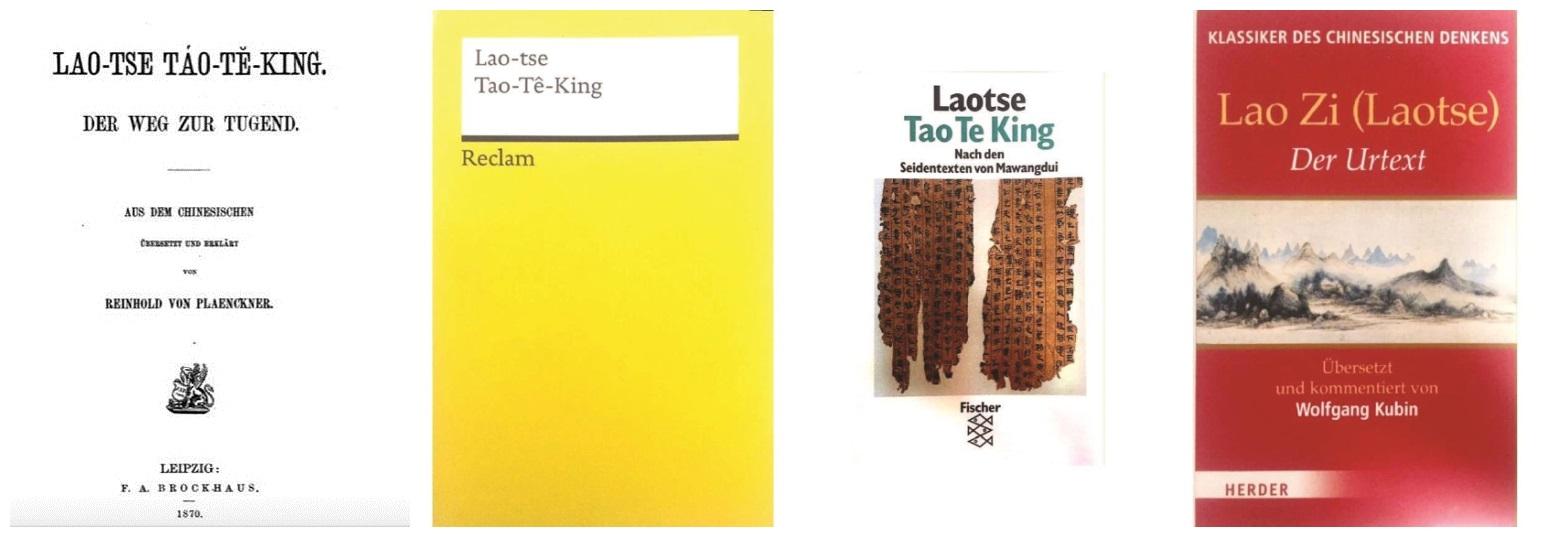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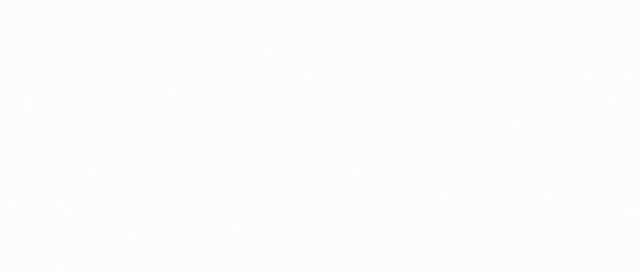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