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对于晚清的读报史研究,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入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报刊内容、形态、发行与影响,往往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加以证实与回应。读者读报不仅是看新闻、学知识、求交往,还通过报纸将个体融入到社会之中,他们在读报时分的所思所言所记,都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知、体验与记忆。
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应该是人,在晚清史研究中,关于“读书人”的思想、观念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但是,关于“读报人”的系统研究却并不多见。尤其是在近代新闻传播史的已有成果中,关于办报人、报馆与报纸的内容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新闻消费的终端,最值得关注的对象——读者,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虽然有些学者对《万国公报》、《申报》、《时务报》等报刊的阅读进行了个案研究,并揭橥这些报刊的价值与影响。但这些个案研究往往将读者视为“个体”,缺乏与其他报刊、人物与事件的相互观照。在整个晚清新闻史的研究中,“读者”与“阅读”的缺位乃是一个明显的不足。
在晚清社会,报刊固然是传递新闻最为重要的载体,其作用与价值随着清末时局的变动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时人往往将报纸之多寡与国家文明之进步联系起来。如果从系统的角度看,报人是生产者,报纸是产品,读者是消费者。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整个新闻市场的核心要素。如果过度突出报纸与报人,而忽略读者作为消费者的存在,就难以全面系统地了解新闻市场的全貌,更无法评价报刊是如何进入市场,并如何产生社会影响的。也谈不上研究读者读报纸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因此,读者的“缺位”是新闻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没有读者的“在场”,报刊存在的意义就难以证实。但是,在晚清报刊业发展的过程中,读者的“缺失”却是“常态”,从晚清报刊的生产角度看,早期的宗教报刊并非为真正意义的新闻纸,有效的阅读也较为有限,在从宗教传播到科学传播的转变过程中,才逐步引起少数开明士绅的关注,报刊作为“知识纸”的作用较为明显,而以《申报》为代表的商业性报刊,由都市社会向城镇社会传播的空间转变中,官绅和商人是其主要读者对象,新闻的社会性和广博性仍然有一定局限,商业报刊作为信息纸的特征较为突出。甲午以后,《时务报》蔚起,开启了从科学启蒙到思想启蒙的新时代,之后,《新民丛报》、《民报》等政论性报刊相继崛起,报刊作为“思想纸”的作用得到彰显。而随着白话报刊的普及,报刊作为“启蒙纸”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报刊作为信息载体,因其内容的差异必然对读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一、“读书人”向“读报人”的身份转变,其背后往往存在着“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保守”与“先进”等理念的认知过程
对于报刊读者的“忽略”,并非是许多研究者故意为之。即便是今天的“全媒体”时代,对于“受众”的重视也仍然不够。从统计的角度看,晚清社会很难有报刊读者的具体数字和阅读调查,尤其是早期的传教士报刊以免费阅读为主,其发行量与阅读率之间的关联性,基本上无从考究。即便如《申报》之类的商业性大报,在发行之初曾经宣称有颇多“市肆之人”阅看,但并没有具体的数字加以证明。而报刊自称的发行量更是存在着诸多疑问,许多代销处往往有大量过期的报刊退回报馆,其有效发行与实际阅读之间有较大差距。从量化的角度研究“阅报史”,的确有很大的难度。
虽然读报的过程较为复杂,但这并非说明读报的史料无从检阅。事实上,读报作为许多读者的日常活动,往往付诸于他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一些有心的读报人养成了在日记中记载读报活动的习惯,他们将读报所见所感付诸笔端,并形成了具有个体情感色彩的读报历程。在晚清无数的文人日记、自述中,蕴含了较为丰富的读报内容。尽管有学者进行了个案或者阶段性研究,但是对晚清日记与读报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通过日记来观察读者的阅读心态、社交网络、价值观念,可以直接而真实地反映报刊进入读者阅读世界的历史进程。而清末民初大量的回忆录、杂记、年谱,也有许多关于读报的史料,尽管这些作者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问题,但他们着重记录某些报刊及新闻事件,至少可以说明报刊对他们具有某种价值和影响。一些读者读报后所写的书信,则比较集中地反映读者对某家报刊或某一新闻事件的态度,通过向亲友“二次传播”而成为重要的“见证”。上述的“零散记忆”,往往通过当时报刊内容得以互证,如报刊刊登的大量读者来信与售报广告,便表明其发行范围与读者阅读的反响。总之,从日记、回忆录、杂记、书信、年谱、报刊等不同的文献来源研究阅报史,可以通过零散的史料中重新构筑阅报的情景和历史记忆。
因此,无论从晚清阅读史、文化史还是社会史的角度看,“读报人”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晚清社会在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方面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屡次入侵和宰割,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传统的逐步瓦解与“被动变革”的剧痛。在此过程中,读书人的思想世界有着极为复杂的变动,读书人的观念冲突与价值取向,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呈现诸多不同的“面相”。而在“时局阽危”的形势下,读书人对“现代性”的接受与拒绝也经历了极为复杂而矛盾的冲突。从这个层面看,作为现代传媒的报刊,是检验“现代性”的重要标识,“读书人”向“读报人”的身份转变,其背后往往存在着“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保守”与“先进”等理念的认知过程。报刊既为读者建构了“情感共同体”,也为读者提供了“思想版图”。1905年,一篇时论对读报的意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中国读书人多矣,读书者亦众矣。而往往求博古之才则易,求识时之才则难,何也?良以考古之道在乎读书,而通今之务莫如读报,报即今之书也。”(李洵:《华字汇报缘起》,见《大公报》,1905年6月3日)因此,当现代报刊进入读书人的阅读世界,“读报人”必将成为观察晚清社会的一道绮丽的风景,“读报人”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是报刊阅读的历史轨迹,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二、晚清报刊如何影响读者进而改变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报刊阅读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面向,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读者读报既是一种仪式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回顾。晚清报刊如何影响读者进而改变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的传教士将报刊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他们虽然具有“眼光朝下”的宗教情结,但是宗教报刊在底层社会的传播却收效甚微。“蛮夷”与“邪说”的概念深存于下层民众的观念之中,对于传教士所谓的“融合中西”的传教理念,也很难得到民众的回应。但鸦片战争前宗教报刊阅读率的低下,并没有打消传教士的办报热情,他们对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也终于得到了少数中国士大夫“睁眼看世界”的回应。鸦片战争后,他们对下层民众的传播策略虽有所变动,并且以“西方新闻”、“社会新闻”吸引读者的关注,但仍然收效甚微。在上海、广州等口岸城市,很少有下层民众对宗教报刊感兴趣。而少数“口岸文人”由于被生计所迫,在被外报聘用的过程中,“被动”地阅读宗教报刊,这些“落拓文人”将编报、阅报视为一体化的工作,他们虽然视报馆谋生为末路,但却在无意中兼具读书人与读报人的双重身份,进而对晚清社会的报刊阅读起着先导作用。
洋务运动对报刊阅读有着重要的影响。洋务官员对现代传媒的认知远超一般士绅。从刘坤一、张之洞、沈葆桢、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吴汝纶等人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大量读报纪录,与早期的口岸文人的被动式阅读不同,这些高级官员和幕僚往往将“饭后读报”视为一种生活习惯,并摘录某些重要新闻以示重视,有时还配上一段评论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一些阅“外国新闻纸”的纪录,已表明他们具有洞察“西方世界”的眼光。少数政治精英的读报活动,虽然没有影响到整个上层社会,但却开启了阅报史的新时代。他们对现代报刊的观感,虽然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但他们通过读报可以增见闻、长智识、学西学,从而与传统守旧的官绅有着明显的区隔。
1872年,《申报》作为商业性报刊的发行与传播,对报刊阅读的扩张有着重要意义。尽管早期的《申报》发行量不大,却在提供新闻、制造舆论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并由此在“现代阅读”中引发较多的关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绅便通过阅《申报》而知时事、评时政、抒胸臆、摆观点;一些文人骚客通过投稿来改变“书写方式”,在《申报》中寻找文艺滋味与自我价值;而一些商人则通过在《申报》中刊登广告来寻找作为潜在消费对象的读者。《申报》为“四民”服务的口号虽然有些夸张,但其文体走向浅易却是适应报刊阅读所需。报刊的通俗化虽然经由传教士的努力有较大改观,但《申报》作为商业性报刊却已经脱离了“古典”的范式,使读者感受到现代传媒的无穷魅力。
读报纸就是读社会、读时代。商业性报刊的职业化分工,使其新闻更具可读性。《汇报》、《新报》、《述报》、《广报》等报刊对地方新闻和社会新闻的重视,有利于商业性报刊的地域性扩张。中法战争前后,报刊对新闻时效性更为关注,读者往往将重大时政问题作为日记中的议题。但是,由于阅读观念、传播技术与邮政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在甲午之前,整个社会精英阶层中读报人的数量十分有限,至于下层民众,则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报刊。报刊发行主要集中于通商都会,城镇社会的民众难有机会订阅,乡村社会更是置若罔闻了。报刊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缩影,只是集中在几个口岸城市。即便读书人具有读报倾向,但报纸的“可得性”是一个现实的难题,从地理空间上看,北方地区的读者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现代报刊。
甲午战争是清末“过渡社会”开始的标志,在士绅阶层向知识人转变的过程中,在古典与现代、保守与前卫、中学与西学之间,读书人面临着身份认同与价值取舍。而读书人是否愿意看维新报刊,更是立场与观念的考量。甲午之役,国将不国,维新报刊以“变法图强”的观念引领社会思潮,很快得到知识界的广泛回应,围绕着《时务报》等维新报刊而形成的读者群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阅读共同体”。维新报人运用其广泛的人脉资源和发行系统,将报刊渗透到“城镇社会”和“乡村社会”,维新言论使许多读书人“如饮甘泉”,在知识界产生巨大的震动,乃至达到“梦寐以求”的地步。尤其是学校、学会与报刊三者之间的互动,在整个士绅社会中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由此吸纳更多的读书人加入到维新报刊的阅读潮流之中。与守旧的士绅不同,新式知识分子对报刊的态度有着明显的改变,他们往往能够观察到报纸文字背后的“问题”与“主义”。
对于读者而言,维新报刊为他们界定了“新”与“旧”的理念,赞同与拒绝意味着政治界限的划分,士绅社会内部的分化已成为必然。时人对“开明”与“守旧”的划界,往往以是否赞同“变法”作为标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报刊舆论领袖,极大地发挥了言论引领思想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报刊阅读革命。虽然以维新报刊的发行量估计,其读者数量并非特别庞大。但是,《时务报》在数年间的重印与“二次传播”,已经在知识界形成巨大的“从众效应”。
三、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末社会已进入“报刊社会”,尤其是随着白话报刊的广泛传播,报刊已普遍树立为中下层社会服务的意识
维新之后,新式报刊虽一度受到查禁,但是,随着庚子事变的发生,“国将不国”的现实已使读书人对现有体制产生强烈的不满。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界已经不再满足是否变法的讨论,而是对“国家”与“朝廷”进行了划分,读书人对清朝朝廷的统治合法性产生了强烈质疑。而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虽然以“保皇立宪”为口号,但是报刊言论对民主、自由、新学、宪政的鼓吹,却客观上使读者了解到中西方社会制度的明显差异,旧思想、旧制度、旧习气由此成为读者憎恨的缘由。清末的十年新政,虽然是在旧制度下的局部改革,却有利于新式报刊的快速发展。以“合群”为价值导向的各种社会力量,在寻求“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学会、社团与派系,这些组织以政论性报刊体现其宗旨,进而激发读者的阅报热情,并促进社会运动的发展。
清末新政客观上促进了“学生社会”的发展,在改书院、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读书人的身份发生了分化,士绅社会虽然还具有较为强大的政治与文化资本,但新式学堂学生的数量急剧增长,并在1909年前后超过士绅的人数。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并存的局面,使读书人在阅读时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导向。学堂学生向往经典之外的现代阅读世界,对进步报刊与革命报刊趋之若鹜,进而对旧制度展开全面评判与反思,在思想与行动上与“守旧士绅”进行区隔。清末留学生报刊和革命报刊在学生社会所引发的巨大反响,使报刊作为“思想纸”、“政治纸”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尤其是革命报刊吹响“革命排满”的号角,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社会的革命想象和斗争激情。围绕着民主革命还是君主立宪的道路选择,学生社会与士绅社会的分歧也愈加明显。读者对报刊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生道路与政治立场结合起来,从而体现“读报纸”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引领作用。
尽管清末许多报刊存续时间较短,但是上千种报刊的发行已形成了巨大的阅读“景观”。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末社会已进入“报刊社会”,尤其是随着白话报刊的广泛传播,报刊已普遍树立为中下层社会服务的意识。而阅报社、讲报所在基层社会的不断推广,使许多“买不起报”、“买不到报”的读者有机会进入“公共阅读”的空间。尽管清末的识字率还较低,“愚夫愚妇”仍然无法读报,但“劝民读报”与报刊所引发的阅读革命已在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反响。“读报纸”与“识时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报刊舆论对下层社会阅读的广泛推动,使现代阅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虽然仍然有一些守旧士绅沉醉于“古典世界”,对现代报刊采取抵抗式阅读的态度。但是,科举社会已经终结,经典阅读不再提供“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在新式学堂,西学与新学已超越儒学,学新学谋新路求自由已成为学生读书的重要目标,读新式书报已成为大势所趋。苟欲通达时务,而清政府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挽救危亡的努力,客观上推动了知识人社会的崛起。同时,清末社会所产生的撕裂性变革,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力量的整合,进步社团与革命团体不断发展,社会界别的概念不断推广,新式报刊的政治符号与身份符号得以凸显,其思想资源对读者的价值观与道路选择起着重要作用。“看何报”与“知何人”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读报人在清末政局变动中的“在场”,已经通过报刊体现传媒文化的广泛影响。
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对于晚清的读报史研究,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晚清时局的变动,与报刊之间存在互动互证的关系。新式报刊从西方移入之后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对读者的阅读历史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报刊内容、形态、发行与影响,往往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加以证实与回应。读者读报不仅是看新闻、学知识、求交往,还通过报纸将个体融入到社会之中,他们在读报时分的所思所言所记,都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认知、体验与记忆。读报纸就是读社会,如果说新闻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新闻。读者则是新闻与历史的见证者。没有读者的存在,新闻与历史都无法进入社会化的过程。(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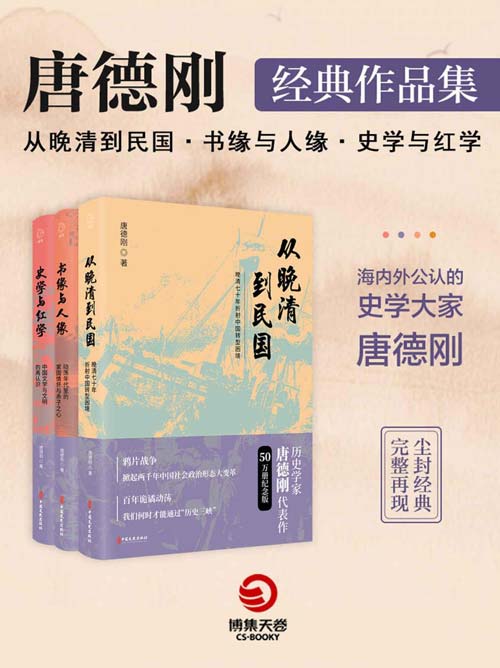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