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歪着脖子的人,如果遇上一个天生歪着脖子的人,加上看人的眼神睥睨,直面对视,我会觉得是一种挑衅,不怀好意。第一印象后就躲得远远的,不想再深入交流;我可怜那些弯着腰的人,如果一个平时气宇轩昂、玉树临风的谦谦君子,见到某些人时,原本笔直的腰,忽然像在背后吹来十二级的大风,深深地弯了下去,那不是一种鞠躬般地恭敬,更像是一种屈膝地刻意奉承。我感叹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的人。曾在僻远的农村,荒宅旧院深处,遇到过一个腰弯得像炸熟了的虾一样的老人,穿着蓝布大襟衣服,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蹒跚迈出大门,身后跟着几只摇摇晃晃的鸭子。她努力地抬起头,用混浊的眼睛看我,带着的沧桑和不屈。在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时光在她身上流淌的印记,在岁月的长河里,就像那长歪了的树,在阳光和雨雪的重压下形成压不垮的模样。我莫名就有一种说不出味道的情感,在心头暗生滋长,不知道是悲悯还是感动。
很奇怪,小时候我就喜欢长歪的树。觉得歪着脖子或是身段的树,好玩,可爱,甚至还有那么一点俏皮。它们不会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我从小在山上奔走,看惯了山上的荒草、松木、杉木、樟木、各式杂木。太正太直的树大部会被留着当檩条,当屋柱,当栋梁。高大挺拔的样子,我举着砍刀也不忍下手砍上一刀,一怕大人的责骂,也怕它身上流下稠稠的,白白的液汁,像受委屈流出的眼泪。说不定哪天我要盖房子,需要用到它们。等它们长得更健壮,更成熟,年轮更密实,再把它们一根根背回家,削皮锯板。它们可以从此不再受风吹雨淋,我也可以在它身体发出的独特气味中,满足地露出笑容,安然入梦。这是长得端端正正树的优势和用处,是那些长歪了树做不到的。长歪的树连砍柴的人都懒得要,捆好它都需多花费些气力,要多砍上几刀,把弯的一段段变成直的。如果弯得好还可以做个牛轭,或是做个犁把手,牛轭白天骑在牛脖子上,弯犁带着铁犁头被牛牵引着犁地,晚上一起放在牛栏一角,整夜陪在牛的自言自语和粗鲁的呼噜声里,这是它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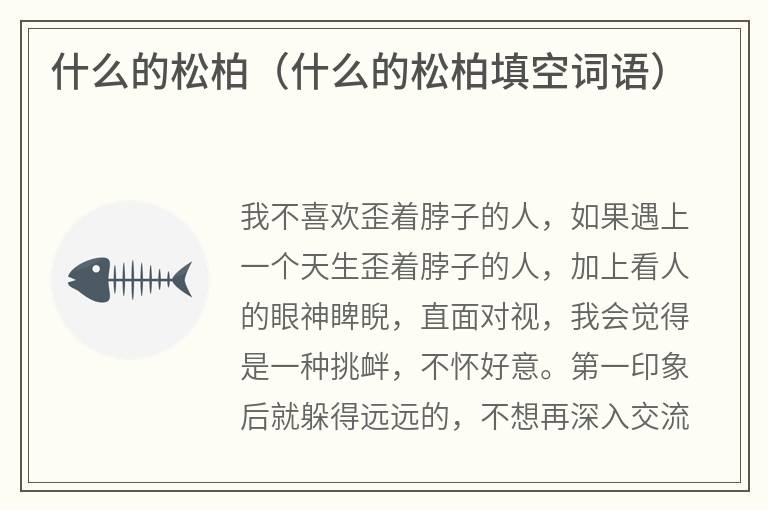
什么的松柏(什么的松柏填空词语)
我家铁沙岗责任田田角,曾有一棵歪脖子的松树。它长在路边的空地上,认识它的时候我十三、四岁,它有碗口般粗。我跟着父母到责任田插秧,施肥,割稻,一到地方,就把带的中午要吃的饭袋挂在它的脖子上,树底下胡乱地摆放着几块大石头。吃饭时,我看见弯着腰的松树底坐着一样弯着腰的父亲。它沐着风和阳光,父亲劳累后享受着片刻的阴凉,卷起一支喇叭烟,深深地吸上几口,烟雾瞬间被风吹散。
我不清楚这棵松树是什么时候歪了脖子弯了腰的。是出身时就根不正苗不红,还是后来某天的一阵风折了它的腰,又或许是在田里劳作的人,每天把中午吃的饭袋都沉沉地挂在它身上。它心想,反正每天都要跟着你们一起经历风雨,承受生活,索性懒得直起身了,这样弯着也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习惯了生活的重压后,要挺直身姿换一个姿势也是很累的事,这样子挺好。
我从未懂我父亲的心思,也不会去猜测松树的心思。休息的时候,会随意用柴刀在它身上砍上几刀,父亲看都不看一眼,不知道他在不在乎,我以后也会像那棵松树一样长歪了,长大后连做檩条的资格都没有,也许能长歪做一个牛轭,跟着黄牛一起犁田。我干活经常偷懒,干一会就躲到松树底,一屁股坐在松树的弯腰处,用早上刚在磨刀石上磨得发亮发青的刀口,刮刮歪脖子松树身上并不厚实的鳞片,也刮刮自己刚刚初长的腿毛,用松针逗逗爬在松树身上匆匆赶路的黑头蚂蚁,扯着脖子呼叫几声迟来的风,听闻远处间隙的鸟叫,看看头顶上空我家的那几片云。几年之后,它的身子结满了疤,脖子更歪了,腰更弯了,像被地面牵引着,似乎要把它拉进泥土。
后来,我不再爬岗背岭,就再也没见过它,每次回村,看到村里的墙角处又多了几个人驼了背弯了腰。曾经坐在它的脚下,弯腰劳作的父亲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知那棵歪脖子松树是否安好,我在它身上砍的伤口,想来应该早就结疤愈合了。
西溪右岸,西阳桥头,溪岸的斜坡上有二棵苦楝树。一棵高大挺拔,一棵歪着脖子,侧向溪流倾斜着身子,像一个窃密者凝神屏气在听着溪流的窃窃私语。那姿势像极了铁沙岗的那棵歪脖子松树,让我想起父亲坐在歪脖子松树下吃饭吸烟的陈事旧影。苦楝树下是菜地,不知是谁家的,种着各种蔬菜。
绿道未修建前,在后龙山隐约传来的梵音中,我在溪的左岸看它们晨起日暮,它们在西溪的右岸看我匆匆来往。我会多看几眼那棵歪着脖子的苦楝树,看它在春风中抽出了新的芽叶,烈日下枝叶渐渐葳蕤,秋风里树叶枯黄飘落,冬雪里光秃秃的枝头只剩一绺绺的苦楝挂着。一群没人管的鸟停在枝间,双脚抓着细枝,歪着头,旁若无人地啄着果实。如我少年时拿着柴刀坐在歪脖子松树上的模样。
绿道修建后,我每天从它们身旁经过,斜坡曾植了草皮,不久又变回了菜地,蔬菜成熟的时候,在苦楝树下竖一木牌,用毛笔写上“菜施农药”。每次我走近它们的时候,都要停留片刻。在西溪氤氲晨雾里,歪着头的苦楝树,树下的潺潺溪水,树枝上跳动的鸟,西阳桥上走过朦胧着荷锄的农人,全笼罩在那一片暖色光影中,恍如梦境。
我以为会是一直这个样子,永远美好,没人会在意这棵没有多大用处的废树,它长在桥边搭配成一个风景是最好的,带给西溪另一种超出用途之外的美感。每棵树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人生也是如此。
只是这梦忽然就破了,只在一夜间,我没有听到任何声响,这棵不知长了多少年,没人要的歪脖子苦楝树就消失地无影无踪,连树根都没有留下,没人知道它去了哪儿,甚至没人在意它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知道,它曾经来过,临水而立,可爱,俏皮,可以横斜到溪水的波心,横斜进我久远的思绪。没有了这棵歪脖子树,西溪桥便没有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情趣,水和桥仿佛失去了灵魂。
我曾不喜欢歪着脖子的人,后来才知道,不管我喜欢与否,那都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存状态,没人喜欢歪着,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姿态,在时光的指针里卑微而倔强地活着。我喜欢歪着脖子弯着腰的树,它早就看淡了风云。
没人知道我的心思,包括这棵伫立溪边歪脖子经年的苦楝树,那些停在上面觅食许多年的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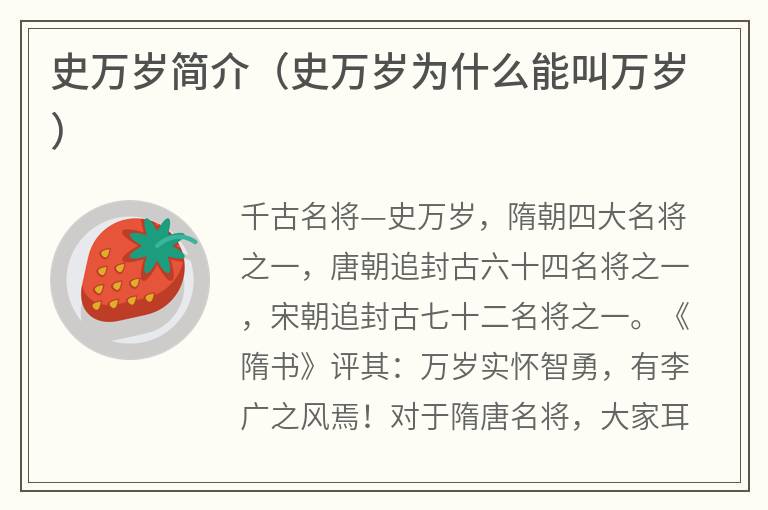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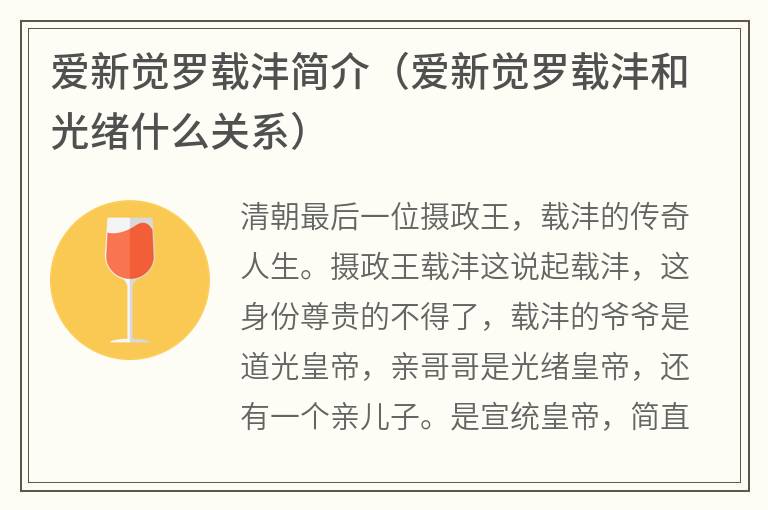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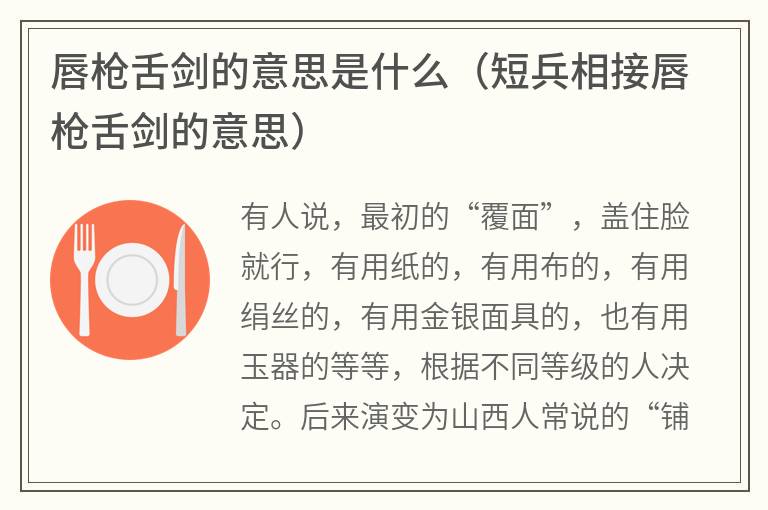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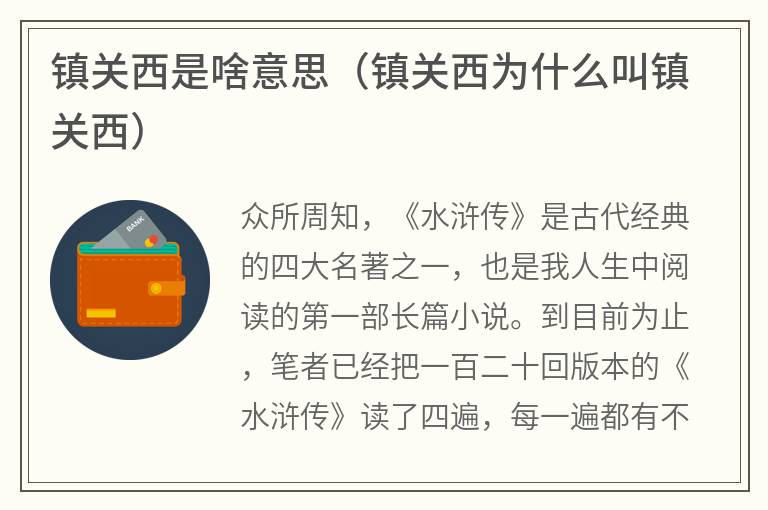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