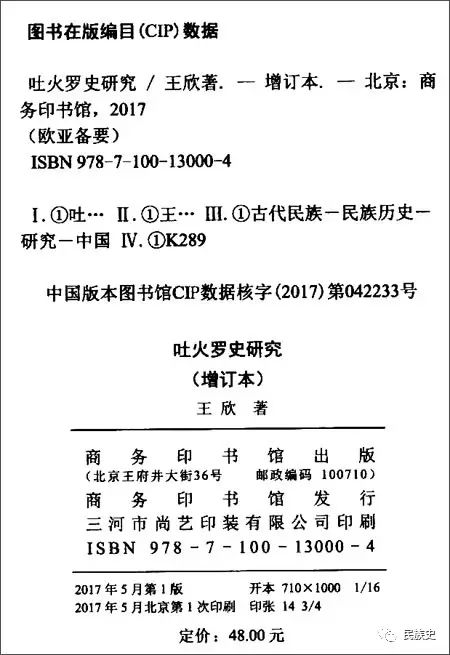
文摘
第一节 吐火罗的族名
一、吐火罗一名的由来
古代东西方的各种文献中,包括那些曾流行于古代中亚地区而现在早已消亡的各种所谓的“死文字”里,有许多都曾提到过“吐火罗”之名。这些文献包括汉文、古希腊文(Greek)、于阗文(Khotanese)、粟特文(Sogdianese)、吐蕃文(Tibetanese)、回鹘文(Uygurese)、梵文(Sanskrit)和阿拉伯—波斯文(Arab-Persia)等,几乎涵盖了曾使用这些文字、在古代中亚地区活动的所有民族留下的文献,时间延续长达一千年。仅此一点就可以反映出历史上吐火罗人在这一地区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性,及其在东西方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史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
关于“吐火罗”一名的由来,史无明征,其含义亦至今无从知晓,甚至在吐火罗语(Tocharian)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吐火罗”一词。人们对这一名称的认识始终是模糊的。但可以肯定,“吐火罗”是古代诸民族、国家对这一古老民族的称谓,并为后世所承袭。20 世纪初以来,结合有关吐火罗人起源问题的讨论,国际上有学者曾对“吐火罗”一名的由来做了种种推测。著名的英国伊朗学家贝利(H.W.Bailey)教授认为,“吐火罗”(Tochari)一词(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名著《地理志》中作“Θογαρα”)原由两部分构成,即前一部分to- (又作tho- 和tu-),后一部分Gara(即*γαρα)。前者(to-)相当于汉语中的“大”(ta);而后者(Gara)则为一个古代民族的称谓。该民族在8 世纪的吐蕃文献中被称作*Gar (吐蕃文献中共有三种形式:mgar、hgar、sgar)。在8—10 世纪的于阗塞语文书中被称为Gara,主要活动在那一时期的所谓南山(即祁连山)中。贝利进一步指出,Gara(*Gar)相当于托勒密《地理志》中的Θογαρα,汉文文献中的月氏(üetsi)。 贝利的研究对于探索“吐火罗”一名的来源无疑具有启发性。
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月氏在公元前177—前176 年被匈奴从河西逐往伊犁河和楚河流域的塞种故地以后,“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就是贝利将Gara (*Gar)比拟为月氏的根据所在。但在8—10 世纪时,这部分小月氏人早已与当地的羌人相融合,并与这里的其他游牧诸族共同形成一个以地域(南山)为中心的多民族融合体。被称作“仲云”,或“众熨”、“众云”、“重云”、“种榅”等。五代时高居诲《使于阗记》中明确记载:“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氏之遗种也。”小月氏之名此时已为仲云所取代而不复存在,在敦煌汉文文书中又称南山人。他们后来成为吐蕃统治下的南山部族中的一部分,相当于敦煌所出伯希和吐蕃文卷子1089 号中的Lho-bal (南人)、斯坦因敦煌汉文卷子542中的“南波”。5 而在敦煌于阗文文书中,仲云则被称为Cimuda(Cumud 或Cimnda)。故以8—10 世纪时期的Gara(*Gar)比称月氏似有不妥。此外,在贝利等学者看来,月氏即吐火罗,这恐怕也是他们将Gara 称作月氏的一个前提。正如后面所论述的那样,我们认为月氏和吐火罗尽管关系十分密切,但两者显然分属不同的民族,不能将他们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我们同意贝利将Gara 比作吐火罗的观点,但不认为Gara 与月氏同族。
著名的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曾将吐火罗人与西亚楔形文字中所出现的古提(Guti)人等同起来,在他看来,Guti 人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公元前三千纪之末和其兄弟部族Tukri 人离开波斯西部远徙中国,“月氏”一名最终源于Guti,“吐火罗”一名最终源于Tukri。他们则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1 亨宁这一假说显然极富想象力,可备一说。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汉文文献中的“大夏”是迄今所知中外各种文献中对吐火罗人的最早记载。
早在1901年,马迦特(J.Markwart)在其名著《伊兰考》( rān ahr,Berlin1901)中首次提出“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中国学者王国维、黄文弼等则进一步探讨了大夏(即吐火罗)人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活动情况。2 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论,但大夏即吐火罗这一观点近年来已日益为我国更多的学者所接受。3 正如我们下面所讨论的那样,早在先秦时期,大夏(吐火罗)就曾活动于中国北部及河西走廊一带,同月氏关系十分密切,二者多次并见于先秦时期的汉文文献中。可能在公元前3 世纪后半叶,受乌孙、月氏战争的影响,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大部分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地。据研究,他们仍有一部分留在原地。4 留下来的这部分吐火罗人可能人数不多,主要活动于敦煌以南的祁连山中,在后世影响不大。有迹象表明,残余下来的吐火罗人集团在8—10 世纪时仍活动于这一地区。上引高居诲《使于阗记》中所记“胡卢碛”之“胡卢”即为“吐火罗”的别译。5 要之,则于阗文中的Gara、吐蕃文中的*Gar 和汉文中的“胡卢”所指的均是还活动于敦煌至罗布泊一带的吐火罗人后裔。所以,与其将于阗文和吐蕃文中的Gara(*Gar)比拟为月氏,倒不如将之视为吐火罗余众似更接近事实。如果以上推论不误,那么Gara(*Gar)很可能就相当于汉文“大夏”中的“夏”。正如贝利教授上文指出的那样,希腊文Θογαρα 一词前一部分to-(tho、tu)相当于汉文中的ta(大)。所以,我们认为,“吐火罗”一词很可能亦由两部分构成,即to-相当于汉文中的ta(大)之对译;*γαρα,相当于汉文中的“夏”,亦即于阗文中的Gara、吐蕃文中的*Gar。当然,无论是汉文文献中的“大夏”,抑或是其他西方文献中所记的吐火罗之名,其本身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指称吐火罗人的,在实际中则不能将其分开,更不能根据汉文字意将“大”、“夏”二字分加解释,如“大月氏”、“小月氏”之类。此外,吐火罗(Tochari)在公元前141 年左右进入巴克特里亚(Bactria)之后才见诸西方文献之中,显然要晚于汉文文献,所以,汉文中的“大夏”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详加讨论。
二、汉文文献中所见吐火罗
在汉文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一名的译写形式十分繁杂,又因时代的不同、史料来源的差异而多有变化。但将它们归纳起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其中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为明晰起见,兹将汉文非佛教文献中所见吐火罗一名的各种译写形式,大致按其所出现时代的先后顺序,列表如下。佛教文献中的有关记载随后集中讨论。
从上列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夏”是汉文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首见于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之中。在这一历史时期,大夏(即吐火罗)主要活动在晋南及晋北或河套以北地区。1 如我们下面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带亦可视为迄今所知吐火罗人迁徙发展的最东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于公元前128 年前后到达阿姆河流域,将西迁后灭亡并占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aceo-Bactria Kingdom)的吐火罗人所建立的国家径呼之为大夏。《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采用了这一称呼。众所周知,张骞在中亚地区曾活动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对那里的各种情况当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他在记载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时采用“大夏”这一古代名称,绝非偶然。这表明他已敏锐地发现了这里的吐火罗人与曾出现在古代文献中的、原活动于中国北部的“大夏”的某种联系,而并未仅仅从二者在对音上的相似之处考虑。2《新唐书·西域传》所云“大夏即吐火罗也”,似乎是后人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确认。
“敦薨”或“敦煌”是汉文文献指称吐火罗人的另外一种形式。据研究其得名直接源于“大夏”,系“大夏”一词的同名异译。 3 从上列表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敦薨”一名首先出现于先秦时期,但其时间要明显晚于大夏。如我们下文所讨论的那样,“敦薨”一名出现时,吐火罗人已从晋南、晋北一带迁往河西地区,所以它所指的实际上是已活动于河西地区的吐火罗人。
从汉文文献中记载吐火罗人的这种名称变化来看,当时人们对大夏西迁河西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所以并没有把在河西一带活动的吐火罗人与之前曾活动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大夏人联系起来,且将他们作为未知民族而用“敦薨”一名加以指称。至西汉武帝开河西通西域时,这里的大部分吐火罗人早已离开河西,并经伊犁河、楚河流域迁居阿姆河中上游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境内。虽然仍有一小部分吐火罗人留在河西,但他们可能已退入祁连山中活动,故不为汉文史家所注意。尽管如此,“敦薨”之名作为吐火罗民族的遗存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研究,汉代敦煌郡的得名就直接源自“敦薨”一词。1“ 敦煌”之名因此一直沿用至今。《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下应劭注云:“敦,大也;煌,盛也。”研究者已经指出:“这种解释,纯属望文生义。” 2 同志“陇西郡”条下有县名曰“大夏”恐亦得名于吐火罗人的活动。此外,在《汉书·西域传》中还记有“去胡来王”之名。据研究,“去胡来”亦为“吐火罗”之对音,皆“大夏”之异名。 3“去胡来”主要活动在今阿尔金山一带,从下文所讨论的吐火罗人的迁徙史来看,这部分吐火罗人更可能是吐火罗人早期东徙时的余部。
一般来讲,“敦薨”在汉文文献中用于指称活动在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但从《山海经·北山经》的注文之记载来看,活动在西域焉耆一带的吐火罗人也首次受到了注意。这一地区所留下的敦薨之山、敦薨之水、敦薨之浦、敦薨之薮等即为当时吐火罗人在这一带活动所留下的影响遗迹。联系“敦薨”一名出现的年代来看,焉耆一带的吐火罗人与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大致属同一时期的。需要指出的是,焉耆一带的吐火罗人是在早期东徙过程中受阻而留居于此的,与另一支东徙中国北部、复又从河西西迁中亚的吐火罗人早已失去联系。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述。
东汉以降的汉文史籍中大致上相继用兜勒、吐呼罗、吐火罗、吐豁罗、胡卢等名指称吐火罗人。此时,吐火罗人的主体早已在阿姆河中上游一带,亦即后来玄奘所称的“覩货逻国故地”或穆斯林文献中的吐火罗斯坦(Tūkhāristān)定居下来。汉文文献中的上述名称(“胡卢”除外)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活动在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汉文这些译写形式可能均源于东汉至唐当地或周边民族对吐火罗人的称谓。如粟特语中的 ’tγw’r’k,回鹘语中的twγry、twxry、twqry 等,而这些称谓无疑又均源自希腊人对吐火罗人最早的几种称谓形式,如Tóχρoι(Tocharoi)、Θογáρα(Thogara)、 Tακοραιοι(Takaraioi)等。6 显然,从上述汉文中关于中亚吐火罗人名称的译写形式的种种变化及其来源来看,东汉以后的汉文文献已基本上将中亚的吐火罗人与过去曾活动在中国北部及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即大夏人、敦薨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渊源关系完全割裂开来。张骞通西域以后试图将中亚的吐火罗人与历史上的大夏联系起来的努力遂宣告失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汉文典籍对大夏的西迁活动多语焉不详,只留下一些有关的地理名词,使后人摸不着头脑,难以遽断;另一方面恐怕是因为东汉以后,中原战乱频起,诸王朝分裂割据,无暇西顾,同西域、中亚的政治联系有所削弱所致。值得注意的是,《魏略·西戎传》中曾有“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的记载。 1 此处称吐火罗人在中亚建立的国家为“大夏”国,似乎是时人对张骞在中亚认识的某种继承和认同。但除了《新唐书·西域传》曾提到“大夏即吐火罗”之外,这种继承和认同如过眼云烟,终为后世所忽略。中亚吐火罗人与大夏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亦告断绝。当汉文文献重新关注中亚的时候,吐火罗人遂以一个未知民族的崭新面貌见诸史端。
目前,学术界在《后汉书·和帝本纪》及《后汉书·西域传》中所提到的“兜勒”所指为何的问题上分歧较大。《和帝本纪》云:永元十二年(100)“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西域传》复云:“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张星烺首先认为:“蒙奇即马其顿(Macedonia)之译音,而兜勒则为吐火罗之译音。”莫任南却认为兜勒应指的是色雷斯(Thrace)。林梅村则不同意张星烺和莫任南关于“兜勒”一词的比附,在他看来,“兜勒”应是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Tyre)的音译。4 他将《后汉书》的上述记载同公元100 年前后发生的一次罗马商团出访洛阳事件联系起来。但“兜勒”与汉文佛教文献中的“兜佉”(《正法念处经》)、“兜沙罗”(《杂阿含经》)和“兜佉勒”(《高僧传》)在译写形式上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均源于古印度梵语中的Tusāra。5 所指的均当是活动在原巴克特里亚一带的吐火罗人。此外,在《后汉书》的上引记载中我们也能看到,兜勒和蒙奇是共同遣使的,两国自应相距不远且关系密切。据考订,“蒙奇”所指的就是与吐火罗斯坦西邻的马尔吉亚那(Margiana)地区,“蒙奇”或即为Margiana 之音译。 1 这一点在对音上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倘如此,则这从一个侧面或也证明“兜勒”所指应为巴克特里亚一带的吐火罗人。当然,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做进一步探讨。
东汉末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众多的异域僧侣东行弘法、内地高僧西行求法活动的展开,大量佛教典籍被引介并译成汉文。在这些典籍及内地高僧的各种行纪和撰述中,亦多见有关吐火罗人的记载。这些记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吐火罗历史、文化的认识。
在汉文佛教文献中,“吐火罗”的译写形式亦多有不同。“吐火罗”(Tochari)一名在《梁高僧传·昙摩难提传》和《鞞婆沙论》中均作“兜佉勒”,《正法念处经》中作“兜佉”,《大智度论》中作“兜佉罗”(还有作“兜呿罗”者),《杂阿含经》中作“兜沙罗”。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作“覩货逻”,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均基本沿袭玄奘的译法,作“覩货逻”(或“覩货罗”)。唯慧超之《往五天竺国传》中作“吐火罗”。“兜佉勒”、“兜佉”和《后汉书》中所记“兜勒”有可能均源自佛教梵语(Buddhist Sanskrit)中的“Tokhari”。“ 兜佉罗”、“兜呿罗”、“兜沙罗”等则可能源于梵文中吐火罗的另一种写法“Tusāra”。玄奘所称的“覩货逻”无疑源于梵文中的“Tukhāra”。他还试图用“覩货逻”这种译写形式,校正常见于史乘的“吐火罗”,但据研究,他“或许意在强调梵名原文Tukhāra 第二音节为长元音”之故。这些佛教典籍和有关撰述中所反映的基本上均是吐火罗人在中亚吐火罗斯坦活动的情况,它们对汉文正史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吐火罗人在中亚历史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材料。
从对汉文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各种译写形式的分析及其演变历史来看,我们认为,“大夏”是汉文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名称,原来主要是指活动于中国北部的吐火罗人。这种写法多见于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之中。张骞通西域后,对西迁中亚的吐火罗人复以此名对之加以确认,《史记》、《汉书》袭之,《魏略》则对此加以继承和认同。此后,除《新唐书》外,以“大夏”指称吐火罗的这种形式遂从汉文文献中消失。在吐火罗人西徙河西后、西迁塞地前的一段时间里,汉文文献中一般用“敦薨”一名指称在河西地区活动的并以敦煌为中心的吐火罗人,顺及焉耆一带的吐火罗人。
东汉以后,汉文史籍中则又用“兜勒”、“吐呼罗”、“吐火罗”或“吐豁罗”等指称已定居于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在佛教文献中则作“兜佉勒”、“兜佉”、“兜佉罗”、“兜呿罗”、“兜沙罗”、“覩货逻”等。所以,汉文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的各种译写形式的演变,多少也能折射出吐火罗人从中国北部到中亚阿姆河流域迁徙发展的某些轨迹。需要指出的是,中亚诸民族在称呼吐火罗人时的各种差异,以及各地吐火罗人的土著化,很可能也是造成汉文文献中对吐火罗之名译写形式繁杂的主要原因之一。
★

弘扬民族文化,
增进民族团结。
汇聚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资讯,
记录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进程。
投稿:minzushi@yeah.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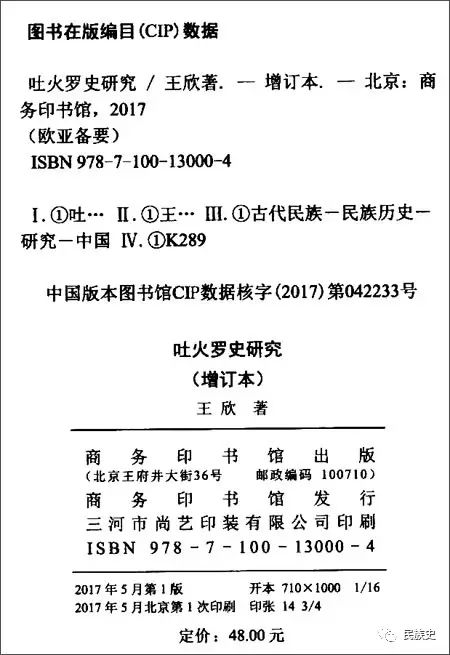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