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重证据法是力求最大程度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其最先为王国维先生定名,后内涵不断扩大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研究之中。二重证据法离不开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两重证据,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在两重证据方面的丰富性为二重证据法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使用二重证据法,需要对两重证据进行仔细择取与合理使用,其具体实践以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最为典型,该书同样使二重证据法的学理意义充分展现。
关键词:二重证据法;历史考古;《白沙宋墓》
上世纪初,在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和新史料大量发现的背景之下,时任清华大学导师的王国维率先将“二重证据法”提升到方法论层面,即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相互结合、彼此印证。“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使用为其时的古史研究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时至今日仍被研究古史的学者奉为圭臬。近一个世纪以来,二重证据法的使用渗透到除历史学、考古学以外的学科领域,许多学者亦对王国维使用的“二重证据法”进行反复审视,试图厘清王国维所言“二重证据法”的真正内涵,并将二重证据法的内涵拓展开来,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更具时代性的现实意义。甚或有学者根据“二重证据法”提出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以求最大程度复原古史的真实面貌,究其根本而言却始终脱离不开地上与地下的二重证据。实际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同样脱离不开地上证据与地下证据,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为宿白所著的《白沙宋墓》。本文尝试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对二重证据法的界定进行再审视,借以推定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二重证据的择取与使用,进而通过《白沙宋墓》一书管窥其如何实践。
一、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再界定
1925年王国维在为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一课时,提出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其在“总论”中如是说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这一论断的目的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讨论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人物及其行事,具有明确的对象性和时代性。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13年,王国维就已经于《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提出“二重证明法”[2],但相较之“二重证据法”,显然后者的提法更为周密严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非全新的方法,以地下之材料考证纸上之材料早已为金石学者所使用,而王氏只是将这一方法系统化和理论化,并赋予“二重证据法”之名。究其根源而言,“二重证据法”一方面受传统金石学的影响,尤其是继承乾嘉考证学派基础,以对传世文献补缺纠谬为目的;另一方面则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古代文献;加之当时的王国维秉持经世致用的观念而投身经史研究之中,意在改变天下道术将坠之局面。无论乾嘉考证学派,还是西方科学思潮,亦或是王国维个人的经世之心与学术追求,都导致“二重证据法”存在一个很明确的指向,即承认纸上之材料存在真伪之别,而注重以地下之材料区别纸上之材料的真伪,对地下之材料真伪的忽略就是西山尚志所言的“不可证伪性”[3],这一性质恰恰是王氏“二重证据法”的缺陷所在,其实质只能说是典型的证实主义。
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至今已近百年,其间“二重证据法”的内涵被不断拓展与深化,其固有的缺陷亦在发展过程中日渐消弭。王氏“二重证据法”的发展轨迹大体可归纳为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延续二重证据法之名,以王氏“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将证据内涵扩大到一切实物资料和一切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并提出其适用范畴与操作程序,代表学者有刘毅[4]、梁涛[5]、李锐[6]等人;一条是针对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将证据予以仔细分类,据以提出新的方法论名称,如饶宗颐[7]和杨向奎[8]等人引入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而提出“三重证据法”、叶舒宪[9]将考古实物及图像资料作为第四重证据而提出“四重证据法”。针对后一条发展路径来说,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在实践层面上对证据资料的使用各有侧重,但在理论层面上仍然跳脱不出二重证据法所界定的地下与纸上之二重材料,只是材料涵盖之内容大大超越王氏“二重证据法”,而趋向于前一条发展路径。由此,两条路径可以说是在同一出发点上的殊途同归。
王氏“二重证据法”的百年发展历程可归纳为对研究对象的拓展和对证据内涵的扩大,如今所提二重证据法远非王国维在上世纪所提出之概念,以涵义论之,前者为广义的二重证据法,后者为狭义的二重证据法。下文所讨论的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特指的即是广义的二重证据法。至于何为广义的二重证据法,其应指利用一切实物资料和一切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研究人类一切之历史,通过对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相互比对印证,达到更接近历史真相之目标的方法。
二、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证据的取用
历史时期即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固有地下与纸上之双重材料,为二重证据法的发挥提供广阔的天地。虽然二重证据法生长于古史研究的沃壤之中,乃至如今仍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但古史研究在传世文献上的缺乏与真伪难辨,导致二重证据法的使用需要慎之又慎。相反,历史时期保留有大量传世文献与实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与此同时我国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数量巨大,充足的地下材料为还原纸上材料所构造的历史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二重证据法是最为核心的指导方法。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离不开二重证据法的有效发挥,其前提是对两重证据的仔细择取与合理使用。
二重证据法在历史时期证据的择取上,根据材料是否出土区分为纸上之材料证据和地下之材料证据两种搜索路线,两者对证据的内涵各有明确的指向。纸上之材料为第一重证据,其包括一切可资参考的文献资料、传世实物及图像资料和对传统风俗习惯等的调查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即是传世文献;传世实物及图像资料涵盖了留存至今的不可移动文物和传世绘画作品;对传统风俗习惯等的调查资料相当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经过调查后形成的系统资料。地下之材料为第二重证据,其包括一切出土的文献资料、一切出土实物及图像资料。两重证据的内涵指向不同决定其本质的不同:纸上之材料是“是经过人们的意识处理过的历史信息”[10],地下之材料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本来的史料”[11]。前者因被处理过而非历史的完全真实反映,后者以瞬时形式留存当时的历史却仍待文本的阐释,正是本质的明确区分与互补使两者能够实现有机结合。
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使用二重证据法时,首先需要对两重证据的性质进行时间性质上的审视。历史时期的纸上材料相对完备且具有系统,是一种流传有序的材料,属于历时性证据;地下材料相对分散,是对特定时期历史的保留,属于瞬时性证据。由此观之,纸上材料应起到搭建历史框架的作用,地下材料作为框架中的各个点,以其真伪的不同对历史框架的构建起到一定的作用,两者相互配合以达到建立最接近历史真相的合理历史框架,进而共同丰富历史事实的内涵。
以纸上材料搭建的历史框架为基础,二重证据法在对历史时期证据的使用上可根据两种证据各自的真伪性区分为四条使用路径:其一是纸上材料为真而地下材料亦真,对证据的使用则是起到证实的作用;其二是纸上材料为伪或纸上材料有缺佚而地下材料为真,对证据的使用则是起到证伪和补正的作用;其三纸上材料为真而地下材料为伪,此时对于地下证据不予取用;其四是纸上材料为伪而地下材料亦伪,面对这种情况需要将两种证据予以存疑备参,留待更为可信的证据出现。四条路径均针对历史框架而言,框架内的历史事实需要两种材料都具备真实性的情况下进行丰富。针对两种证据真伪的判断,纸上材料需要依赖历史文献学与训诂学的成果,地下材料需要依靠地层学与类型学来验证。
归结而言,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追求的是最大程度还原历史时期的面貌,考古研究拥有的地下材料是二重证据法的关键一环,其共同决定着二重证据法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如何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运用好二重证据法,一是对两重证据广泛收集与仔细择取,二是对择取的两重证据选择合适的使用路径,贯穿取用过程之中的则是秉持科学客观的态度。
三、《白沙宋墓》中二重证据法的实践
二重证据法作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其可行性最终需要在实践层面予以检验。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以宿白先生最具代表性,他开创了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典范,将二重证据法融汇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中。宿白先生一生著作丰硕,以《白沙宋墓》颇具典型,其为历史时期考古发掘报告与二重证据法结合树立了标杆,因此本节将借以此书管窥二重证据法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实践。
《白沙宋墓》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的经典之作,其在无先例可循的前提下明确了历史时期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例与标准,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开创了典范。该书“全面报道了白沙宋墓的发掘资料,书中所描述分析的三座宋代雕砖壁画墓为了解宋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12]。全书的重心在于对各墓构造、各墓装饰及各墓随葬品的描述,其中以墓的构造和墓的装饰论述最为精彩,也即二重证据法的发挥最为淋漓尽致之处,其具体的取用过程介绍如下:
《白沙宋墓》对证据的择取分两重,第一重证据是地下材料,包括该墓的原始材料和其他地区可资参考的地下材料,其中该墓的原始材料是报告正文部分对三座墓葬的客观描述;其他地区可资参考的地下材料出现于注释之中,是第一重证据的旁证,如书中的注释[31]、[39]、[40]、[51]、[74]等[13],均是以其他地区的出土材料对该墓材料所要解决的问题起辅助与强化证据的作用。第二重证据是纸上材料,包括纸本历史文献与对现存古建筑的调查材料等,集中罗列于该书的注释部分,体现出与第一重证据的明确区分。可资借鉴的是,该书对第二重证据展现出清晰的取向:墓的构造聚焦于宋代李明仲所著的《营造法式》;陵墓装饰所见名物兼用正史与文人笔记进行考证。对材料的准确引证是宿白先生治学功力的体现,同时亦是对使用者是否熟悉材料的考验。
《白沙宋墓》在证据的使用方面同样斟酌得当,其使用路径可以通过前节归纳的四条路径进行观察。两重证据皆为真的情况起到证实作用,例如注释[34]确证《营造法式》中门簪后尾四枚的说法[14]、注释[42]和[244]对“骨朵”一物进行详细考证[15];纸上材料为假或缺失而地下材料为真的情况起到补正作用,例如注释[39]中提及甬道壁画马的风俗不见诸典籍文献,但在地下材料屡屡出现,可以确定其应是当时的风尚[16];纸上材料为真而地下材料为假的情况虽应弃用地下材料,宿白先生却对地下材料进行了反思,例如注释[24]中明确指出“此细部尺寸和彼此的比例,大多与《营造法式》不合......凡此类皆因受砖本身限制所致”[17];两重证据皆存疑的情况则应尽数留备,例如注释[33]将关于“穴”的各类证据一一摆出[18],以待日后实证检验。《白沙宋墓》的最后一部分“与三墓有关的几个问题”是对二重证据法的综合使用,两重证据的相互结合与印证还原了墓葬的年代与相互关系以及墓主人的身份,展示了宋代建筑风格和居室陈设的变迁。就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角度而言,该书对各种情况考虑充分,结论处综合各类证据加以升华,足以称之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典范。
从《白沙宋墓》一书回到宿白先生的治学生涯来看,他在北大讲授汉唐宋元考古课程时就明确表明二重证据法使用对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秦汉以后的考古资料虽然也发现很多,可是文献记录却日益完备。因此研究秦汉以后的历史,就需要文献与考古发现并重了......所以我们说,文献记录越来越多的秦汉以后部分的中国考古学,要比研究秦汉以前考古学部分,更需要注意文献史料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19]《白沙宋墓》恰恰是这番言论最为真实的写照,其将二重证据法在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的取用操作落于实践,使得二重证据法的学理意义通过此书以别样面貌完美呈现。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3.
[2]王国维,罗振玉编校.明堂庙寝通考,载《雪堂丛刻:第三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97-299.
[3](日)西山尚志.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J].文史哲,2016(04):45-52.
[4]刘毅.“二重证据法”新论[J].南方文物,1997(03):104-109.
[5]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3(02):151-162.
[6]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J].历史研究,2012(04):116-133.
[7]饶宗颐.谈三重证据法,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16-17.
[8]杨向奎.历史考据学的三重证[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05):77-78.
[9]杨骊,叶舒宪编著.四重证据法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10]宁可.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J].文史哲,2011(06):68-76.
[11]宁可.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J].文史哲,2011(06):68-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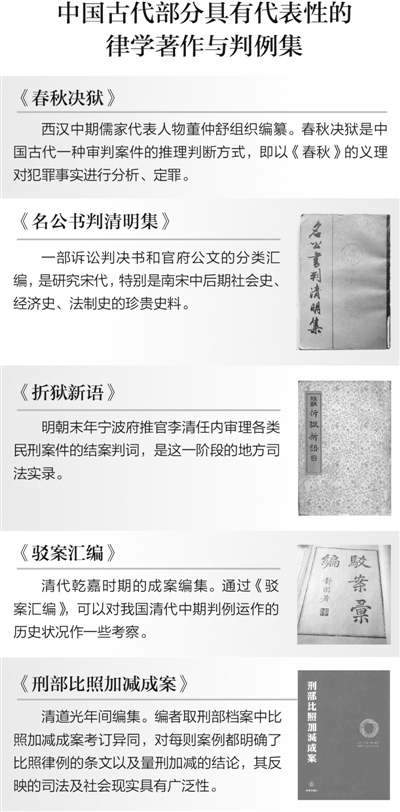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