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铸就统一体:考古与文物所见西藏和中原关系资料研究》读后
张云
由霍巍教授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中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整理与研究”,其最终成果《历史铸就统一体:考古与文物所见西藏和中原关系资料研究》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三部分组成,即基础资料部分5册;综合研究部分3册;专题研究部分1册。这是近几年来西藏文物和历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可喜可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霍巍教授主持完成的《历史铸就统一体:考古与文物所见西藏和中原关系资料研究》,就是藏学研究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在此先对该套丛书做一整体介绍。
基础资料部分按时代、时间和类别为序,搜集学术界业已公布的各类考古成果和文物资料,补充以课题组新发现和拍摄的材料,既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也为学术界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更是广大读者了解西藏与中原关系史的好素材。
专题研究部分系该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论文汇集,其中《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表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研究评述》一文,虽然是评述,却起到统领全书主旨,表明立意的作用。霍巍教授的《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一文,通过对西藏西部早期墓葬的形制、埋葬习俗、动物殉葬、器物随葬等方面内容的分析,认为最迟在公元1千纪前后,在该地区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这个中心已经具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来自各地的人群汇聚于中心之内,不仅带来和保持着自身的传统文化特点,而且也逐渐开始形成区域性的若干共同性文明标志,积石冢、石丘墓、石室墓、黄金面具、箱式木棺、青铜器、丝绸和茶叶等各项因素的出现,显示出跨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吐蕃“告身制度”的考古学新印证》一文,提出告身制度最直接的来源应当是唐朝的官服制度,并与虎皮肩章、帽子、衣甲等共存,且受到来自中亚和北方“胡服”的影响。《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一文,用考古发掘成果和相关实物资料表明,在公元前1千纪晚期至公元1千纪早期,西喜马拉雅山地与塔里木盆地南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汉文化也经由丝绸之路南道进入西藏西部边缘地带。说明来自不同方向的外部文化因素在该地区汇聚生成,又继续扩散的状况。认为正是基于早期金属时代的物质文明积累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才使得11世纪西藏佛教的复兴自西藏西部发轫成为可能。其他文章也不同程度地就文物中所包含的历史内涵进行了探析阐释,不乏创新观点。
综合研究部分是该书的核心或者主干成果,这一部分内容既是对基础资料的发掘利用,也吸纳了专题研究部分的相关成果,这里择其要者,谈以下几个方面的感受。
第一,用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史实。
作者在书中指出,大量考古学证据表明,从西藏史前时代开始,西藏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便已经十分密切,而有别于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体系。西藏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明显与东亚地区——尤其是我国中原史前文化体系最为接近,而与同时期的中亚、南亚史前文化体系相去较远。至于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共性,书中简明而较为系统地从居住式样、陶器形制与纹饰、磨制石器、骨器、玉器、海贝,以及粟的栽培等几个方面,梳理了两者的内在联系。
关于吐蕃时期的文化,作者指出了晚期藏文史书一味将吐蕃文化纳入印度佛教文化圈存在的误区,进一步指出“如果从更为宏大的视野来考察吐蕃文化的面貌,其中更多的因素是受到来自东方汉文化圈的影响,而不是南方的印度文化圈”,用以证明的文物材料十分丰富,涉及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儒家思想,吐蕃佛教中的禅宗影响,来自中原的历算、阴阳五行、八卦、丝绸服饰、饮茶习俗等。关于吐蕃王陵借鉴唐代帝陵制度,书中列举了“依山为陵”的建陵规划设计,模仿“方上之制”的封土形制,地面竖立石碑、石狮等标志物,以及围绕封土的四方形陵垣等,说明了吐蕃借鉴唐朝制度的客观事实,并清楚地指出:“吐蕃王朝的陵墓制度在多方面受到唐陵制度的影响,应当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在考古文物的背后,隐藏着当时唐蕃交流的宏大历史背景。首先,吐蕃王朝君主主要实行土葬制度,这与当时天竺(印度)主要流行火葬、野葬的习俗以及中亚波斯、伊朗高原等地的葬俗相去甚远,而与汉地唐朝葬制最为接近。”厘清了唐朝与吐蕃之间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也就雄辩地得出了西藏文化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客观结论。
第二,用信实可靠的文物资料清晰地揭示了元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
从1247年元太宗窝阔台次子阔端与代表西藏地方的萨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会谈开始,西藏地方纳入大蒙古国暨元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元朝在朝廷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理吐蕃地方事务,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机构、任免官员、清查人户、征收赋税、设立驿站、驻扎军队、颁布法律、审判案件,实施了充分有效的行政管辖。八思巴字皇帝圣旨、藏文帝师法旨、册封僧俗官员的印章、使者使用驿站的令牌,以及1959年在西藏自治区萨迦寺内发现的至元通行宝钞等,都从不同方面证明了中央政府管辖西藏的历史事实。明代继承元代在西藏实施的各项措施,并顺应政治格局和西藏地方政教势力的变化,采取了一些新的完善措施。该书比较好地利用相关文物资料,对明朝初年对元朝西藏职官和行政机构承袭与调整情况,包括万户与万户府、元帅与元帅府、西藏宣慰司,以及地方官员的承袭制度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对相关涉藏管理机构,朝廷封授西藏地方宗教首领的僧职名号等,结合文物资料予以清晰交代,最后还通过西藏地方寺庙供奉“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供奉明朝皇帝御容像等,考察了西藏地方对明朝中央的政治认同。清朝对西藏除了行政管理、军事保障和法规制度约束之外,进一步采取的经济、商贸与货币管理措施,这些都有大量的文物资料提供例证,很有说服力。
第三,用系统而完整的文物链条勾画出自古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
该书基础资料一脉相承、上下贯通,综合研究系统、完整,全面呈现了西藏地方与中原,藏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密切交流,民族间联系不断的历史场景,描绘了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西藏实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地穴房屋、打制石器、彩陶、青铜器与中原的内在联系,到大小昭寺、布达拉宫、萨迦寺、夏鲁寺对中原建筑风格的吸收利用;从阿里出土的汉字王侯纹饰织锦、茶叶茶具到逐渐繁荣起来的吐蕃丝绸之路,延绵千年的茶马古道;从金属冶炼、天文历算、医疗医技传入西藏,到音乐舞蹈、唐卡绘画、风俗习惯;从政治制度借鉴到儒家思想的吸收,西藏与中原地区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始终未断,而且持续由表及里,更深更实。《明会典》记载了明代乌思藏地方向明朝进贡的方物,包括画佛、铜佛、铜塔、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铁力麻、各色氆氇、珊瑚、犀角、左髻、毛缨、酥油、明盔、明甲、刀、剑等。明朝皇帝赏赐乌思藏地方首领的物品也有特色,主要包括茶、服饰、丝绸、瓷器、金银、玉石、鎏金佛像、佛塔、经书、唐卡、法器等。书中梳理了朝廷赏赐物品在西藏存在和使用的情况,包括大昭寺、楚布寺、萨迦寺、纳塘寺、色拉寺、甘丹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丹萨替寺、泽当寺、白居寺、噶玛寺、昌珠寺、乃宁曲德寺、达隆寺等收藏的明朝赏赐物品。虽然还远算不上完备,却也足以说明问题。该书综合研究部分在这一方面用力最多,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对于说明相关历史问题,效果十分显著。总体而言,该书用丰富的文物资料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深刻地说明了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巨大动力这一深刻道理。
第四,用考古实物和文物资料讲好中国历史文化故事,讲好西藏历史故事,做好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工作成效突出。
自唐朝文成公主携带汉文经典、医学书籍、乐器工艺等到吐蕃之后,中原地区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与此同时,吐蕃赠送唐朝的珍贵物品如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的金鹅,上面塑铸有狮子、象、驼、马等动物形象的“金城”,以及金瓮、金颇罗、金盘、胡瓶和土产方物等,相继送达中原。历朝历代相沿不断,成为制度,不同时代虽然有不同的代表性物品,但在表明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关系,增强西藏与中原联系方面则一脉相承。这些物品既是珍贵文物,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牵动宏大历史、触动人心的故事。该书十分重视对文物细部的准确考察与描述,重视还原文物中所蕴含的历史场景,以及所承载的时代内涵。书中以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故事性强,容易理解,也容易受到感染,通过轻松阅读获得了对复杂历史的清晰认识和深刻了解,这一做法无疑是成功的,相信也能获得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
该书如再增加民国部分的文物资料和综合研究内容,体例会更加完整。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书中自然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问题,比如在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前,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族群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一样经历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直到吐蕃王朝建立后,文明进程才开始加速,进入封建社会。这就引发对吐蕃王朝究竟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问题讨论,相应也会引发西藏封建农奴制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了多少年的问题。还有一些概念的使用,如采用吐蕃的方位概念,称中原地区为东方,又以吐蕃为基准称吐蕃在东方的“中国文化圈”和南方的印度文化圈之间的选择问题;在使用汉藏关系,西藏与中原关系中的概念的界定问题,扩大文物涉及范围。
与此同时,书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些地方对前人研究成果吸收不够充分,如对答失蛮入藏置驿年代的叙述。有些地方还存在需要慎重对待学界成说的问题,如认为“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应该是从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的,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就是忽必烈及其帝师八思巴”,把大蒙古国与元朝分开的做法是否妥当,还需认真研究,把西藏纳入元朝行政版图的时间从1271年改国号算起,更要从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从大蒙古国史与元朝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来理解,不宜轻易给出断论。
此外,近几年西藏考古又有新的重大发现,希望重版时能得以吸收,目前西藏还有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深藏闺中,也希望有朝一日有关方面能将其有序公之于众,以助力中国藏学研究,也能进一步丰富本书基础资料部分的内容。最后,本书还提醒我们,从考古和文物资料视角系统阐述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多学科角度系统阐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张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31号,邮编100101)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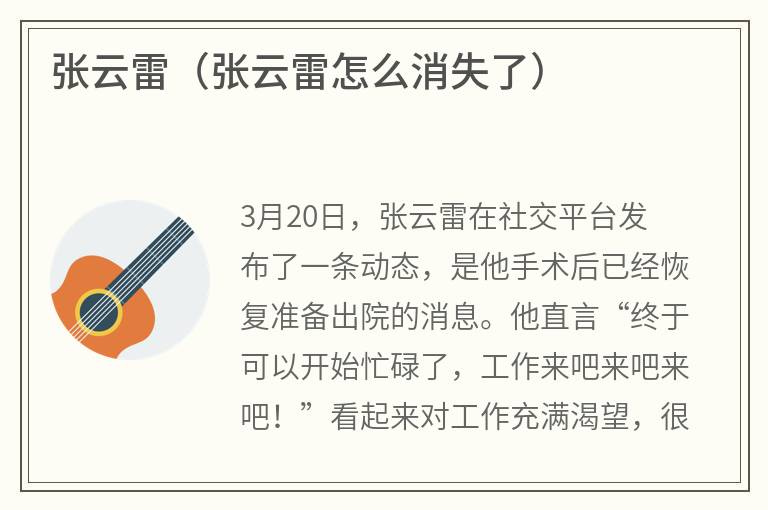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