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范英军,天津市第四十一中学教师。
赵亚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应转向为
中学历史教育研究(中)
二、中学历史教学的专业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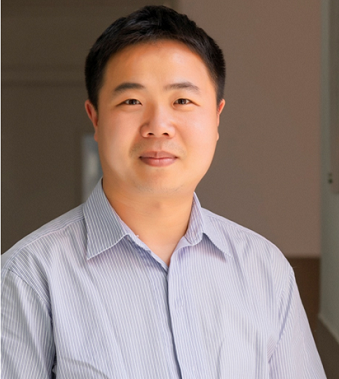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中学历史教学是一个专业,需要专业研究。但是,如果这个专业不是指历史学,那是指教育学吗?好像也不是吧!

赵:确切地说,不是指“学术的”或“纯粹的”历史学。如果一般的历史学或单指历史学的教育性,那是又当别论了。为了清楚起见,我说是“历史教育学”,或视为“历史学—历史教育学”。这里的“学”,指作为专业研究的历史教育,教学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所谓“历史学取向的历史教育研究”和“教育学取向的历史教育研究”的“取向”,不是定性的意思,而是所指其定位,即研究意义上的特征。因此,不能截然分为“历史学的”研究或“教育学的”研究,因为“取向”本身意在更侧重于解决哪些问题。从学科建设角度说,它是交叉学科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专业意识、专业态度或专业精神。
回到你开始提的问题:(1)“教科书的观点与某些学术权威的观点不同,教师如何做取舍?”答:“因为教科书体现国家意志,故需服从教科书观点。”(2)“教科书的观点落后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教师该如何处理?”答:“‘最新研究成果’要被公认、认定后方可进入教科书,并作为基本知识必须具有稳定性。”(3)“历史教师是不是应该像培养历史学家那样,向中学生传授历史学技能?”答:“中学历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主要任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知识和技能需服务于教学任务和目标。”
这样的回答体现历史教学的专业性吗?或换个视角说,你满意这样的回答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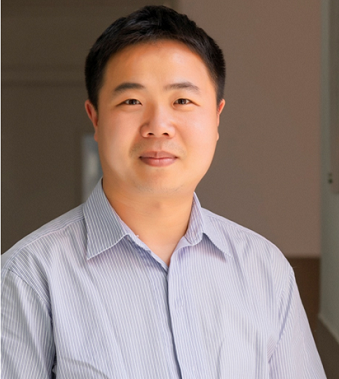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它有助于我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案,但教学似乎也变得简单了。具体来说,我想重构教科书的叙述逻辑,可以吗?又该如何重构?我需补充史料,补充到什么程度?“教教材”就是照本宣科,“用教材”就是解读教科书吗?总之,还是不能解决如何“上好历史课”的问题。

赵:是啊!复制以往的教学法(法则),只是说些隔靴搔痒的话,这样的回答并不能解决专业问题。目前的教学论又何尝不是这类简单的翻牌式的教学法呢!
再如,从专业角度考虑重构教科书的空间问题,至少可看到两个方面:(1)目前的空间甚小!“用教材教”不过是个专业噱头,实践环境和条件以及教师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2)两种取向的历史教育(研究)会给出较大的重构空间,但前提是必须真实地——不能停留在概念上,必须在观念和行为共同作用下——改变教学观念和方法。理想地说,每位历史教师都应该具有重构教科书的能力,因为学生对教科书内容的理解与教学目标有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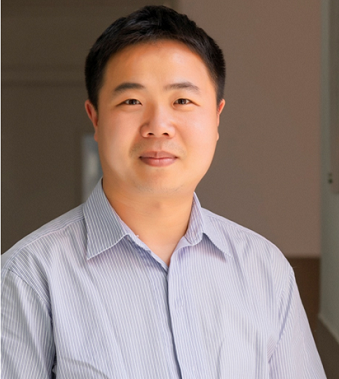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您的意思是,只要教师根据学情进行教学设计就是在重构教科书了,不一定非要打破教科书叙述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的空间因人而异,也不必太拘泥形式。

赵:是的。教师如果了解历史学的叙事特点,包括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相关理论,就会做专业性的处理。把教科书当成一种叙事文本来看,分析给定的史事逻辑,这是理论问题!从教学方面看,表现为教师能否从专业上把握(读懂)教科书逻辑。重构即再组织,不一定都是结构性重构,更多情况下是理解性重构。所以我说,教学存在着历史事实本体、教科书叙事、教师解读、学生理解等四种逻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是专业问题!至于每位教师的“重构空间有多大”,脱离了学习环境和条件、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教学内容便没有任何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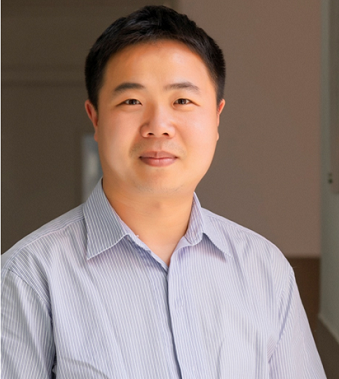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您一再强调不赞成繁琐的、刻意结构化的教学设计,是因为教学空间非常有限吗?

赵:不是指“教学空间”问题,而是说过于“严整的结构”实际伤害了对事实的探究,挤占了学生思维空间。当下的不少“教学结构”甚至违背事实逻辑,完全是教师在做历史演绎。教学结构必须简洁,否则“专业的教学”没有空间。
再说补充史料的问题。其一,教科书是根据历史学研究成果写出的教学用书,其书写的史事都有史料支撑,即它是历史书——也是一种历史著述——当然可以“照本宣科”;其二,“教学用书”与学术著作或一般的历史读物有着不同的编写逻辑,但仍不能将其直接对应学生的学习逻辑和客观历史逻辑,因此“照本宣科”肯定不属于优质教学;其三,一套教科书无法适用于各种水平和要求的教学,作为教学“文本”,其本质是学习资源,如何使其达到深度学习的目标,发挥最佳的学习指导效果,取决于教师的教学逻辑与其他三个逻辑的契合程度。概言之,是否应该补充史料以及补充到何种程度,这个专业性问题需要针对具体的教学情况才能做有效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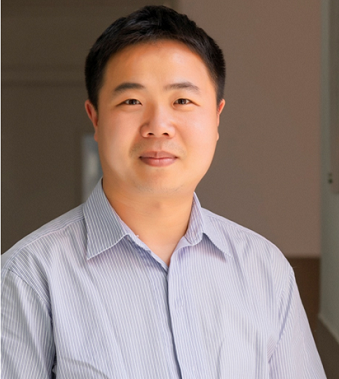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我看到一些历史教学类的专业书提供了某些方法和策略,还是挺有启发性的。另外,某些学者编的材料性专著为中学教师提供资源,我也觉得不错。

赵:恕我直言,专业人士不读这些书。最直截了当的理由,教学中的材料除基本史料(或更严格的原始材料)外,其他材料非常个性化,必须根据学情、探究目标和活动过程等多种因素选择和运用材料。而掌握基本史料属于教师的专业基础,在本科阶段就打好基础了。更何况这类专著提供的材料并不是基本史料。至于“学术动态”之类的东西,同样带有过强的个人色彩。作为历史教师若热衷于读“给定思路和材料”一类著作,说明你的教学很不成熟、专业性严重不足。
另外,我在国外也曾试图寻找这类“教学工具书”,也询问过为什么专家不写这类书的理由。他们强调三点:(1)教师是专业人士,提供怎样的专业支持需谨慎——个人的业务水平不断进步,自我要求不断提升;(2)教学是创造性活动,应避免教学同一化——任何参考都是有限的,而且越在意教学的专业就越重视养成个性;(3)如何使用史料与教师的教学意图(教学设计)密切相关,脱离了具体的教学情境、过程和方法的“史料”就没有价值——教学,包括史料教学都是因人而异的(考虑环境、条件、个性等多种因素)。我国的情况或许有特殊之处,但我还是质疑:“专家”和一线教师本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什么一下子冒出来领跑者,而且理直气壮地编写“指导书”?历史教学是一门学问,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可是一经课程改革似乎很多问题已迎刃而解(这些书的出发点),中学历史教学如此简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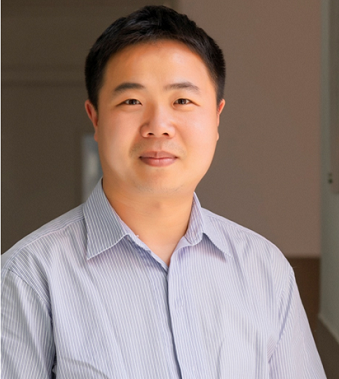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我也有直感,在教科书之外不宜过多引用历史资料。一是一节课的教学内容已经很多,教学时间不允许;二是征引的资料很多并无必要,如引用大学教科书、某些畅销书和历史学家的评语。从历史学研究方法看,材料不具备探究语境和方法的话,也没有专业上的学习价值。

赵:是啊!我做过若干课堂实录分析,发现中学历史教学使用材料的问题主要是臆断太多。传统的历史教学,“补充材料”是镶嵌在自己的历史陈述中的,特点是讲述完整和流畅。一些老师也使用补充材料,但有个特点很鲜明:材料学生一看就懂,不用另加解读;稍有难度的材料,一定让学生全部理解后再往下讲课,材料和教科书是一体的。现在的历史教学,“补充材料”一则、二则……排下来,粗浅(展示)且应接不暇(过多),美其名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考,其实都在服务教师的历史解释。说到底,材料没有起到专业性指导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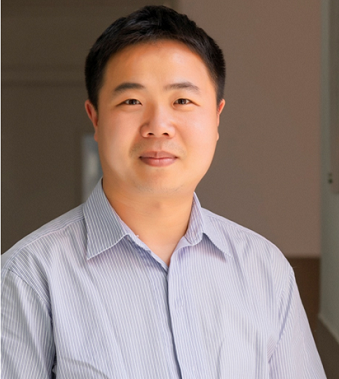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我再提一个普遍的专业性问题。一些教师认为,应坚持讲解的重要性。你不讲,学生如何能懂呢?教师的作用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离开了讲,还能做什么?从我个人的教学经验和观察来看,日常的历史教学几乎都在讲,似乎只有“做课”时是不讲的。但是“做课”与日常上课是两回事儿。您看,应该如何看待“讲授”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看待讲解式的教学活动?

赵:我可以反问道:自然学科的教学不“讲解”吗?语文课、政治课不“讲解”吗?为什么历史教学的“讲解”如此特殊?引申说,自然科学的教学不做“解释”吗?凭什么说“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这一论断能迁移到其他学科吗?你怎么证明“不讲,学生如何能懂吗”这句话呢?比如我让学生先看书,他们“懂”了的内容,还有必要讲吗?另外,什么叫“懂”了?“能考试”就“懂”了吗?再较真地问,教师都能读懂教科书吗?能“懂”何必要反复培训呢?如果教科书学生完全看不懂,是教科书编者的问题还是教师的问题?不错,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么,讲授是“布道”吗?传的是什么“道”啊?只有讲授才是“授业”吗?“授业”与“传道”又是什么关系?“惑”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解得?“做课”的确和日常上课是两回事儿,又是什么原因使二者割裂的呢?“讲授”和“讲解”都是传统教法,“讲解法”有什么优势吗?仅这些问题是不是够你应付的?
其实,问题不在我们提出了多少问题,而是要从专业方面追问“这都是些什么问题”“怎样区分哪些是根本问题、哪些是一般问题”。
现在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看问题”的习惯,就是动辄用“实际不实际”搪塞真问题!你写了一本“应景”和“实用”的书,捧的人就多。然而,“应景”无外是“教学需要什么给什么”;“实用”是因为它剪裁了不少教学案例。真的有用吗?比如“教历史就是讲故事”怎样成了硬道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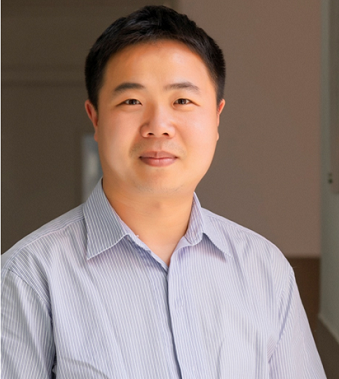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我也不知道,经验告诉我似乎“讲”是变通的方法。

赵:那我们借助其他经验追问:(1)对于讲故事,教师是否堪比评书艺人或演说家?(2)故事何以能吸引听众?(3)它是如何被加工出来的(情节、描述、结构、冲突)?(4)事实或事件是否都能对应出一个前因后果井然有序的故事?(5)是史料串联成了故事(探究),还是故事成就了史料(讲解或解释)?如果是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学,因为故事是确定的、必须掌握的甚至是绝对的认知对象,即遵循故事先设原则,当然讲述、讲解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史料不过是辅助手段,并不具有“拼(史料仅反映事实的碎片)镜(基于史料将碎片拼成可辨、可识的事实)”的功能。
我理解,“学科核心素养时代”就是把单一性的“讲历史”的历史教学提升为整体性的“做历史”的历史教育的时代。它一方面要求历史教育教学必须成为专业(仅针对专业训练学科思维和认识),另一方面应时刻牢记不能再使“教育从教学中抽离出来”,(雅斯贝尔《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如果历史教学仅仅是课堂讲授活动,无论补充多少史料、多么重视历史叙述,它也难以完成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任务,因为在专业上它不具备充分的教育性。所以,讲授、讲述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没有唯一性;讲解同样有其必要性,但也不具有优先性。问题还在于怎样讲、讲到何种程度,这首先是实践中的理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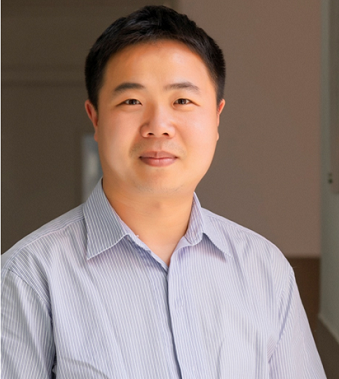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您把历史教育学叫做“实践性理论”,也是用心良苦!现实对一线教师影响最大的是一波又一波的观念冲击,既应接不暇又难以理解,比如“大概念教学”,理论上来说是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历史理解能力,从而达成深度学习的目的。可是何谓大概念教学,又真是令人费解?

赵:完全理解一线教师的苦衷!让我说,这依然反映了历史教育专业性弱和不研究基础理论的后果。前面说了,历史课程改革仅会做填空题不行。“大概念教学”和“深度学习”都是教育学范畴的概念,我们缺乏基础性研究;到了“非用不可”(作为课改理念放入课程标准里)的时候,就只能硬贴上历史教学内容进行解读。为什么非要有个“大概念教学”呢?或进而问,历史教学真的存在“大概念”吗?
我研究“社会科教育”二十余年,知道其课程和教学理论都讲“核心概念”。“核心概念”针对单元设计而言,其下是“子概念”,一节课或一个活动一般解决一到两个子概念。简单地说,“核心概念”关乎课程构造以及教学性质和形态等重大理论问题。比如“知识传播性质”的社会科、“社会(问题)理解性质”的社会科、“批判性思考性质”的社会科,其“核心概念”所对应的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差异甚大。具体到教学实践,一个“核心概念”究竟包含几个“子概念”,既受制于知识结构也必须考虑学生应获得的学习成就,即“核心概念”和“知识结构”是在“课程设计”环节确定的东西。从操作性看,单元凝聚“核心概念”的主旨或中心思想;课是“核心概念”的载体,它通过若干子概念澄明“核心概念”的意涵。还有一个相关研究,即主题和专题及其关系。(赵亚夫《学会行动:社会科课程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目前,课程、教材、教学在这个问题上是脱节的,仅靠一线教师在教学中解决“大概念教学”问题,我认为很不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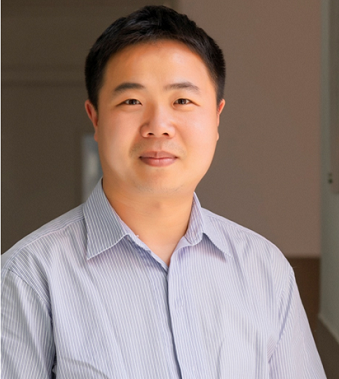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原来如此。我把您的观点概括一下,一是必须承认中学历史教育的专业性,毕竟历史教育是“以史育人”,具有较高的道德要求;二是中学历史教育必须研究自身的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并不能直接对应大学历史教学的专业性;三是中学历史教学的专业性应凸显历史教育的专业特质,或说在历史教育中研究历史教学。

赵:谢谢你的概括。我再强调一点,没有理论研究不行。比如在做阅读指导时,何谓“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怎样理解“所有的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并在其中渗透“即我必须接受某些反对我自己的东西,即使没有任何其他人要求我这样做”的观点,以及通过对话达成“要求每个人在表达中向他人敞开自身”,进而形成“相互理解”和揭示事实和文本意义的目标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显然,要建立历史学取向的中学历史教育,理论必须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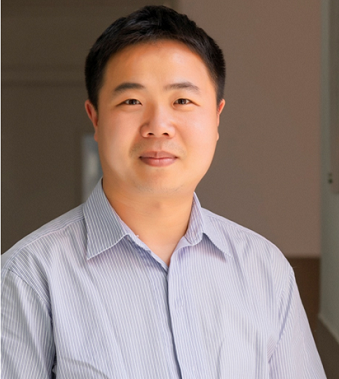
范:建立这样的理论基础很难啊!既然专业性要求我们针对历史学提升教学研究的专业性,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关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呢?

赵:别的不说了,仅结合基础教育发展趋势以及历史教育学建设方面讲我的两点认识:中学历史学科的专业性应着眼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学”的专业性;中学历史教学的专业性多么“浅显”不是问题,但是它若致使历史教学庸俗化就一定出了大问题。
本文原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21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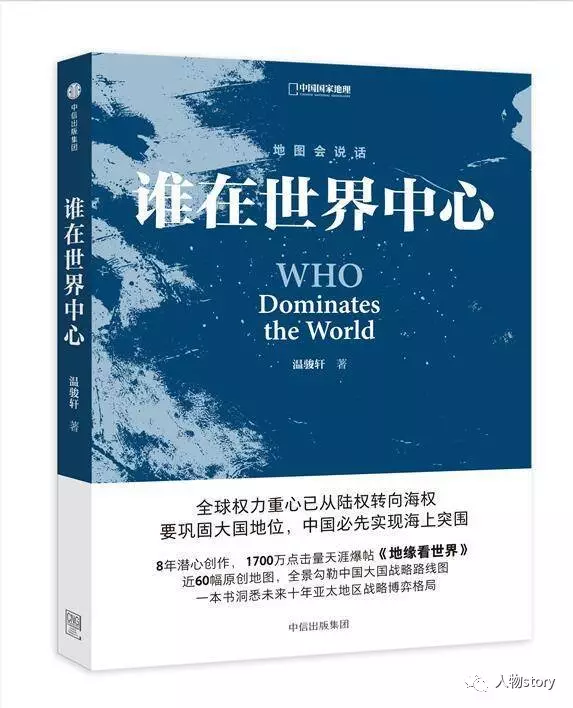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