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是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90岁生日。是日晚间,他来到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畅叙“我与清史研究”。尽管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老人家安步当车,依旧精神矍铄,笑言晚餐时还吃了两碗寿面。

“我与清史研究”讲座现场
作为历史学家,阎崇年从事史学研究已逾一个甲子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学术研究中,清史始终是他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领域。清史研究的魅力何在?他在清史研究的关注点与治学方法是什么?清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又是什么?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大众出版相结合?阎崇年与宋志军在对谈中围绕为人与治学、研究与出版的主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分享。
对谈正式开始前,阎崇年还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读书能使人康寿,不仅增长智慧,还增加健康的寿龄。“我最近在读三本书,这三本书都让我写序言,我的习惯是必须先看书,再写序言,否则就无的放矢,心里没数。这三本书分别是《北京的胡同》、《中国古籍修复技艺》,以及今年是我登上央视‘百家讲坛’二十周年,当时先讲的是《清十二帝疑案》,后来出书书名就叫做《正说清朝十二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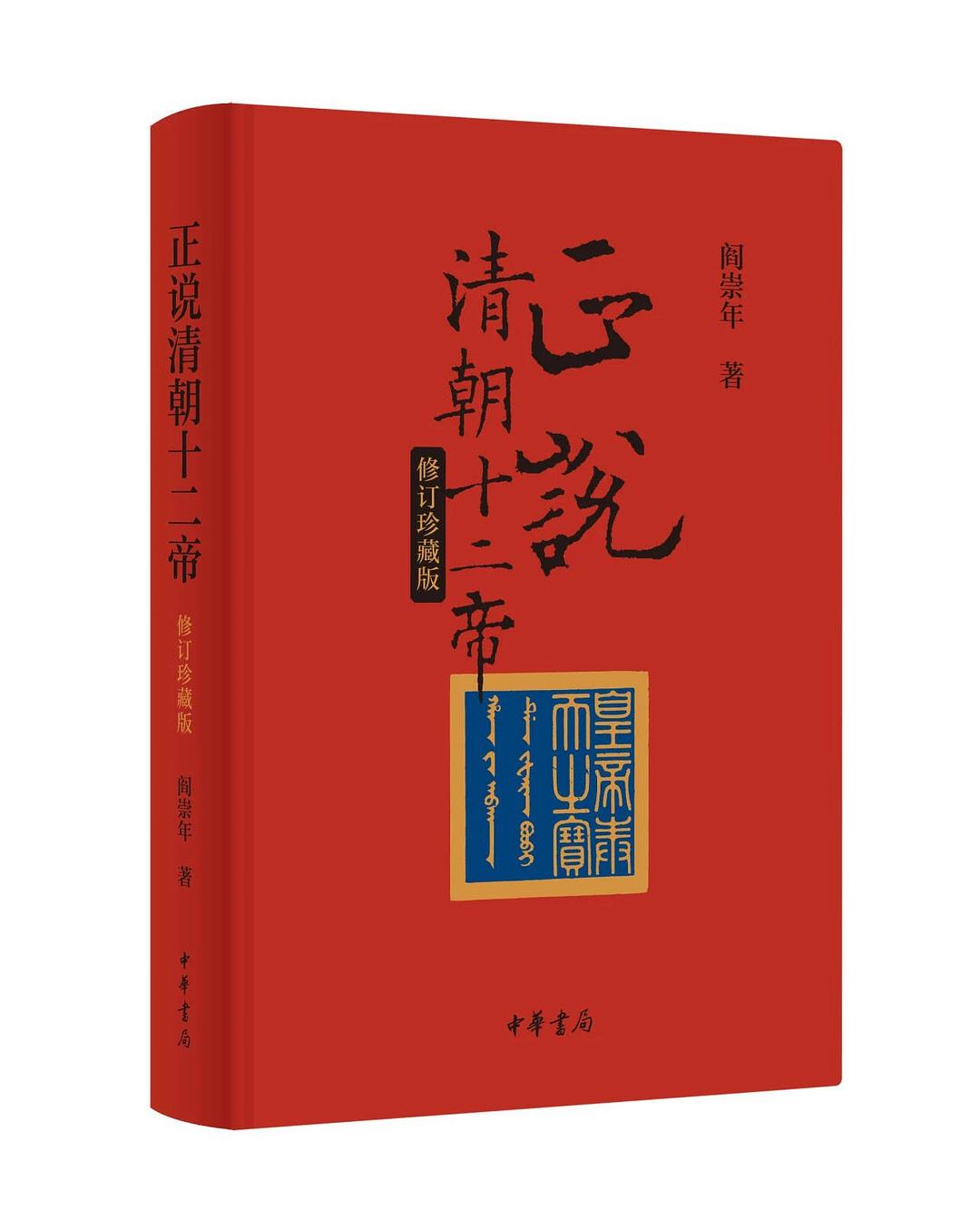
《正说清朝十二帝》
“《正说清朝十二帝》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二十年来出版了十八种不同的版本,印了估计有一百万册,到现在还在畅销。这次是出版二十年了,准备出修订珍藏版。编辑特别用心,一个字一个字重新校正,下了很大功夫,可以说是精益求精。这本书已经印好出版了,我重头读了一遍,写下序言。”阎崇年说。
写《努尔哈赤传》,“望尽天涯路”
对谈开场,阎崇年介绍说,自己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继续研究历史课题时,先是选择了先秦史。一次,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主任杨向奎先生指点,后者鼓励他找杂志发表。

阎崇年
“现在年轻的朋友发表论文很困难,当时更难,因为就两三个杂志。过了一个礼拜,杨先生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在北京,干吗研究先秦史?先秦史是人家西安的事。先秦的考古发掘在西安,在北京看发掘报告是二手材料,不是第一手。你应该研究清史,因为你在北京,明清的首都在北京,明清宫廷档案在北京,重要的古典文献都在北京。而且清史当时研究人很少,杨先生说清史是一块处女地,随便丢个种子就有收获,这话对我刺激太大了。”阎崇年说,学术研究要慎始善终,“选定一个方向最重要,那是1963年,从那时到现在六十年了,我一直在研究清史。”
清史从努尔哈赤建国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历296年,可以说是卷帙浩繁。“我最初找的切口是研究康熙,看历史资料如坠入雾海,没边没影、不前不后。迷茫中,我得到了北师大历史系系主任白寿彝先生的指点,他说树有根、水有源,研究清史一定从它的‘根’和‘源’上入手。清朝历史的‘根’和‘源’在什么地方?当然在关外,所谓它的龙兴之地。如此我就从头开始做,从清朝的开国史开始研究。这么一做就是六十年,常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这条路走对了。”
1983年,阎崇年第一部学术著作《努尔哈赤传》正式出版,其间甘苦备尝。他介绍说为了研究努尔哈赤,他从1963年到1973年先是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我完全是看原始资料,用倒查的方法,从元末明初,他们的老祖宗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开始捋,看了明朝的实录、清朝实录,包括朝鲜李朝的实录,用了十年时间写成论文。原本论文想在社科院权威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但当时还在‘文革’后期,编辑让我在文末再加一段研究努尔哈赤对反修的意义。一位老师劝我,加这样的一段文章就废了,不如把文章搁抽屉里,将来有机会再说。”
阎崇年回忆说,“文革”结束后自己研究努尔哈赤的文章才得以在大学学报上发表。“我把文章给白寿彝先生看,他告诉我当时还没有人写《努尔哈赤传》出书,我又做了整理和补充,才在1983年把这本书出出来。从研究努尔哈赤到出书,前后整整花了二十年。我敢说一句话,跟努尔哈赤有关的各种资料,汉文的、满文的,我都见过,也体会到了王国维所谓做学问的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以说每研究一个问题,要望尽一次路,如此不断地望尽天涯路,不断地前进。”

《阎崇年史学论集(清史卷、燕史卷、满学卷)》
历史是人文科学,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阎崇年看来研究历史最困难的,是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举个例子,北京昌平区有个‘平西府’,相传是吴三桂的府邸。在当地的村子里也确实有座铜井,井盖还铸有龙纹。老北京有句话,‘二环以外无王府。’明朝的藩王都在外地,清朝的王爷都在北京,现在的二环以内,这是定例。为什么五环外的昌平出了个王府?我翻了能翻到的许多汉文资料,并没有相关记载。”
阎崇年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查满文资料。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康熙满文朱批奏折》,记载了一则奏报康熙帝的御批奏折,详细记录了行宫城池、房屋、游廊等数量,正好与昌平“平西府”一带发现的城墙和护城河等遗址相吻合。此后,他又和其他专家一起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奏折中,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关于兴建行宫王府的开工奏折,地点正是前述“平西府”所在地。结合其他史料,阎崇年论断,“平西府”其实与吴三桂无关,而是康熙兴建的郑家庄行宫、王府。从开始考证到最后公布结果,总计花费了一年多时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阎崇年看来历史是人文科学,更需要多了解实际,为此他曾在80岁时登上海拔3800米的布达拉宫。“从2004年到现在,这二十年间,我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走路,这个收获是在书斋里学不到的。我算了一下,从咱们国家最北端的漠河、黑河,包括现属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最南端我去到三沙市;从最东边的滨海之都日照,到最西边口岸城市霍尔果斯,我都去过。”
旅行走读的成果之一,便是2018年在三联书店推出的原创学术专著《森林帝国》。阎崇年认为,过往很多学者称满洲东北属于草原文化,其实不对。“大家如果去过呼伦贝尔,站在那一看,天似穹庐,一望无际都是大草原,找棵树都很困难。但东北是森林,不是草原。我从山海关向北穿过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一直到黑河,到哈巴罗夫斯克,满目都是森林,森林蔽天,不见日月。”
“通过考察我得出结论,东北是森林文化,不是草原文化。东北的林海雪原怎么放牧牛羊?满族是狩猎民族,打猎飞禽走兽,骑射是他们祖先的文化。而从满洲人渔猎经济的围猎方式中,逐渐孕育出‘统合’意识,并运用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统合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人群为一体,建立八旗制度,以满洲、漠南蒙古和部分汉人的三股力量问鼎中原,建立清帝国,并维持了268年之久。”阎崇年说。
《森林帝国》出版后,被称为是阎崇年给学术界贡献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发展简史、第一部森林帝国史。书中首次提出中华古代文明五种文化形态: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南沿海及岛屿海洋文化,并论述了文化统合的相关概念。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学术研究讲究“约、博、通”
对谈中,宋志军提问道,阎崇年先生选定清史研究60年,与此同时,满学这个学科实际上也是阎崇年开辟的,他还研究北京史。“除了专以外,还有广博,如何看待治学道途上的专精和广博间的关系?”

宋志军
“虽然袁崇焕是明代人物,但清承明志,明朝不了解,清朝就搞不明白。另外明和清是互相对立的,你从明朝看清,它的问题看得很清楚。反过来从清朝看明,也看得很清楚,这就叫辩证对立统一来观察问题。”阎崇年介绍说,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里重点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当时开学术会议,我就找学术的交叉点。努尔哈赤和袁崇焕交叉,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袁崇焕被皇太极给克了,所以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研究北京史绕不开袁崇焕,北京的龙潭还有袁崇焕的祠堂,东花市斜街还有袁崇焕的墓。所以我在清史和北京史之间找一个交叉点,就是袁崇焕。”
“做学问,用梅兰芳先生的话讲是‘少、多、少’。他唱戏开始少,会一出戏,后来多,能唱好多出戏,最后又少。我问过梅葆玖,梅老先生可以唱多少出戏?他说父亲大概可以唱百十出戏。但到了晚年,梅老先生就是《贵妃醉酒》《宇宙锋》《穆桂英挂帅》《霸王别姬》等,我数过,他就演五出戏左右,经常唱这五出戏,由少到多,由多到少,这就是精。”
“同理,换到学术研究也是三个字:第一是约,简约的‘约’,开始看《东华录》的材料。后来就多,数十万字甚至百万字地看,也就是‘博’。最后又少,少到很精,少到研究努尔哈赤就能变成一本书。这个过程就是‘约、博、通’,到了‘通’就可以成家了。”阎崇年说。
谈到人生90年的体会,阎崇年也给出了四个字,对待事业要“敬、诚、淡、静”。“我有三个‘有幸’:第一,我同龄的同学、同事,很大一部分已经作古,我有幸还有户口本;第二,健在的很多同龄的同学、同事大都出不了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我还能自由活动;第三,我现在90周岁,生活可以自理,上午、下午、晚上分三个时间段,一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日。体力跟年轻时比肯定是不如了,但我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就像蚕吃了桑叶然后把丝吐出来,蜜蜂采了花蜜把蜂蜜献给人间。只要我的身体许可,还是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