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中西书局出版的《日本学者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日]鹤见尚弘、吴滔、陈永福主编)收录了日本明清赋役史领域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共27篇,包括山根幸夫、岩见宏、小山正明、鹤见尚弘、谷口规矩雄、滨岛敦俊、山本英史、岸本美绪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涉及明清赋役制度改革等内容。对于夯实并推动国内明清赋役史研究,这本书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收入了一篇访谈,受访人是山本英史,采访人是佐藤仁史。二人在访谈中回顾了20世纪中叶以来日本的明清赋役史研究,也谈及中国学者的探索,以及明清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等等。在这篇访谈最后,两位学者谈到了另一个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史研究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以及,如何思考全球史流行之下的“地方”。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从“他者”的问题和对话中审视自身,于中国读者和研究者而言,也是具有启发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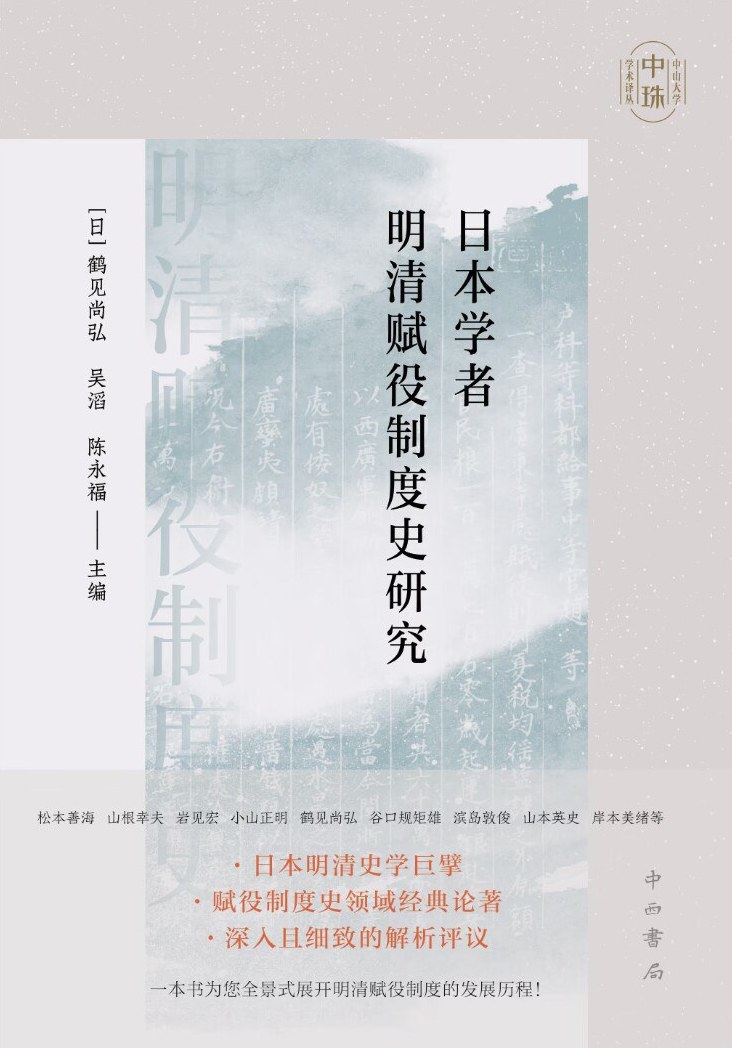
中国史研究的出发点
佐藤:最近,我经常思考的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中国史研究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意义?
山本:中国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从日本的殖民统治开始的,与政治紧密关联,如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所代表的那样,是从占领地、殖民地统治的现实必要性出发的。而且支撑这些的理论是停滞论,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样,日本学校制度中的东洋史就是为了支撑这个政策而建立起来的学科。战后,中国史研究则是从对侵略以及殖民统治的赎罪意识出发的。
佐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这个世代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动机应该怎样概括呢?您觉得呢?老师当然不是从赎罪意识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的。老师您是带着怎样的问题关心来研究中国史的呢?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史研究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山本:哪一个学术领域都存在被称作“〇〇史”的东西,其主要目的是去分析过去而确认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这些对通过时间先后顺序去理解现在的研究对象非常有效。从某种意义上讲,目的意识明确,不需要为“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去烦恼。但是,这与本来的历史学研究还是多少有所不同。
所谓历史学,跟我们应该如何去看现实世界,如何通过历史去理解这些有着非常大的意义。但是,“〇〇史”的话,往往是已经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个定论,然后追溯过去去确认定位的。
典型的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史。它不是依据中国历史进程而追求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个不动的理论已经存在,然后如何把这个理论套用定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去。但是,这和我们本来的历史学还是不同的,从赎罪意识出发也是如此,先有了“中国社会不是停滞的社会”这样的结论。
因为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反过来说也很有做的价值,实证去证明这个事情本身也很有意义。但是,这是本来历史该有的样子吗?我觉得不是。“现状认识规定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是从属于“现状认识”的。年轻的时候我也在不自觉中做了很多“目的意识明确的”研究。但是,内心却感觉无趣。
我认为,历史学从这种桎梏中解放的今天,不以这些框架为前提,通过对现实存在的理解,可以看见很多东西。不被意识形态所束缚的历史研究,某种意义上讲不聚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但是,不是说把焦点放到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上就一定能够正确地理解历史。这种认知困难是切实存在的。关于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学这个问题,如果设定一个“为什么要研究”作为前提就无法研究历史学的话,“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提起本身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佐藤:比如,日本人研究日本史的动机非常好理解,与自己的民族意识、自己本身形成这个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并且,可以通过欧美历史中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作为前提来把握。到现在为止,日本人还有着很强的“脱亚入欧”的精神影响。但是,对中国,政策需要、现实需要、赎罪意识等动机更多被提起。对这些动机抽丝剥茧去剖析时,中国史学习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备选的答案。在人员流动和文化交往中,中国非常重要,是离日本最近的大国,对日本有着直接影响等地缘政治学观点的答案能够被想到。迄今为止,文化等广义的范畴中,也有日本同在这个文明圈中的理由。但是,每一个说明都有些力不从心。至少无法勾起现代日本年轻人的兴趣。
如果脱离中国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为什么对阿拉伯世界感兴趣,为什么对非洲感兴趣等问题,因为感兴趣这样的动机已经足够且重要。如果没兴趣根本不想去知道。
山本: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研究外国史这个问题是一个永远的课题。另一方面,因为你是日本人所以要研究日本史这种想当然的想法,也有着进一步商量的余地。
佐藤:至少日本学生,抱着这样的动机选择日本史专业的人很多。
山本:我也知道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研究西洋史这一个问题,不但从明治时代开始,其实现在也都还没有弄明白。西洋史的研究者对研究西洋史的意义是怎样回答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佐藤:研究法国地方历史和想要研究中国江南史,我认为大致相同。如果说到和日本史之间的关系,感觉是很遥远的世界。
山本:研究西洋史的人很少把欧洲全域作为对象,各自对比如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等根据个别地域对象进行区分。为什么以这个国家为对象呢,学生给我的反馈是:“我读了那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或者去旅行时接触到了古迹,对此产生了兴趣。”这是比较单纯又直接的表白。但是,作为专业的研究者,这样说的话就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呢?像刚才所说的那样,中、日两国历史上关系很深厚,距离很近,影响力很大,等等,可以列举很多理由,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么其他的东亚国家都可以。所以中国还是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魅力。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这个问题,我个人观点很单纯,就是因为非常有趣。以前开始就是邻居,相处很长时间,但到现在也不是很了解,身形庞大却粗中有细,感觉他很放得开但却很爱面子,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个“奇怪的人”。而且,又无法搬家,所以以后还必须要相处,所以没办法当作看不见。对于这个邻居,会产生“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诸如此类的兴趣,这就产生了想要了解这个人的欲求。“秋深感哀悲,邻人将何为” ,这首俳句就非常能代表这种心情。
另外,不该被忽视的还有,在我们觉得中国是“奇怪的人”的同时,中国也觉得我们很“奇怪”。如果我们以逆向思维去比较思考我们日本人为什么觉得中国人很“奇怪”,为什么觉得日本人不会采取像中国一样的行动模式,中国某种程度上可以当作与自身作对比理解的“一种镜子”。从这个层面来看,对于日本人,中国是再好不过的邻居。
佐藤:因为我也有时会想到“镜子”这个表现形式,听到您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增加了不少勇气。无论以哪个国家为对象,看到观察中的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有这种目光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重要。
“历史综合”科和中国史
佐藤:这几年,全球史的呼声很高,所以在高中也开始了一种叫作“历史综合”科的新课程。 通过“地方”“国家”“地域”“全球”的多层性、多角度的解释方法备受重视。特别是从高中教育的现场去考虑的话,这里“地方”的前提是我们的周边地区。我觉得把周边地区作为前提是因为可以实际去田野调查或现场调查。但是,外国史研究中的“地方”,对于更多人来说是非常不熟悉的存在。所以,如何在“历史综合”科中去考虑这个“地方”呢?
山本:“历史综合”科是世界史和日本史一起教的意思吗?
佐藤:是的。内容从18世纪开始。也就是说,用全球化的角度去把握和现在有直接联系的近现代史。
山本:如果这样的话,无论如何都是以日本的现代化为话题的中心。那么,像以前一样的框架范畴中的西洋近代社会形成,明治以后日本的西洋文明开化肯定是要学的。在这里,亚洲的历史基本上就被排除了。
佐藤:结果,就变为“西方冲击”。提起和亚洲的关联,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还是会被作为焦点。当然这些知识的确有必要知道。但是,考虑中国史时,中国的近代是很晚才开始的。那是因为明清时代的制度、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完成的形态,因此中国异常艰辛地清算这些。对其完全不去了解就开始学习近代,结局就好像西方冲击才带来近代化一样,变成一种隔世的认知状态。中国如果不从长时段去进行把握是无法理解的。
山本:说从全球化去理解,但实际上,前近代中国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将完全被舍弃。
佐藤:的确是这样。就是要通过“世界史探寻”科学习的意思吧。
山本:不需要我们刻意强调,中国的律令制度以及儒家、佛教对日本文化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历史综合”科的话,这些将全部消失。
佐藤:只是用“历史综合”科的范畴,无法被说明的东西有很多。“地方”,比如像以日本的多摩市和町田市为出发点的历史还相对比较容易分析。但只是用近现代的范畴把江南的县或城镇、四川巴县跟民族、地域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山本:只要是从对于中国的兴趣关心,也就是“好奇心”出发的话,其实研究哪个地区都可以。但是,正因为想把它做到普遍化所以才难,而且也不知道普遍化到底有怎样的意义,更不知道普遍化是正确还是错误。而且,做到哪个地步为止可以普遍化也是一个问题。再者,外国人去做要耗费大量精力。
我觉得正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模糊不明确,反而可以从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觉得自由地去研究、不被指责是最好的。而且,到这个年代,你研究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责难也减少了。就在这之前,研究的意义经常被说起。我的前辈中有一个人,说中国史要是有封建制就好了,如果有封建制,就会有资本制,也会产生社会主义,所以主张一定要找到封建制。但是如果带着这种心情去研究中国史就太枯燥了。历史经常被称为科学,但我现在认为并不是这样。我反而觉得历史不应该被隶属于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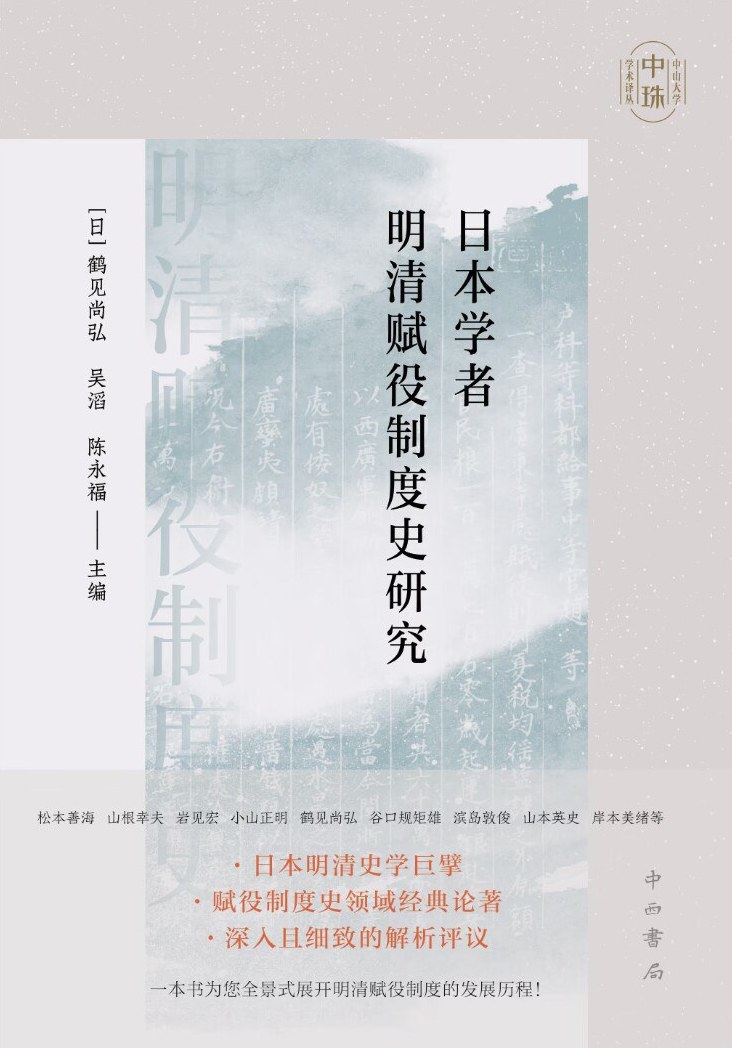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