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涌现出一股历史转向的热潮,社会科学家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求灵感与资源,借助历史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来回答当下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任何社会政治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起源与演进过程,只有了解起源与过程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积极的思路。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通过对十五位引领潮流的著名学者的访谈,力图生动地反映这一转向背景下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发展进程。本文是郭台辉与彼得·伯克的对话。
学人简介:
Peter Burke(彼得·伯克),剑桥大学历史系;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文献来源: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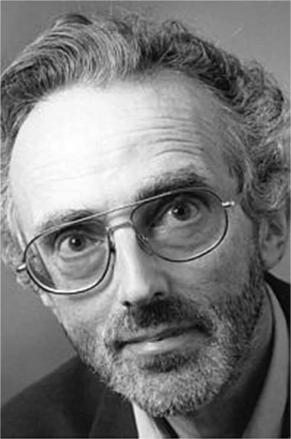
彼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郭台辉: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您关注社会史与文化史并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而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作为一场学术运动,主要是抵制19世纪由德国洪堡与兰克首创的主流史学范式。正是从70年代开始,正统的兰克史学就逐渐成为多元的史学,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因此,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題,我们如何可能从多元的历史学研究中获得可靠的客观知识或者事实?在史学研究中是否存在一种牢不可破的现象学基础?
伯克:在我看来,正统的、主流的兰克史学从来都是一种幻觉,往往是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中心论的虚构,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类观念与活动的多样性,无论个体还是集体层面的人类都从来不是单一的。同样,我认为客观史学也是一种错误的追求,正如查理·贝尔德(Charles Beard)称之为“贵族梦幻”。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里,史学界已经集体发展出几种批判方法,这让正统的兰克史学观完全抛弃了一些对过去的错误阐释,戳穿了许多谎言(比如对大屠杀的否认)。
郭台辉:作为文化史学家,您能否评估一下倾向于长波段结构变迁的宏观史学的优劣之处?
伯克:我认为,宏观史学在经济史与社会史方面做得最好,可以大规模运用清晰的定量方法来测量结构变迁。即便如此,我认为纯粹的宏观社会史是相当“空洞的“,无法理解人类经历的结构变迁。我认为,宏观方法对于文化史应该有着积极作用,但其作用不如在社会史中明显,而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可以对微观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
郭台辉:几十年来,比较历史分析成为历史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在美国尤其如此,但一直以来也遭到诸多非议。那么从您的新史学来看, 比较历史分析如何可能运用自变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进行比较?
伯克: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形式的历史比较研究来回答。当我研究有关17世纪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两个城市的政治精英时,我可以统计并比较它们相关的财富,至少是在公开征收的赋税方面,其精确性完全可以是合情合理的。相应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容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当我试图讨论并比较它们的教育、宗教信仰或者价值时,我就被迫更为主观或者凭印象,只好从精英群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推测,把他们假定为更大社会群体的代表。所以无法一概而论。因此,主题和问题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择,哪种方法更适合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相反,更不存在方法之间的优劣。
郭台辉:您似乎并不赞同把历史学视为科学,是吗?那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您是如何理解社会理论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呢?
伯克:历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取决于你如何理解“科学”。在19世纪前期开始就有一个普遍认识,认为自然科学可以为所有历史与社会研究提供绝佳的模式与方法。从此之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这个表述就开始存在。今天,我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认为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竭力去模仿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实际上,从事学术研究的行当也不存在某种唯一的“科学方法”,因为天文学家与化学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他们运用截然不同的研究策略。我用德语来回答这个问题更准确。在德语中,历史学并不是“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l),但确实是一门“科学”(Wissenschaft)。因为它是一种系统研究,已经发展出某种明确的研究程序与规则,诸如对史料来源的批判性考察,尽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各个不同方面的东西都充满兴趣,比如政治事件、社会结构、文化符号,等等,使得这些规则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对史料来源的考据与证伪还是一致坚持的。
无论如何,从“硬科学”(hard science)意义上来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都不是科学,但这并不严重影响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学者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创造性联系。历史学家可以借助社会科学家创造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以从历史学家那里了解到长波段发生的各种变化。由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作用的影响,我们有时候很难判断某本书是由历史社会学家写的还是社会历史学家写的。当我出版《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一书时,有些人评论时就认为我是一名社会学家。
郭台辉:有些一流的社会学家,诸如查尔斯··蒂利与沃勒斯坦不太喜欢“历史社会学”这个表述,也抵制把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列入社会学的子学科,转而呼吁一种“历史社会科学”,希望与历史学界所表述的“社会科学的史学”完全融合。您能评估一下这种前景的可能性吗?
伯克:我认为,蒂利与沃勒斯坦关注大结构的历史变迁,对西方社会与经济变迁的研究起到过非常有价值的贡献。我希望有人能继续超越他们的研究,不论所受的训练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但除了他们关注的社会史与经济史之外,历史研究还应该有许多其他的主题与方法,尤其是关注微观层面、人类体验、文化等方面。这与他们研究的宏观长波段大结构变迁是互补的。只有当这些方法—主题与蒂利—沃勒斯坦模式融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时候的“历史社会科学”才真正等同了“社会科学的史学”。
郭台辉:我与社会学家迈克尔·曼交流过,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英国迁居到美国的,对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英美的差异有体验。我问过他一个问题:“历史社会学在美国与在英国有何主要的差异?”他认为,这个主题领域在美国表现得非常突出与活跃,但在英国几乎不存在这个说法,所以美国的历史社会学比欧洲的健康得多。您如何评价他的观点?
伯克:我相当同意迈克尔·曼的观点。如今很难想象在英国大学或研究所工作的学者能出版一本不错的历史社会学作品,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曼自己的著作可以说是英国人在这个领域的贡献。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种英美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为英国训练过许多转向历史的、年轻的社会学家,他还严肃批评过那些他称之为“回避历史"的研究。但只有少数学科和少数人能够认真对待并接受他这个批评,比如史蒂芬·门内尔(Stephen Mennell),但他也与曼一样,都是在海外谋教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而不是在英国本土。
归纳与演绎之间
郭台辉: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出现过一场方法论之争,主要是历史社会学家们之间争论归纳与演绎的差异及其相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是如何理解这种争论,如何解决他们的争端呢?
伯克:我们所有人都同时需要这两种方法,即使不同学科和不同文化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光谱的经验主义一端,在英语国家的学者与普通大众也是如此。所以要在英国训练成为史学家,就等于必须忍受双重的经验主义,同时还应极大怀疑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我认为这场方法论的争论至今并没有解决,至少不可能永久性地化解争端,但我所希望的是一种糅合与折中的方式,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允许存在个性化的差异,而不是对任何人灌输或者强迫某种千篇一律的模式。
郭台辉:倾向于历史的社会科学家通常关注解释,而倾向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更关注阐释或者叙事。我们年轻一代的学者如何可能在解释与阐释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
伯克: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尝试解释与阐释,虽然因不同的学者据于不同的考虑而对二者之间的平衡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我们也应该根据自己已经选择的主题、方法或理论来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而不必过多考虑是否达到某种平衡。
郭台辉:随着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浪潮以来,有人进一步主张后学科时代的来临,也有人呼吁进入无学科划分的时代。他们似乎在反思通过系、专业或者学科来划分的知识生产传统。您如何看待这些反思?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方式,尽可能整合历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推进人类福祉与和平提供更完整的知识生产?
伯克:这个问题很不错,我的观点可能与众不同。像不同的文化及其语言一样,每一个学科都包含特定的视野和独特的洞察力。假如你所提出的雄心变成现实的话,能够把不同的学科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某一个学科,那么许多视野和洞察力就消失殆尽。因此,对于那些在某个学科得到训练的学者来说,不是去整合更多的学科,更重要、更可行的方法是开放视野,广泛阅读与思考,从外部获得灵感与想法,以此用来并转化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至于“后学科"时代,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学科复制与再生产的时代,增加专业化,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处理与日俱增的信息量,用来解决与日俱增的私人生活问题和公共生活问题。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