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是关乎人类社会团结和秩序的基本论题。在西方社会理论中,共同体取向与个人主义构成理解公共性的基本范畴,从托克维尔和涂尔干对个人主义的批评和重建,到列奥一施特劳斯的“正当”和“权利”之辨,再至罗尔斯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公共性设计、贝克的制度化个体化,都在这一范畴下推展。相比于西方公共性的个人主义基础,在中国,无论是张集馨代表的儒家士大夫阶层抑或“马桥”这样的准自然社会,公共性的想象和实践,都离不开差序格局这一家庭隐喻。差序格局与个人主义的冲突、调整和重塑,是现代转型背景下中国公共性建设的基本语境。
精彩书摘
《公共性及其实践(中西古今之间)》:
这里需要先审视“公共性”。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起点是个人主义,但公共性在其中的地位一点也不逊色,不仅是保护和维续个人主义的唯一有效工具,亦同个人主义一起构成其政治哲学的最终目标。“作为公平的正义也要求政治正义的第一原则是公共性……在关于基础结构的诸政治观念中,公共性条件看起来也是适当的。它意味着原初状态中的各参与者在评估诸原则时应该考虑公民的公开承认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后果,即这些原则是相互承认的,并因此而将有效地调控基础结构。”(Rawls,2001:86)在这里,公共性意味着理性的公开运用以及公民们对某些基本原则——“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某些这类重大价值就是被正义诸原则所表达的、存在于基础结构中的正义价值:平等政治和公民自由价值,机会公平的平等价值,经济互惠价值,以及公民自我尊重的社会基础的价值”(Rawls,2001:189-190)的公开的相互承认,以及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合作精神”(Rawls,2001:118)和合作实践。这种公开的相互承认和合作精神将构成、影响并有效地调节基础结构(Rawls,2001:121)。
公共性的运用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公民们对正义诸原则以及基础结构的各项制度实际满足这些原则的公共知识(或者理性信念)的相互承认”。第二个层次是公民对一般事实的相互承认,正是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原初状态中的各参与方选择那些原则。第三个层次是对作为公平的正义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完全正当化的相互承认。也就是说,公民对其正当性的知晓与你我这些正在研究这一观点的人所知晓的一样充分。当然,他们未必能很深刻地自我反思;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就能从公共文化中获得充分的正当性。当然,当各种统合性学说中存在重叠共识时,公民们就将正常地拥有自己确认该政治观念的更深基础,这个事实也就变成公共地知晓了(Rawls,2001:121)。这三个层次应该说是一个从抽象走向具体,从话语意识走向心灵习性的过程:第一个层次是实践理性意义上的,是具有充分理性的公民对抽象原则的相互接受和承认;第二个层次回到一般的事实,公民们以某些事实为参照而接受和承认抽象的正义原则;第三个层次则是文化的,不管一个公民的理性程度如何,只要浸染在相应的文化中,就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原则从而推动公共性的达成。这种逻辑与康德关于实践理性的逻辑高度一致。
罗尔斯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并无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是两个似二而一的概念。公共理性就是“适合于平等公民的推理形式。这些平等公民作为一个合作体在国家权力许可的支持下相互施加规则,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探究与各种推理方法的共同指南塑造理性的公众,而宪制体制下的言论和思想自由使得这种理性也是自由的。与此相对照,非公共理性是适应于社会中的个人和社团的理性:它指导他们在做出他们个人的和社团的决定时如何十足恰当地深思熟虑。教会和大学以及科学家协会和私人俱乐部的非公共理性各有不同。这些协会有不同的目标和意图,在政治正义范围内,他们非常正当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自我审视。”(Rawls,2001:92)在上述文字中,罗尔斯界定了“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基本特征:第一,对公共性的界定是以国家这样一个政治社会为边界的。基于此,罗尔斯区分了公共理性与非公共理性,前者是基于政治社会,后者则基于各种共同体、社团以及私人。进一步看,非公共理性可以区分为集体理性与私人理性。所谓集体理性,指涉的是共同体、社团自身的理性,私人理性则指个人“如何思考把政治领域的各种重大价值与他们所接受的其他价值关联起来”的理性。属于公民个人的良心自由的一部分(Rawls,2001:190)。
这一点也是罗尔斯同社群主义相区分的标志,他强调公共性不是部落主义的公共性,而是政治社会这个更大范畴的并可能运用到世界政治社会中的公共性。第二,是平等公民在国家权力边界内,在宪制体制的保护下,自由地、公开地相互运用理性进行探究和推理,国家权力边界内理性的运用是平等的,其基本规则是统一的,这一点与非公共理性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局限于某一个社团或者地区内部,其所遵循的规则只适合于本社团或者地区。第三,理性是支持公民所要表达的政治观点的基础,是公民在表达其政治观点时所必须公开接受的规则,因此,理性的运用应该是公开的。“在产生基本的政治问题的诸个案中,公民必须能够相互表达支持其政治观点的被公开接受的理性。这意味着我们的理性应该归入通过政治的正义观念所表达的政治价值之中。”(Rawls,2001:91)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界定显然带有康德的痕迹。如前所述,康德对公共理性的界定坚持公开的反身性原则即罗尔斯所说的互惠性和反思平衡原则,要求理性运用者面向公众把求诸于人的理性同时求诸于己,以保持理性运用的平等性和真诚性。第四,公共理性的最为基本的根据是政治权力既是国家的也是公众的,是平等公民共享的政治权力,在宪制和基本正义问题悬而未决、国家权力合法性缺失的情况下,公民基于公共理性来推行和实践政治权力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引入公共理性理念的一个理由是:虽然在民主政体中政治权力总是强制性的——依靠政府垄断的合法强力的支持——但它也是公众的权力,换言之,是作为合作体的自由和平等公民的权力。
但是,如果每一个公民平等地共享政治权力,那么,只要有可能,至少是在宪制和基本正义问题处在悬而未决状态时,政治权力就应该以一种所有公民据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够公开拥护的方式来运用。”(Rawls,2001:90)第五,正是在理性被运用的过程中,理性进入公众的心灵、思维和行为中,塑造和重造理性的公众,从而进一步推动公共理性以及公民合作体的形塑和稳定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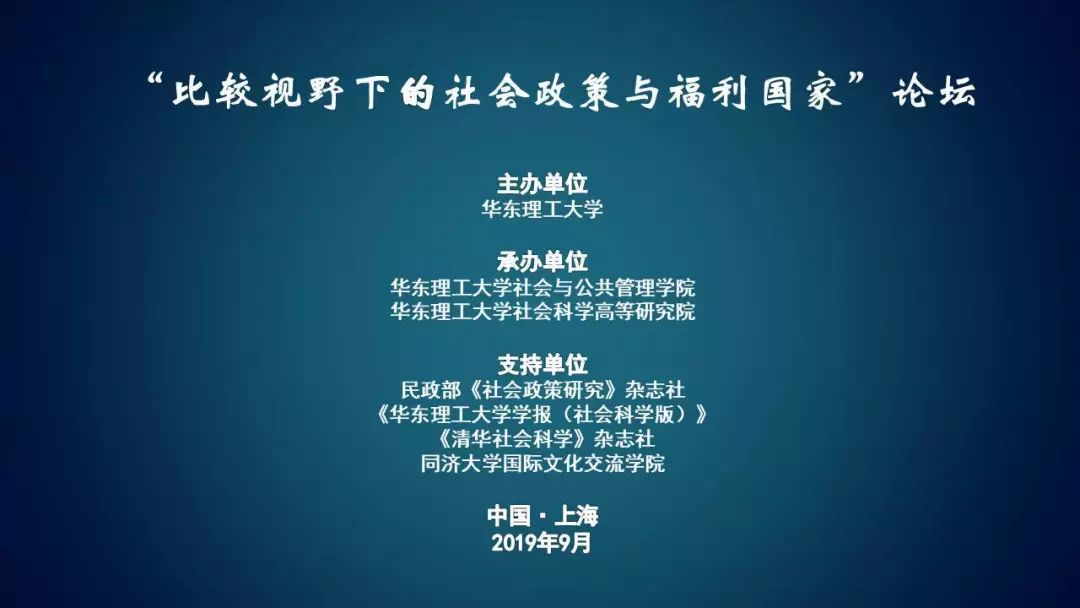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