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作者韩礼德;译文发表在《东亚学术研究》2022年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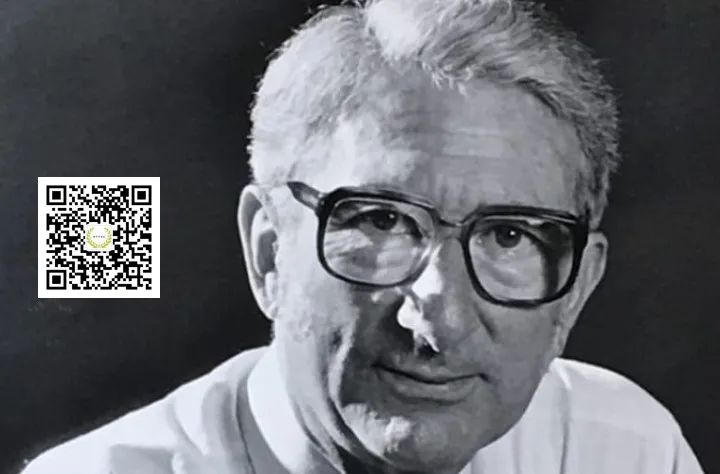
学
术
观
点
都市社会中的语言
韩礼德 著
丁建新[1]、苏根英[2] 译
[1]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2] (通讯译者),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是韩礼德语言理论的重要著作。本文出自该书第四章“语言与社会结构”。本文主要观点有:一、语言变异是社会结构的象征表达。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意义表达习惯,不同的意义表达方式也负载了附加在社会群体身上的社会价值。二、都市方言的显性差异在于发音与词汇形式,但更深层次的区别是语义模式。方言本身无优劣之分,人们讨厌某些方言是因为其意义表达方式及象征。三、语言变化的动因和机制可在少儿同伴交际与口头游戏和竞赛中发现。
【关键词】方言;社会结构;都市社会;语言变异
城市乃言说之都,由语言建造和维系。城中居民花费大量精力与彼此交流,在交流中,他们无时不刻不在重申和重塑那些定义都市社会的基本概念。如果倾听城市言说,你总能听到那些有关城市机构、时间地点、出行方式,以及城市生活中特有的社会关系类型的说辞。
以上或许可以用“言语社区”这个熟悉的术语来描述(Gumperz 1968)。一座城市就是一个言语社区。但是“言语社区”是一个可以用于几乎任何聚集人群的通用标签。因此必须说明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以及作为都市社会的一种描述,它被赋予什么特殊意思。
“言语社区”是理想化的构想,其中整合了三个不同的概念:社会群体、交际网络、语言同质,三者都有各自的规范。在这种理想化的意义下,言语社区指这样一群人,他们:(1)由某种社会组织联结;(2)相互言说;(3)以同样的方式言说。
方言学家们一直认为这样的言语社区是理想化的构建,现实中的人类群体只能接近这种理想状态。某个欧洲古村的村民们可能确实形成某种交际网络,例如在利特尔比(Littleby)、克莱恩斯达(Kleinstadt)或马尔戈罗德(Malgorod)的村庄里,罕见陌生人。但是除去生活在同一个村子这个事实外,很难说村民们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社会结构。此外,他们确实不以同样的方式言说:想想土地主和牧师的言说方式。
尽管如此,作为乡村语境下的一种语言学模式,“言语社区”概念有较强说服力。“利特尔比方言”指的就是利特尔比语言中最为独特的语言形式,即那些将之与邻村方言明显区分开来的形式。如今这种方言通常仅为最年长的村民使用。乡村方言研究一直以来严重倚赖年长村民,一方面无疑是因为希望他成为语言学家理想中的纯正信息提供者,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更可能说“纯正利特尔比方言”。这就有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我们一贯认为,在语言史上,分歧是常态;时间越往后推移,方言之间差异越大。但是当方言得到系统性研究时,乡村地区的语言分歧趋势已经被语言聚合趋势所替代。年轻一代不再囿于乡村,在语言方面,他们也逐渐远离乡村方言的独特形式。
直到20世纪60年代,研究兴趣才转向都市言语。现代都市方言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的创新,他首次将语言学引入纽约街头(实际上首先是在纽约的百货公司(Labov 1966))。在都市语境下,经典的言语社区模型很快就开始瓦解,不再是与现实相对的理想形式。拉波夫很快发现,联结都市居民的,与其说是他们的语言习惯(这是极其多变的),不如说是他们的语言态度和偏见(这些始终如一)。一个普通的纽约人(或芝加哥人、伦敦人、富兰克福人)的言说方式不仅与其他纽约人(或芝加哥人等)不一样,甚至和他自己的都不一样。拉波夫的调查对象听录音后,给说话人打分,以确定说话人的职业等级,他们的评分等级惊人一致。但是尽管他对他人的语言评判可能始终如一,他在自己的言语实践中却远非一成不变。他甚至常常察觉到自己言语实践的不一致性,并且为此担心。他了解一些常规,并认为自己偏离这些常规,这就存在三方面的区别:(1)他说的话;(2)他认为他说的话;(3)他认为他该说的话。拉波夫甚至设计了一个“语言不安全感指数”,以此来测量说话者认为与他认定的常规的偏离程度。
都市“言语社区”是一个异质结构,其差异不仅表现在个体之间,也表现在个体内部。这让我们认识到都市言语的一个基本事实,即语言本身是可变的。换言之,语言系统是变化的系统。我们不能将都市言语描述为某种不变的常规以及对常规的偏离;可变性是语言系统的内在属性。换言之,都市言语规范指的是空间的规范,而非观点的规范。实际上,许多语言学家会声明这是语言的普遍真理。他们会将语言看作是一个高度灵活的系统,而非外行人(或语言哲学家)所认为的不变的系统。
没有证据表明,在都市居民的头脑深处潜伏着某种统一的言语系统。相反,在他头脑中内化的是一种极为异质的模式。他的应对方式是从中选择少数变量,并赋予它们不同的规范度值。所谓的一致性,指的是赋值的一致性。在像我们的文化这样的一个等级社会结构中,赋予语言变体的值是社会价值,语言变异则是社会结构的象征表达。赋值的一致性并不是说都市中的每个社会群体对某种语言变体的社会价值的赋值完全一致。一种语言变体对某个社会群体而言是高贵的(至少是在某种具体社会语境下的目标),但对其他群体而言可能是嘲弄与规避的缘由。但这本质上没区别,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同一现象。选中的少数变量作为社会意义的载体被凸显。
所以城市语境下的语言是变化的语言,其中某些变量承载着社会价值,是社会的标记,并在正式言语中顾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语言变量只有两种形式(或曰“变体”),那么这两种变体必定形成“高下”对立。在下面这组句子中(两者都能在伦敦听到)共有五对这样的变体:
I saw the man who did it, but I never told anybody.
I seen the bloke what done it, but I never told nobody.
这些对立的变体包括;I saw / I seen, man / bloke, who / what, (he) did /(he) done, never … anybody / never … nobody。此外,还有一些没有体现在拼写上的语音特征区别。语音特征的区别是连续的,而非对立的。例如一些元音的发音,主要是在单词I和told中的元音,以及单词but中的末尾辅音。群体内部都知道哪些变体是“高级的”哪些是“低级的”(群体之外的人则无从知晓)。如果说话者两种形式都掌握了,那么选择哪种一定程度上与话语的具体使用情形有关:高级形式常用于正式言语而非闲谈中。因此,看来语言系统的变异似乎通过某种方式由社会语境调节。
语言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由社会语境调节,但不能简单地说由社会语境决定。说话者可能在正式场合使用高级变体,在非正式场合使用低级变体,我们不妨称之为“一致式”。但他也可能使用非一致式,即在规范形式的语境之外使用,目的是取得前景化效果,如幽默、震惊、嘲讽,或者具体语境下的许多其它效果。重要的是,这种语言变异是承载着意义的。特定情境下某个特定选择的意义,取决于一系列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能使任何意义交换体现某种社会现实。
接下来我将证明这只是冰山一角,并非只有独特的语法或语音特征才承载社会价值。某种意义上,整个语言系统都负载着社会价值,这与我们一直以来的看法不同,层次更深。但是我们首先简要回顾语言系统中的变异。如前所述,语言系统是一个变化的系统——但变化是有限度的。总体而言,各种都市方言是某个方言的不同变体,客观来讲,它们之间差别不大。在这方面,都市方言与现存的乡村方言(如英国的方言)不同。现存的少数几个英国乡村方言在发音、语法和词汇方面各不相同,其差异比任何英国或美国的都市方言之间的差异都大。这个状语“在发音、语法和词汇方面”构成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款,我在下文将再讨论这一点。但是因为这个限制性条款,我们可以说哪怕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或者其他说英语国家中差异最大的都市方言,如美国中西部中上阶层语言与所谓的黑人土语,它们的差别也不如约克郡乡村方言和萨默塞特(Somerset)乡村方言,甚至约克郡乡村方言与伦敦都市方言之间的差别大。当然这只是主观印象,我们无法测量这些差别。我们也可以指出这个事实,上文提到的那组乡村方言大体上难以相互听懂。可惜这个结论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客观意义上差别不大的语言变体通常被说话者认为差别显著,这就造就了一个互相无法沟通的鸿沟。说话者对语言变体的判断常常是社会的,而非语言的:“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是一个有关社会结构而非语言系统的论断。所以语言方面的差异(如果我们视之为纯语言概念)并非有益,也不可靠。总之,从语言变异整体而言,都市方言是在有限范围内的变体,这是事实。
要讨论“方言”和“标准语言”,需要先回顾方言和语域的区别。方言是由说话者定义的语言变体:你是什么人就说什么话。从这个方面讲,方言与语域(另一个维度的语言变体)不同:语域是由社会语境定义的语言变体,由当前正在做的事决定。方言是你平常说的话语,语域是你正在说的话语。人类文化中常见的是,一个说话者常常能说不止一种方言,当他转换方言时,就意味着语域的变化。“标准方言”是已经取得独特地位的方言,大家公认它在某种意义上履行了超越不同方言群体边界的社会功能。“标准方言”通常与书写和正式教育有关,在许多文化中,“标准方言”被称为“文学(即书面)语言”。因其特殊地位,说话者通常很难认识到标准方言实质上只是与其他所有方言一样的“某种方言”而已。在说英语国家,通行的术语将“标准语言”与“方言”对立起来,由此通过拒绝将“标准语言”视为一种方言,赋予它独特的社会地位。
再谈都市语境下的语言变异。通常不同的次文化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代际等)选择某些语言变体要素,以此与其他次文化划清界限。某些较为通行的语音或语法特征逐渐与某个社会群体联系起来——首先是他人这么认为,然后群体内部也可能持同样观点——因此象征着那个群体。例如,某个群体常被认为在元音后面加入或者省去r音,或将词首的清爆破音发成或不发成摩擦音(如 a cup of tsea, in the pfark),或不用定冠词,或使用某种否定结构,或某种句子结构(如He’s not here isn’t Tom,对比:Tom isn’t here.)。某些词也能起同样作用,只要它们的频率足够高。(这里说的不是俚语。俚语是有意识的选择,是人们为某种社会目的而特意使用的某种言语变体。)如果你来自群体之外,你就察觉不到这些变体的区别,也很难相信变体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但是对于群体内部而言,区别不言而喻。
方言基本上就是总是相伴出现(或至少是经常相伴出现)的变体集合。在城市言语中,这样的变体组合绝非一成不变。我们无法在方言A和方言B之间划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说方言A有这样那样的言语特征,并且这些语言特征总是共现,而方言B的特征则完全不同等等。现实中方言之间的区别更具连续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变体之间并不能任意组合。我们常发现语言变量都有一个从高到低的“级度”。顶端内部变量、底端内部变量各自的共现频率都较高;而位于两端的变量随机组合的频率则较低。因此有一些语言特征的常规组合被当作典型组合,它们常对应着主要的社会经济群体。当一个群体内部的人与火车上的邻座开始交谈时,他马上知道他来自哪里,教育程度如何,做什么工作。
社会方言变化的这种系统性模式如何兴起,我们知之甚少。我们无法详细描述都市语境下的人际交往模式。显然不同社会阶层确实相互交谈,并没有什么山川河流将他们分隔(只有轨道)。然而,虽然不同都市言语变体随着时间不断进化,它们并不像曾经希望的那样,表现出任何大的融合趋势。尽管确实出现了一些小变化,但尚不足以消弭差异。相反,拉波夫发现都市方言多样性增加了。倒是有一种融合趋势,不过不是语言方面,而是对语言的态度: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语言评判越来越趋于一致。这种明显的悖论,即越来越同一的语言态度与越来越多样化的语言表现,从语言的社会功能角度来理解,根本不是一个悖论。与其说语言多样性增加,不如说语言多样性与社会阶级结构的相关性程度增加。语言越来越成为社会阶级的度量衡。
语言变化的一些实际动因和机制能在少儿同伴交际中发现。在家庭、同伴、学校这三大主要社会化机构中,同伴是我们了解最少的,这显然是因为没有成人参与。在某些次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社区组织——一个语言联结中心,明确规定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同时允许加入和出局,以及重新加入这个重要功能。它同时也是语言创新中心。例如,元音裂变[1]游戏似乎从中世纪时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说英语的城市儿童中流行。(元音裂变游戏使得女孩名Ann听起来像男孩名Ian。用安格斯·麦金托希(Augus McIntosh)的生动比喻,就是英语元音像沸腾的牛奶一样,在口腔内相互追逐。)对于那些仅在一个社会群体里发生的语言变化而言,这似乎是其根源之一。
但是无论社会方言来源何处,人们都能在社区中清晰地辨认和确认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这样一种方言(即语音、音韵、语法和词汇特征的组合),它关联及象征着可以不同程度上客观定义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通常贴着流行的社会地理标签,如“中低阶层南部地区”等。一方面这些标签很流行,因为人们在脑海里明确且持续地将之与某个特定群体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些标签又不受欢迎,因为使用它们常常让人尴尬。
多数人可能常用一种方言,这种言语形式对他们而言是自然的(即使同一种方言也可能有很多变异之处)。同时人们可以,也经常跳出这个方言。都市言语社区中的个人不总是囿于一种语言习惯模式。他通常有一个非标记的语言身份,他的言语通常在这个语言范围内。此外,他还掌握其他方言,他或随机或系统地自如运用这些方言。这种方言转换部分地在有意控制之下,所以说话人选择哪种方言,要么是因为情境需要,否则,那就是方言的使用创造了情境。如果你在工作中常以某种方式说话,那么即使不在工作场景,这种言语方式也会唤起工作情境。(这是言语变体首先与相应情境关联的最重要证据。)通过这种方式,方言转换在都市居民擅长的语言竞赛和口头幽默中发挥作用。
语言参与游戏,都市言语也不例外。都市言语通常与各类口头游戏和口头竞赛相关。讲故事就是其中一种常见模式,与其他口头游戏一样,讲故事通常是竞赛性的:故事高手不仅自己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还能设法让别人的故事黯然失色。少年儿童与同伴之间的互相咒骂,和其他游戏一样有双重属性,既是语言游戏,也是语言训练。口头语言游戏也可以发展为非常复杂的形式,如诗歌竞赛以及高度仪式化同时非常残忍的游戏,如瓦扬(Vailland 1958)所描写的意大利南部的“法律”[2]。最受人关注的语言游戏似乎多为男性活动。研究它们在女性中的相应形式如何,会很有意思。
口头语言游戏涉及所有语言要素,如韵词、节奏、词汇和结构,但其本质还是意义,包括社会结构中蕴含的意义(如前述几个例子所示)。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游戏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模仿其它群体的发音和语法,同时模仿他们的常见角色和态度,这是创造刻板印象和维持现有刻板印象的有力方式。同时,发展社会语言游戏潜势,也可以作为防御。当某个社会群体受到压力,察觉其语言规范被其他群体轻视,它常常会精心开发一种复杂语言艺术,单独推崇其语言规范。
回到前述观点,即“整个语言系统都负载着社会价值”。要理解都市社会中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换言之,如果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们是否都表达相同意义?
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我们通过朋友们表达意义的特有习惯认出他们,正如我们通过他们的面貌、声音、服饰和走路方式认出他们一样。人如其“意”。但个人并不脱离语境而存在。他存在于与他人的交流中,意义是交流的主要形式。意义是社会行为,受社会结构约束。人以群分,我们表达意义的习惯与所在群体一样,正是群体定义了我们的符号环境。那些转换过社会群体的人,如从中产阶级家庭到工薪阶级同辈(或反过来),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都明白他必须学习表达不同的意义。从一个民族社区搬到另一个民族社区,意味着大量的语义重新调整。参军、跳槽、入狱也是如此。
为何如此?我们习惯于从发音、词形、词汇方面考虑方言差异,这些是更为明显的语言要素,也是在历史进程中变化最快的要素。但是婴儿学习说话时,最先学的是什么?他学的是语言系统中的“外围”层次,是位于语言系统两端的两个层次:一端是语音层,指的是言语中最基本的节奏和语调模式,胸腔与喉咙中声音的跳动;另一端是语义层,是表达意义的基本方式,或不同语言情境下的符号习惯。这些习惯深入我们的意识深处。无论时光变幻,无论语言形式如何变化,这些习惯依然不变。回到我们先前谈论都市方言差异时所提到的限制性条款[3]。如果说黑人英语中存在非洲语言基础——很有理由相信确实存在——这种非洲语言基础一方面可能表现在潜在的节奏和语调模式,以及气流方式,另一方面表现在意义的深层趋势,即语义模式,而不是表现在引述最多的更为明显的语音和形态特征。
任何多元社区中的社会群体都有不同的意义表达习惯,伯恩斯坦(1975)称之为“不同的社会语言编码倾向”。对于同一个社会语境,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意义解读。对于同一情境下的符号结构,他们也有不同的概念命名。一个社会群体可能视之为私人信仰的公开宣告,另一个则视之为关于客观世界的观点交流,第三个群体可能另有不同看法,如视之为游戏。不同代际与性别之间的交流充斥着这种符号错配。定义某个个体的,不是他个人的语义配置,而是他作为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城市居民在任何时刻都有某个社会群体身份,只有当他是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一员时,他才是引人注目的。
因为不同的社会团体在特定语境中采用不同的意义模式,他们表达意义的方式逐渐负载了附加于他们身上的社会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居民常常对自身环境中的语言变体态度鲜明。他们明确区分唯一可接受的变体(“标准体”)与其它不可接受的变体(“非标准体”或“方言”)。但是因为他们不能系统地描述这些方言变体,他们从大量的“不标准的”语音、语法特征中挑选出一些特征,作为鲜明的社会态度和评判的靶子。在英国以及古罗马,“遗失h音”(在词首位置省去h音)作为不可接受的言语形式被凸显。在纽约,不可接受的则是省去词末元音后的r音(在英国,不加r音则是“标准”发音,加上r音反而是“不标准”发音)。在黑人土语中也有一些语音和形态特征被单独挑出来,作为这个英语变体的特征。
几十年来,以及接下来的几十年,语言学家毫无疑问仍将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言语形式或任何一种方言从语言本身角度而言,优于其它语言形式。方言的优劣之分不在于语言作为系统,而在于语言作为机构,即语言作为社会结构的载体和象征。所谓“标准语言”的概念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指的是某个方言的社会地位,以及它所实现的功能范围,而不是指方言本身的任何语言要素。那么为什么人们对方言抱有根深蒂固的态度?为什么许多城市居民如此强烈谴责某些“欠标准”的语言形式?
答案似乎是这样的。虽然人们对方言的态度表面上与显而易见的语言特征(如发音、词汇形式)相关,但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缘由。人们谴责某些方言是因为他人表达意义的方式不同,他们感觉受到威胁。并不是不喜欢某些发音这样的简单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这些语言形式让人讨厌),而是担心不同的意义表达方式。因此问题不在于不同的元音系统,而在于不同的价值系统。如果我讨厌某个人的元音发音或者句子结构,通常打着美学的(“很难听”)或语用的(“听不懂”)的幌子,或者两者皆有。我确实这样觉得。但是我真正反对的是这些语言特征的象征意义。作为语言象征,它们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直接作为社会结构的标记(如同胡须或衣着),另一方面,间接地作为说话者建构自己次文化身份的意义实现方式。
语言只是人们表征社会系统内在意义的方式之一。社会系统内在意义一方面由人们的行走方式、饮食习惯及其他的行为模式表征(直接地表达),另一方面由人们分类物体的方式、确立的规则,以及其它思想模式表征(隐喻地表达)。语言则既直接又隐喻地“表征”。语言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它同时给我们的经验现实以及人际关系编码。语言连接我们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即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语言使得两个环境互为隐喻。每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社会观。这些不同的模式相互竞争,在拥挤的城市中贴身肉搏,很容易被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因此我认为,许多城市儿童学习说话时,他们学的是如何表达意义,但他们的意义表达方式与既定的社会规范不兼容。要是这些社会规范没有体现在学校教育的原则和实践中,这本不成问题。但现实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教育失败或者教育抵制。教育失败的问题不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语言问题指的是不同都市方言的问题,但是一些方言因素,尤其是对方言的态度,将问题复杂化了),教育失败本质上是(社会)符号的问题,与我们构建社会现实的不同方式有关,也与社会现实各方面的不同意义表达类型有关。我所说的意义,即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配置的语义资源,可能与你所说的意义不一样,也可能与你对我的意义的期望不一样。这就可能导致你我沟通不足,令人困惑。
从“言语社区”的经典意义上来说,城市并不是一个言语社区。显然城市居民并不全部相互交流。他们说话方式不一样,表达的意义也不一样。但是城市是意义交换的场所。在交换过程中,冲突发生了。虽是象征性的冲突,但是与经济利益冲突一样真实,这些冲突包含了变化机制,让语言学家高兴的是,他们发现冲突中包含一些语言变化的机制,因此研究冲突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语言历史的新看法,以及关于文化变迁本质(我们每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为自己构建的现实的变迁)的新观点。通常城市居民的宇宙观并不是有序和恒常的。但是他的宇宙观至少有,或者如果允许的话可能有,一个重要的补偿性质:许多截然不同的群体共同塑造了这个宇宙观。
注释:
[1] 元音裂变指的是一个元音裂变为双元音或三元音,译者注。
[2] 见法国作家罗歇·瓦扬的小说The Law (《法律》),书中阶级地位高的人可以为其他人“制定法律”——译者注。
[3] 即“在发音、语法和词汇方面”——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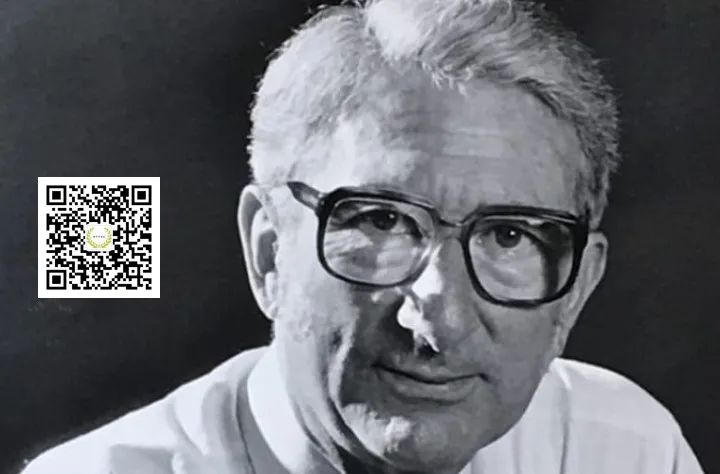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