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作战。直到战国时秦国逐渐一家独大,纵横家们提出了“合纵连横”的主张。从此,合纵连横成为战国时代的典型标志,但其本质仍是诸侯间的结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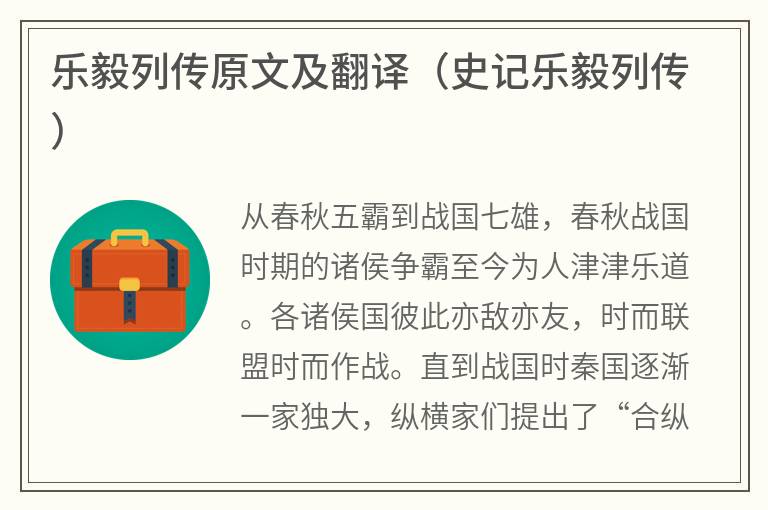
乐毅列传原文及翻译(史记乐毅列传)
所以问题来了,本来就是诸侯争霸,无论是远攻近交还是远交近攻,无非都是结盟与制衡,为何又会出现“合纵连横”的叫法?它与普通的诸侯结盟又有什么区别?
“合纵连横”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是西汉才出现的。
严安上汉武帝书云:“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纵连横,驰车击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因“从”“纵”相通,“横”“衡”相通,所以“合纵连横”也写作“合从连衡”或“合从连横”。
学者指出,“从”“衡”才是本字。秦汉之前,“合纵连横”也确实用“从”“衡”来表示。
韩非子说:
不过,这个定义并不准确,我们来看两个事例:
第一个是公元前318年,楚、魏、韩、赵、燕五国合纵攻秦,楚怀王为“从长”(《史记·楚世家》),当时秦、楚是强国,魏虽然衰落,但仍强于韩、赵、燕三国,所以这场合纵战争是一个强国率一批中小国家进攻另一个强国;
第二个是公元前288年,秦、齐、韩、魏、燕五国曾打算连横攻赵,《战国策·赵策一》称:“五国之王,尝合横而谋伐赵,参(即“叁”)分赵国壤地。”当时秦、齐是东西两强,燕、赵次之,韩、魏最弱,所以这场连横战争是两个强国率一批中小国家攻打另一个强国。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韩非子的话并不能准确概括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情况。但韩非子就生活在战国末年,他的定义肯定适用于当时合纵连横的情况。战国晚期,秦国一强独大,其他诸国相对而言是“众弱”。那么,韩非子的话就可以理解为:诸侯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叫做合纵,一国联合强秦攻打其他诸侯叫做连横。
韩非子塑像
战国晚期的这种合纵连横模式对后人有着深远影响。《过秦论》作者贾谊、《史记》作者司马迁、《战国策》编订者刘向、为《战国策》作注的高诱等都认为合纵是诸侯联合攻秦,连横则是与强秦结盟。
但是翻阅文献,我们会发现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如《战国策·赵策四》说:“赵使赵庄合从,欲伐齐。”《史记·乐毅列传》说:“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就是说合纵还可以伐齐,合纵连横在更早肯定还有其他含义。
合纵连横最初的意义要从其产生的时间来分析。西汉刘向在《战国策序》中指出:“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苏)代、(苏)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
其中公孙衍、张仪时代最早,徐中舒《先秦史论稿》、杨宽《战国史》、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等也都将公孙衍、张仪在列国政坛的一系列活动作为合纵连横时代的开始。
公孙衍、张仪都是魏国人。公孙衍早年任秦相,后长期在魏国任职,多次组织合纵攻秦,曾“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史记·张仪列传》);张仪长期担任秦相,一度兼任魏相、楚相,曾推行秦、魏连横,秦、韩、魏连横,秦、楚连横等策略。不难看出,两人的外交活动都是以“秦——魏”为坐标中心。三国时期的学者孟康从地理角度对二人的外交策略进行解释:“南北为‘从’,东西为‘横’。”(《史记·周本纪》集解)
就是说,秦国联合东方的一国或多国,属于东西方向的合作,叫连横;南北方向的魏、韩、赵、楚、燕等国联合起来叫合纵。
合纵连横策略的内涵和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改变,但“南北为纵,东西为横”的含义则被继承,如秦末项羽等反秦力量叫合纵,西汉七国之乱时吴、楚也叫合纵,他们都是南北方向上的诸多势力联合在一起去进攻一个位于西方的强大政权。
合纵连横示意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大体上可以了解合纵连横含义的演变:
连横,最初是秦国为了开疆拓土而采取的外交策略,开创者是张仪,连横拉拢的国家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在地图上看,这个联盟呈东西走向。
合纵,最初是魏国为了对抗秦国而联合南北方向各国的策略,参与国家一般在三个以上,开创者是公孙衍;后来齐国一度强大,于是攻齐也叫合纵。
战国晚期,诸侯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叫做合纵,诸侯中的一国或多国联合强秦攻打其他诸侯叫做连横。汉代之后,合纵连横逐渐泛指外交谋略,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王凤说“《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书·宣元六王传》),都是这个含义。
战国形势图
战国中晚期,人们将包括合纵连横在内的各种外交斗争模式都归为“外事”。策士曾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合纵连横是春秋和战国早期外交策略的延续,它继承了许多诸侯结盟的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呈现出大争之世的世道人心。
首先,合纵连横是策士积极参与的结果。春秋时代和战国早期,诸侯的外交决策是由各国君主和执政共同作出的,而合纵连横时代多了策士这个群体,他们会积极参与到各国外交决策中,使各国外交决策多了一种“外力”,而这种“外力”有时甚至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公孙衍影视形象
典型的表现就是策士往往以他国势力代表的身份出任所在国的宰相等高官。如“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能出任魏国宰相是因为他背后代表着秦国势力,魏国的这一做法也是向秦国表明魏国将坚定地站在秦国一边。作为魏国宰相,张仪要参与魏国内外事务的决策,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监督魏国的外交政策。
再如公孙衍,他为了巩固魏、齐、韩联盟,在与齐国宰相田婴缔结盟约后,由田婴之子田文出任魏国宰相,公孙衍则出任韩国宰相。
自张仪、公孙衍开启携一国之重出任他国高官的模式后,这一做法随即普遍展开:公元前308年,秦国重臣樗里疾出任韩相;公元前299年,齐国重臣田文出任秦相;公元前298年,赵国重臣楼缓出任秦相;公元前281年,秦国重臣魏冉出任赵相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重臣也可以视为一国派往另一国的人质。在春秋战国时代,除了太子、诸公子外,朝廷重臣也可以作为人质。公元前610年,晋国不满郑国对楚国示好的行为,于是郑国派太子夷、大臣石楚到晋国做人质;战国中期,魏大臣庞恭曾和太子一同到赵国做人质。还有大臣单独做人质的,如公元前589年,宋国与楚国讲和,宋国将执政大臣华元送到楚国当人质;战国中期,魏国与齐国结盟共同对抗楚国,魏国将大臣董庆送到齐国当人质。
合纵连横时代,这些重臣在他国虽然位列宰辅,但生死却仍握在他国君王手里。齐国孟尝君相秦时就差点被秦昭王所杀,靠鸡鸣狗盗之徒才逃出生天。
张仪影视形象
有时为了保证联盟的巩固,策士们会同时担任多国宰相。公孙衍曾“佩五国之相印”(《史记·张仪列传》),张仪“并相秦、魏”(《战国策·魏策一》),乐毅以燕将兼任赵相(《史记·乐毅列传》),周最曾打算“兼相韩、魏”(《战国策·东周策》),赵献曾打算“并相楚、韩”(《战国策·魏策一》),苏秦在燕、齐、赵同时拥有封地和官职,等等。这些外交现象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后世也极少发生。
其次,合纵连横诸国讲求“权”和“变”。“权”指影响力,“变”指外交方针和结盟对象的改变。“权”分轻、重,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策士分析当时形势:“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战国策·齐策三》)
翻开《战国策》,我们会发现大量关于“权”之轻重的讨论。各国会对加入哪个联盟仔细斟酌,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苏秦为燕昭王分析燕国外交地位时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秦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战国策·燕策一》)
所以苏秦给燕国制定的外交策略是将齐国作为主要盟国,同时也和赵国保持良好关系,让齐、赵相互牵制。五年之间,“齐数出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合一离,燕王不与齐谋赵,则与赵谋齐”(《战国策·燕策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权”必然意味着“变”,所以,各国朝秦暮楚,秦昭襄王就曾痛斥韩国“不固信盟,唯便是从”(《战国策·赵策一》)”。
苏秦影视形象
再次,合纵连横既要组建自己的联盟,又要拆散别人的联盟。主张合纵者想离散连横,主张连横者想离散合纵。
贾谊《过秦论》说孟尝君、春申君等“约从离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以伐秦,“离衡”就是拆散连横。
公元前288年,秦国欲联合齐、燕、韩、魏共同伐赵,打算瓜分赵国。策士苏秦作为燕国谋臣,认为国力相对弱小的燕国必须让齐、赵这两个强邻相互制衡,才能求得生存。于是苏秦先是说服齐国改变策略,变伐赵为伐秦;而后又在齐、赵的支持下说服韩、魏,彻底瓦解了连横。
公元前287年,在苏秦的策划下,赵、齐、魏、韩、燕五国合纵伐秦。这是合纵者拆散连横的经典事例,还有很多连横者拆散合纵的事,如公元前283年秦攻魏,赵、燕救魏,反将秦军困住,秦国被迫求和。第二年,秦国拆散了赵、燕、魏联盟,将魏国拉拢到了自己一方。而后出兵攻赵,占领两城。
总之,合纵连横从战国中晚期一种特殊的外交现象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我们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实力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
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合纵连横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资料: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杨宽《战国史》
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