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代乾嘉考据学家王鸣盛的考史著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主,但其中也穿插一些史论内容。

或先考证史实,然后对其议论;或直接议论历史人物和评论历史事迹;或以述代论,因此构成了《十七史商榷》“史”、“论”兼俱的特色。
其中,评骘各家书法义例和品评历史人物是其重点。本文拟对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的特点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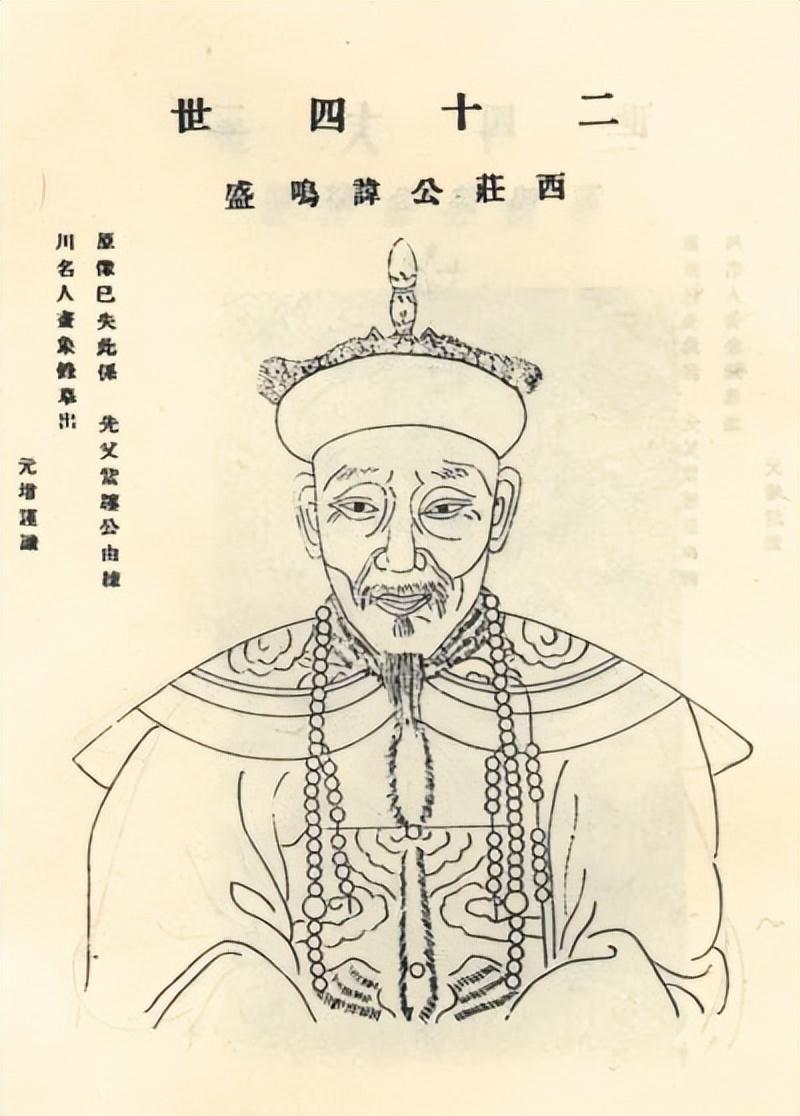
一、注重道德品评,褒贬鲜明
王鸣盛指出:“若无史书,小人更何所惮哉?有史在,恶人多福者,其恶千载炳然不灭矣。”强调了史学所具有的见证善恶、彰善贬恶的“明体致用”的功能。
王鸣盛在考证史事、评论人物时,特别注意彰忠贞、贬失节、斥逆谋,以明人伦、正风俗,人物品评折射出王鸣盛在道德上的价值取向。

(一)抵斥“无德小人”
在王鸣盛眼中属于“无德小人”的有这样几类:不讲信义、倾危之人;得意忘形、无德之人;作秀、虚伪之人;善阿谀、无气节之人;嗜杀、残忍之人等。
对这等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皆为他们贴上“无德小人”的标签,并在评论时作出具体划分。

王鸣盛极为反感不讲信义、倾危之人。所谓倾危之人主要是指那些反复无常、背信弃义之流。
王鸣盛大肆讥讽作秀、虚伪之人。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这些人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所用语言极尽讥讽。

如《为羽发哀》篇中评论刘邦在项羽自刎后的所作所为:“以鲁公葬,为发哀,泣之而去。天下岂有杀之即我葬之者,不知何处办此一幅急泪,千载下读之笑来”。
王鸣盛无情鞭挞善阿谀、无气节之人。重气节、疾阿谀是王鸣盛对历史人物道德品评价值取向的又一着眼点。

王鸣盛指出:南朝宋人王俭虽“自幼年笃学,手不释卷”,但“专以学术为佞谀之资。华林宴集,跪齐高帝前诵相如封禅书,其谄弥甚,殆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是“真小人”。
五代时期冯道“历事刘守光及唐、晋、汉、周”,毫无气节,却还要自我标榜“齿德位望兼优”,“明目张胆言之,真觉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实在是“令人呕秽”。

王鸣盛对臣仕多朝,还要自感德高望重,很是鄙夷。王鸣盛极端痛恨嗜杀、残忍之人。
在王鸣盛看来,如果自身作恶,即使一心向佛也于事无补,体现出他不信天命的唯物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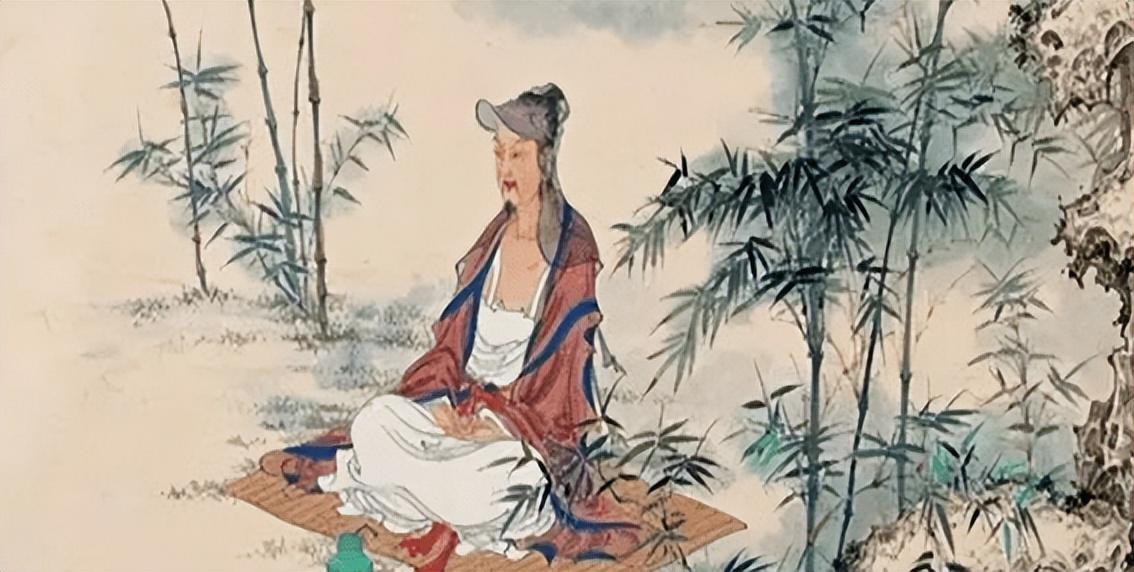
(二)颂扬忠义、守节之人
王鸣盛非常赞赏范晔,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范晔所著《后汉记》,重视对忠义、守节方面内容的记载。
列有“党锢、独行、逸民等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

王鸣盛以此提醒人们要以作品来推知范晔人品:“善读书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
王鸣盛在评价人物时,特别彰显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美德。如专列一条评说山涛之忠诚。
山涛即使在遭受委屈、误解的情况时,仍能对朋友不离不弃、在危难之时能伸出援手,王鸣盛对这样的忠义之举大加赞赏,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真君子。

“山涛掌选,举嵇康自代,康与书绝交,诋斥难堪,而其后康被刑,谓其子绍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后涛举绍为秘书丞。以康之诡激,而涛能始终之,何友谊之笃也,君子哉!”
王鸣盛在人性道德价值取向上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的。王鸣盛不以胜败论英雄,而是以气节和品德来评判人物,这在对刘邦和项羽的评价上最具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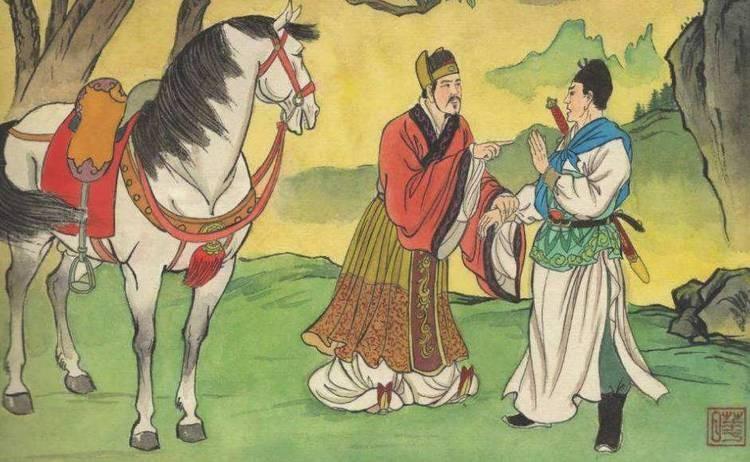
在王氏眼中,贵为皇帝的刘邦仍不改其“亡赖”本性,是“惟利是视,顽钝无耻”的小人;而项羽则不然,始终浩气凛然,虽败犹荣。
王鸣盛充分肯定了项羽亡秦的巨大功绩,认为“当日若非羽破秦兵于巨鹿,虏王离,杀涉间,使章邯震恐乞降,沛公安能入关乎?”刘邦实“借项之力以成事,而反噬项者也”。

通过对刘邦贪鄙市井之气的揭露和项羽凛然浩气的彰扬,使人感觉刘邦虽胜,但胜之不武;而项羽,虽败犹容。王鸣盛实际上是在对豪迈之气和高尚人格进行颂扬。
二、不以成败论英雄,突出个人作用
王鸣盛重视人才,强调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在历史转折关头,英雄人物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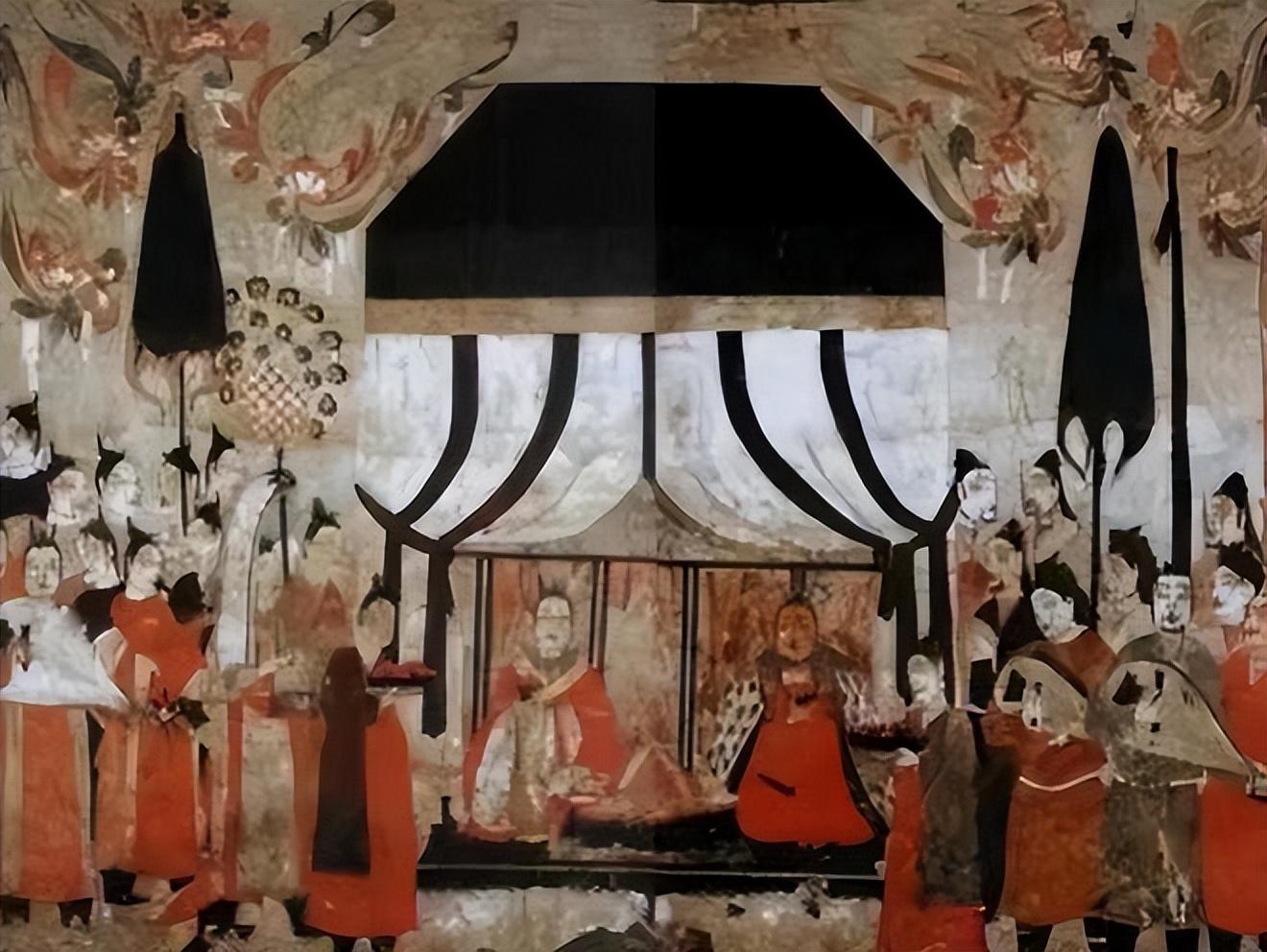
三国时蜀国存在时间较短,后人对此有过诸多分析,但王鸣盛指出了别人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蜀国人才过早凋零是蜀国短命的关键。
关羽中年丧命,“张(飞)少于关数岁,其死年未必老,固可恨。而诸葛(亮)年亦仅五十四,马超四十七,庞统三十六,法正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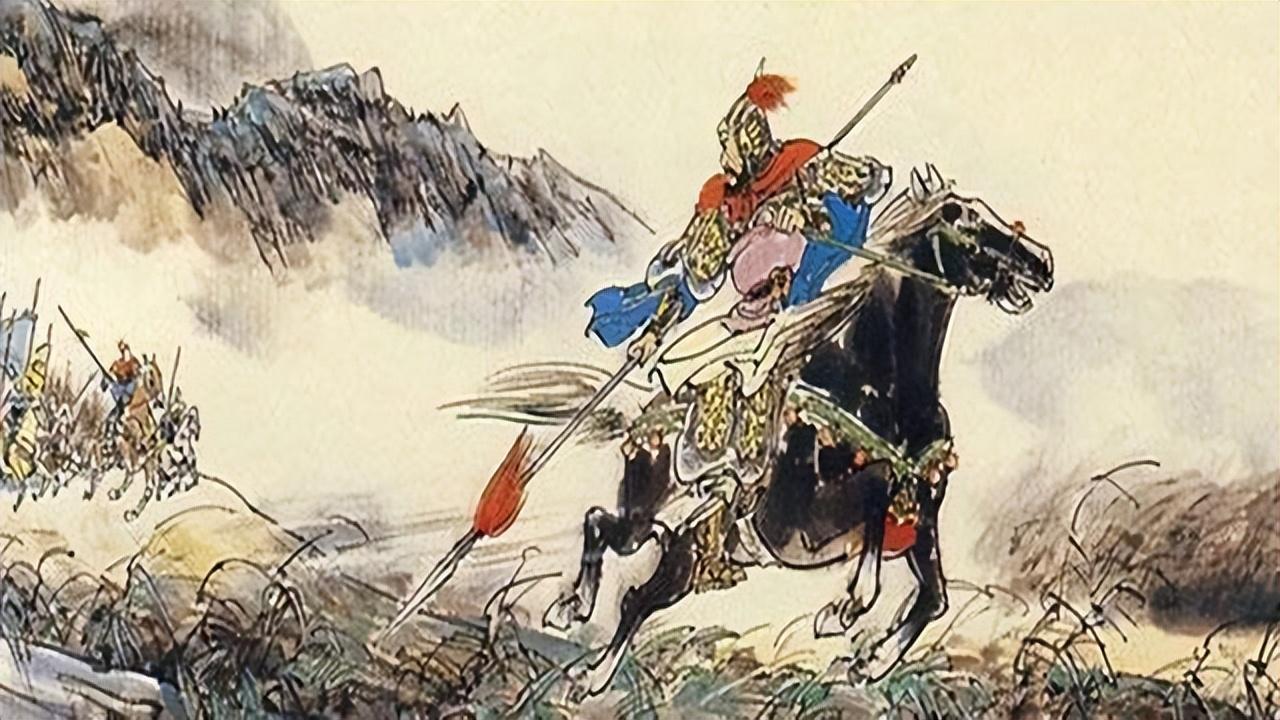
《黄忠传》言其勇毅冠之军,而名望不高,则年亦必尚未老,乃先主为汉中王之明年遽卒。
赵云卒于建兴七年,其年想亦不过五十余。惟空虚无实之许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废汉,人不能兴之矣。”
王鸣盛还认为东晋的灭亡也与东晋人才早逝有关,他指出在谢安、谢玄、谢石相继去世后:“自此晋无人矣。桓玄篡位,刘裕讨玄,而晋亡矣。”

王鸣盛认为个人的失误也会影响大局甚至国家的安危。东晋何充荐举桓温,几致东晋政权易手,何充实是东晋衰微的罪魁:“举西夏而委之桓温,如虎傅翼,成其跋扈,晋祚几倾。”
把个别人的思想动机、杰出人物的主观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否认社会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显然是不对的,历史人物所发挥的作用,最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
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杰出人物的作用,是构成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合力”中的一股,必须对此有所揭示。
这不仅有利于对朝代兴衰原因进行具体而深刻地分析,而且对后学发散性思维的开发也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三、不囿成见,敢发前人之覆
王鸣盛评价人物不依成见,而是根据事实进行客观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发前人之覆。
卫青是西汉抗击匈奴名将,战功赫赫,一直以来,史家对其褒扬有加,但王鸣盛却认为卫青是“用兵制胜皆竭民力以成功”,不值得大书特书。

王鸣盛不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四杰”的大逆不道和不识时务,而是推重他们的学识和气节。
对以“安享爵禄”、以官位高低为价值标准来评判人物的做法进行强烈抨击,认为这些人“可鄙甚矣”。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也只有像王鸣盛这样的有史识、真率的性情中人才会说出这样具有叛逆色彩的话语。

王鸣盛在透视了这段历史后,发前人之覆,指出王叔文的革新措施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改革职弊,加惠穷民”。
不赞同司马光对王叔文“欲夺兵权以自固”的指责,他指出:由于宦官掌握兵权,造成“威柄下迁,政在宦人”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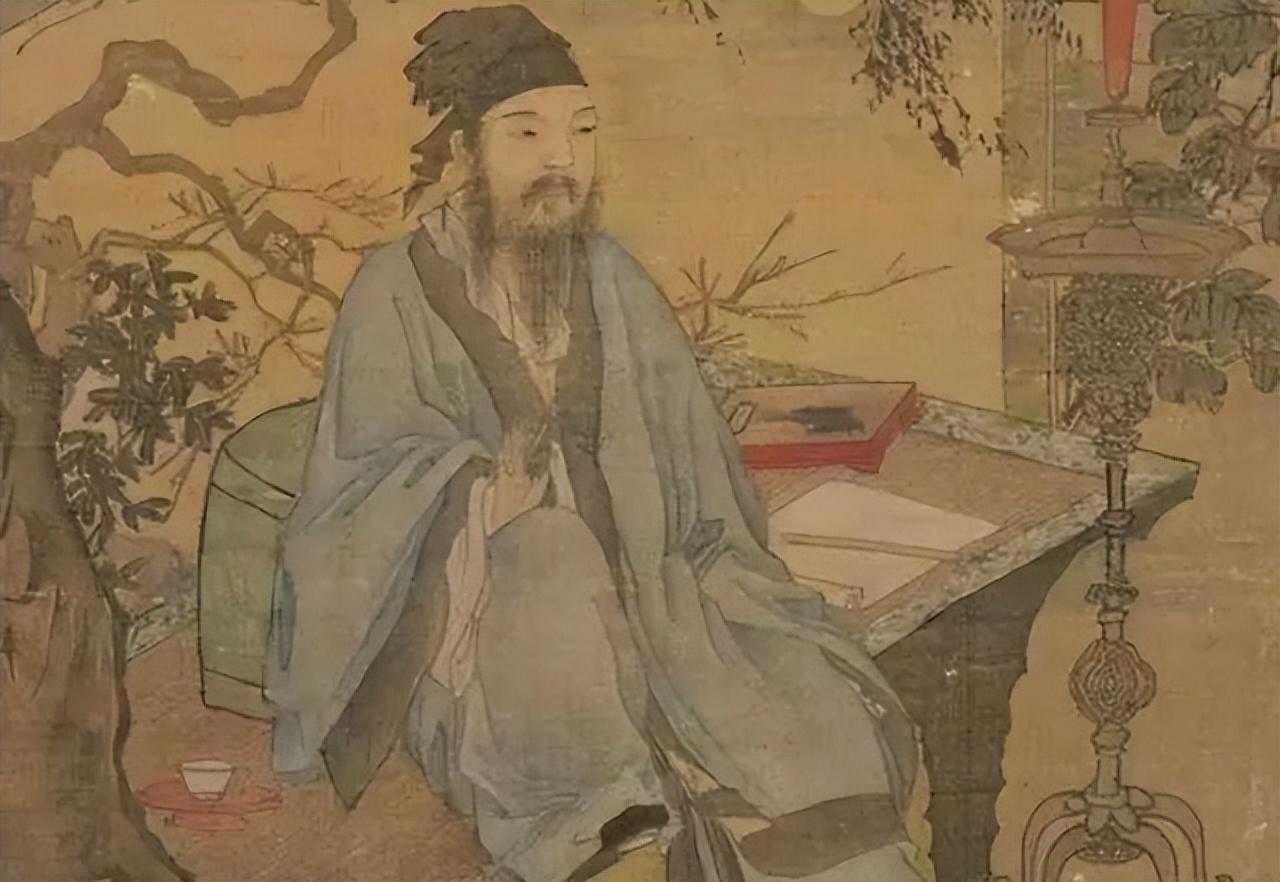
王叔文谋夺兵权,在于稳固国家统治,不但不应贬抑,而且应该褒扬,此举是忠于唐室、忠于国家的行为。
王叔文任用范希朝等人,也不是“朋党专恣”,而是“举贤为国,可谓忠矣”。
他的结论是:“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清人李慈铭赞同王鸣盛的这一看法,称“此论千古巨眼”。

四、多视角分析行为背景,议论深刻
王鸣盛评价历史人物,重视对人物行为背景的综合分析,不仅分析个人心理动机,而且对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加以剖析。
对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深层剖析,且具有浓郁的辩证意味。王鸣盛对秦国范睢谗杀大将白起这一行为的动机分析是“为一身富贵计而不为人主计”。

王鸣盛对孙权没有多少好感,原因是孙权“反复倾危,惟利是视,用柔胜刚,阴谋狡猾”。
王鸣盛对陈霸先害王僧辩一事的动机分析,也入情入理:“乍观之似若发于忠义者”,实则是因为王僧辩妨碍其篡夺政权:“篡梁所忌者,惟僧辩故也”。

虽重视人物道德品评,但并不拘泥于封建正统道德观念。王鸣盛虽憎恶仕任多朝却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但对仕任多朝的魏征却能给予公允评价。
“魏征始事元宝,继事李密,降唐高祖,又仕窦建德,复归隐太子,终事太宗,更六主矣。然夫子许管仲以仁,则征可以此例。生当乱世,不得不尔,功足晚盖,可无苛责矣。”

他没有以“俗儒”、“忠臣”等空泛的道德标准来指责魏征,而是站在当时的历史坐标上为当事者切身设想,根据实际业绩做出评价。
显示了其务实态度,也说明了他论史考时势、理性地评判人和事,不夸言,不作态,不仅能够对历史作出正确认识,而且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片面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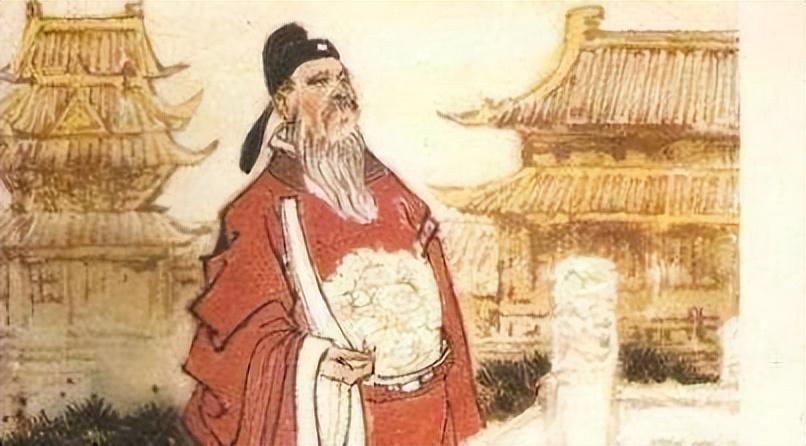
特别注意分析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对人的影响。通过对东、西汉和宋唐义士多寡的分析说明了世风和社会心理对人的影响。
同样,王鸣盛认为良好品格的形成也与家世渊源密切关联:“宋有袁粲,梁有韦粲,二粲忠义,千古流芳,以六朝之浮薄而疾风劲草,未尝无人,血性激发,非由学问。

袁粲、袁淑之兄子,而淑本忠臣;韦粲、韦睿之孙,而睿实梁之名将也,渊源有自。”体现出王鸣盛在历史评价中对历史主义地评价历史原则的运用。

五、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
王鸣盛为人自负、率真、磊落。在他给钱大昕所写的诗文中,称“牛耳平生互相持,江东无我独卿驰”。
这种性格对其学术的自信产生一定影响,使其敢于表达一般学人所不能言和不敢言的论史卓识。
也正因为王鸣盛自负、率真、坦荡,在评论时往往直抒胸臆,用语苛刻,因此招致非议。

王鸣盛虽时有过激之辞,但皆言之有据,他所指责对象,皆有可指责之处,只是王鸣盛在批评用语上太过激烈、率直。
王鸣盛并没有一味地指责,一旦发现了被批评者身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他又会大加称赞,“恶而知其美”,这一点在对李延寿的评价上表现最为突出。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李延寿的批评最多,但对其长处也有肯定。如南朝宋文帝为太子劭所杀,《南史·宋文帝本纪》直书“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

结语
王鸣盛的评论能做到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得失兼指,是非皆评,不因是掩非,也不因非隐是。
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在骂人,也要看到他经常表扬人,如他赞扬“近儒史学惟万斯同季野善于稽核,识见独精”;“阎氏若璩辟伪古文尚书最精”,等等。
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好坏互不相涉,得失兼指,是非皆评,是王鸣盛品评历史人物所持的态度。
参考文献
《十七史商榷》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