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名
——对社会价值观的一个观察
文 ·何怀宏
对权力、金钱、名望的追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不作褒贬评判,只是试图描述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从过去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今天的社会是价值多元社会。但如果从事实的角度评判,是不是仍存在一种主导的价值趋势呢?它追求的是什么?
权、钱、名
首先说权力。这里所说的权力是明确的政治权力,例如担任政府官员,和福科所说的广义的、隐蔽的权力不同。人为什么追求权力?有没有把权力作为本身目的来追求的?有的。但也有人并不是将权力作为自在目的,而是作为手段。比如试图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取成就感;也可以作为索取财富和名望的手段。一些人花钱买官,就是看到了权力背后的财富回报。
金钱有一种底线的性质。完全没有金钱就没有办法生存。而往高处看,物质的欲望又是无限的。因此,金钱几乎被所有人追求但又不像政治权力那么稀缺。社会中可以有大量富人,甚至一个很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权力几乎永远是金字塔型,塔尖是稀缺的。
名望比较复杂,它不像权力、金钱那么实在,有些时候看不见、摸不着,忽起忽落。但有的名望比较持久。名望似乎是最有可能把物质和精神、有形和无形结合在一起的。名声其实存在于他人当中。知道你的人越多,你越有名望。名望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存在。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强调一种文化的名望,因为文化名望曾经在制度结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权力也好、名望也好,都比金钱更引人注目,但也有它们的限度。权力的本性会很容易有一种侵夺性或僭越性。因为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管理其他资源的,因此很容易把其他东西也据为己有,都纳入权力的范围。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权力的本性是扩张的,因此不得不经常使用一些外在的也是同样强硬的东西来限制它。尤其最高的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它同时也就是最大的财富和名望。在集权主义的社会中,最高权力者同时也是最大财富和最高名望的拥有者。
文化的名望会更持久。历史上多少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消失了,但人们还记得贝多芬和孔子。他们在所处的社会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和财富。所以有时候,文化比政治更长久。
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权、钱、名
权、钱、名都是社会价值观,也是社会资源,因此必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去讨论三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社会资源的追求受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在一个时代和一种社会制度中,人们追求什么是由这个社会提供的条件和可能性决定的。所以,不妨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来讨论权、钱、名的关系。
春秋以前基本是世袭社会,原则是“血而优则仕”。高位官职基本是由一些大家族垄断的,当然会有此起彼落,有些家族消失了,另一些家族慢慢兴起了,但基本上都是世袭的结构。到了选举社会,原则变成了“学而优则仕”。至少从唐以后,唐宋元明清都是科举,通过考试来选举官员。
划分世袭和选举社会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权、钱、名。这里的名望主要是指文化名望。社会分层的结构是由权、钱、名的分配规定的一个人要升职就要通过察举、科举制度。
这样造就了一个书卷气很浓的社会。从世袭社会到选举社会,获取权力的途径变了,但不变的事实是,政治总是占据关键地位,必须担任官职才能得到财富。所以中国最长久的政治现象就是官本位。但改变之处在于,血统是先天不可改变的,学则是后天可以努力获得的,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都是如此。
察举主要是地方长官从当地一些有名的人中,推荐几个人到朝廷去做官。推荐的依据就是名望。一是德行,一是才学。科举阶段不直接根据名望推荐,首先通过考试证明文化能力,金榜题名之后,获得文化名望才有任官资格。
当时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本位,但文化名望是获取权力的首要途径。中国人最重视权力和名望,使社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社会。权力占优的社会并不少见,但像中国这样名望占优,在其他文明中是很少见的。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斯巴达社会。它把财富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甚至排斥财富而重视武士的荣誉。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提到了这样的社会。他希望是一个统治阶层的共产制,这个共产制不是全社会的,只在武士阶层实行。一旦进入武士阶层,进入社会统治阶层就可以获得权力和名望,但不能有个人财产。试想,如果今天推行这个制度,告诉大家“欢迎来当官,你可以有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名望,但将失去个人财产”,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考公务员了?
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权民社会”一方面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遇到了困境—经济实力下降。这在近代与西方相比就很明显了。古代中国人从来就不缺技术发明的能力,但为什么两千多年来技不如人、器不如人?这与价值追求太有关系了,也就是中国人“志不在此”。科举变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让中国的国力和财富明显受到了影响。
1905年废除科举制,文化土崩瓦解,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这时文化名望衰落了。而经济的实力在近三十年迅速崛起,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权钱社会“。从价值追求来说,这两者变成了最主要社会价值,权力也是以经济为中心,意味着整个社会国家的价值目标集中于此。对于个人而言,过去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现在则有多种多样的机会。
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从社会趋势来说,权、钱、名还是应该相对分流,各得其所。过去的关系可能过于紧密,比如说权钱交易。为什么茅于轼提出,不要让有钱的人有权,也不要让有权的人有钱?这就是要在权钱之间产生一些分割。在美国,亿万富翁几乎不可能竞选上总统。洛克菲勒对政治也有兴趣,但很难在政治上有所发展。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文化是文化,不要搅得太紧密了。比如说,政府太重视哲学,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的观点是不能太重视。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不是更好吗?
权、钱、名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各有各的领域。不要一有了权力,就什么能力都具备了。布什、里根要在大学里得到名誉博士是很难的,经常被拒绝;中国的很多官员退休后马上到大学里当教授、院长,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分流的关键是慢慢弱化或者消解官本位。关键的手段还是权力的制衡,要使这个社会各得其所,各尽所能。
影响社会结构的权、钱、名的分配,主要是指高端的分配,是影响社会统治阶层再生产的那种分配。但这种高端的权的分配应该不影响所有人的基本权利,钱的分配不应该影响所有人基本的生计;甚至还应该让人都过能体面地生活。名望也是如此,名望是稀缺资源,但它不应该影响到对所有人的普遍承认,人之为人的一种承认、尊重,这是基本的。此外,在价值方面,我们希望不光是权、钱、名,还要有更广泛的、超出于此的其他价值追求,比如说精神和信仰,都应该有恰如其分的地位。
何怀宏:脆弱的良心和坚固的伦理底线
文·朴抱一
《中欧商业评论》(简称CBR):我们知道您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是《良心论》。我们这个时代,良心时时受到挑战,但整个社会又在呼唤良心。什么是良心?良心有什么用处?
何怀宏:良心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良心是人性中最脆弱也是最坚固的东西。就像何光沪先生说的“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防线。平时微弱,在最危险的时候它会变得强大。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称之为“存在我们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旁观者”让你做一些事情会不安,做另外一些事情很安心,这也是良心。良心对每个人是不同的,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人到了晚年,尤其碰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会想起我自己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就会“良心发现”。所以孟子说,良心会放逸,要把良心找回来。
CBR: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一些感情都有相对应的生理基础。良心有相对应的生理基础吗?或者说良心在哪里?
何怀宏:确实有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同情心、恻隐之心与人类大脑的某个区域是有联系的,但良心归根结底还是不能从生理学上去解释。因为这要复杂得多,人类的思想意识来自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CBR:您在《良心论》中提出要建构一种现代人的个体伦理,这是指的什么?
何怀宏: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底线伦理。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发表了《新民说》,希望建立起一种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良心论》也是承续了梁启超先生的学脉。我期盼一个具有合理底线和稳定常理的时代尽快到来。
CBR:这种底线伦理,与传统内圣外王的圣王之道有何区别?
何怀宏:过去讲圣王之道,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伦理,不是针对所有人的。现代伦理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底线伦理,所有人都应该适用。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常轨。”底线伦理强调的是底线或者基本义务。现在是平等社会,伦理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我们不否认崇高,但应该从底线伦理走向崇高。
CBR:构建当代中国个人伦理的构架是什么?经纬坐标在哪里?
何怀宏:它的起点是恻隐之心或者同理心,也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建构就是要从传统的、以关系为主的伦理过渡到以规则为主的伦理。恻隐、仁爱是起点,忠恕、诚信为基本义务,通过敬义明理来建设一种普遍的道德规则。 “生生”是社会根据,“为为“则是指应积极有为,且为所当为。
CBR:您从同情心出发讨论个人伦理。这让我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是从同情出发的。
何怀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而《道德情操论》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他的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的基础。《国富论》认为个人的自利心是推动公益的看不见的手。《道德情操论》则主张一种看得见的手,就是个人的道德努力,从人的同情心出发,努力促进公益,至少不去损害公益。
CBR: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传统价值资源的丧失和集体主义伦理的崩溃,很多人在终极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疲惫”和“无奈”。比如一些企业家觉得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再拼也没意思了。在这一点上,道德哲学能否有所启迪?在思考自己为什么活,如何去活的时候,这些知识资源能不能提供帮助和指引?
何怀宏:在这个时候要“养心”。要超越商业和专业本身,文化的、道德的、审美的、艺术的各种修养都要去养,去和其他领域的巨人对话。
知识是立竿见影的,养心是潜移默化。要排除和放下外在的纷扰,进入比较专注的世界。比如有些人通过抄写经书来体会深邃的东西,让自己静下来,入静。无论世界怎样纷扰,如孟子所说的,要求放心,让自己心安。圣王之道不通的时候,就要把底线巩固住。
CBR: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宗教改革所建构和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在中国,您提倡的一个面向现代的个人伦理的建构何时才能完成?
何怀宏:我个人认为,现代性的伦理建构是三千年文化传统和三十年社会变革交织的问题。三千年是从历史而来的古老的东西,与现代文明将结合成什么?我们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不放弃西方文明,尤其要注意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的伦理。政治和经济上有些事情是很紧迫的,必须马上去做,机会稍纵即逝;文化则急不得,也可能突飞猛进,但是还没到突破期,需要相当程度的酝酿。
CBR:如何维护社会道德底线?每天都看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被击穿。比如在婴儿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这种做法竟然在那么多的奶粉企业发生,成为潜规则。
何怀宏:道德底线不是一夜之间被击穿的,而是逐渐滑向深渊的。那些企业或者奶农刚开始添加的时候没有受到惩罚,就慢慢变成一个潜规则。这不仅是道德问题,同时是法律问题。不是道德的脆弱,而是法律的脆弱。如果法律的底线守住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就能守住,但法律也需要道德提供正当性基础,人要知道法律后面的道德理由是什么才能尊重法律。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道德问题要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不能惩治见死不救的人。前两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救老太太反而被法院判支付4万多块钱,这就是法律戕害了道德,会直接导致社会道德滑坡。
CBR:从您强调的底线伦理出发,您觉得现代中国的商业伦理应该如何构建?
何怀宏:商业伦理上,优先的是遵守道德规则,解决财富的正当性问题,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使用外部性的手段,伤害社会、员工、供应商等利益关联者。其次是境界的问题,怎样花钱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具有同情心,就可以运用理性,考虑如何去有效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或者支持公益事业。社会也应该提供这样的法律和机制上的保障,如捐助免税制度等,为社会道德提升提供一个向善的通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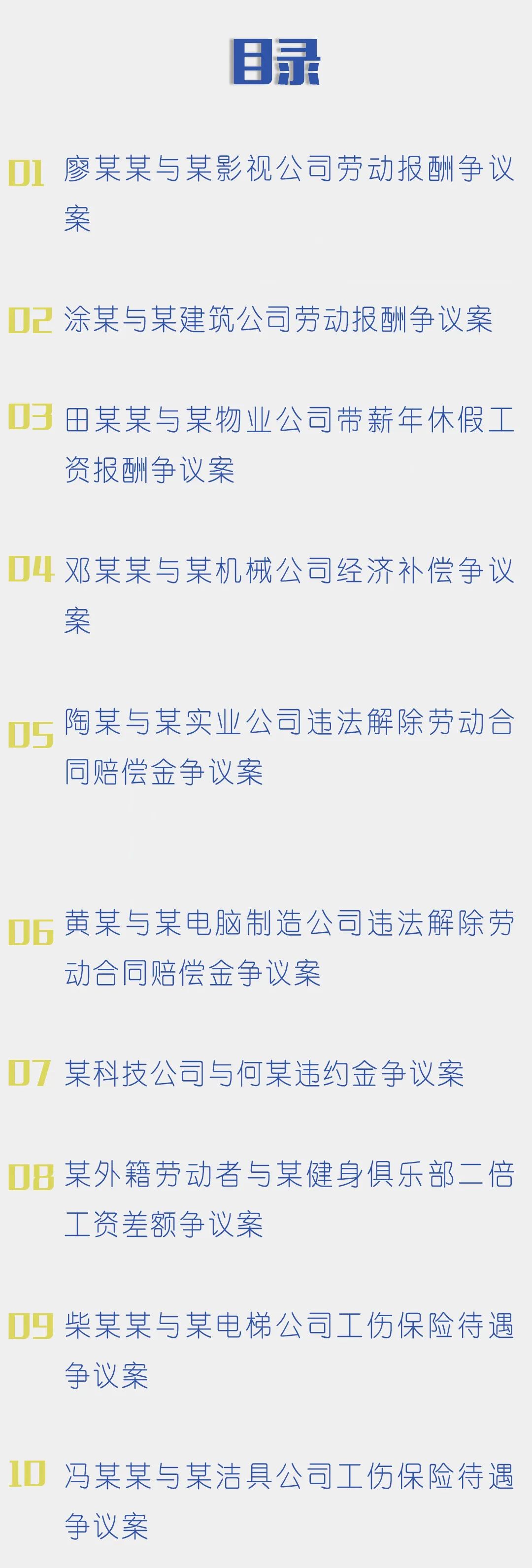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