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涵(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在明清史研究中,“明中叶”是一个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高频词汇,大约由此开始,中国的政治格局、国家制度、经济水平、社会文化均出现了剧烈的变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国内学者或专注明中叶变革中的积极因素,或专注其消极因素,鲜有人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首尔大学的吴金成教授是韩国明清史研究的权威学者,曾著《国法与社会惯行——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知识产业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国法与社会惯行》)一书,考察明中叶至清初一系列社会变革中的法律、制度、政策在现实社会的贯彻问题,探索明清变革中的积极与消极因素的内在联系。如今已由北京工业大学的崔荣根教授译成中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让国内不识韩文的学者能一睹其真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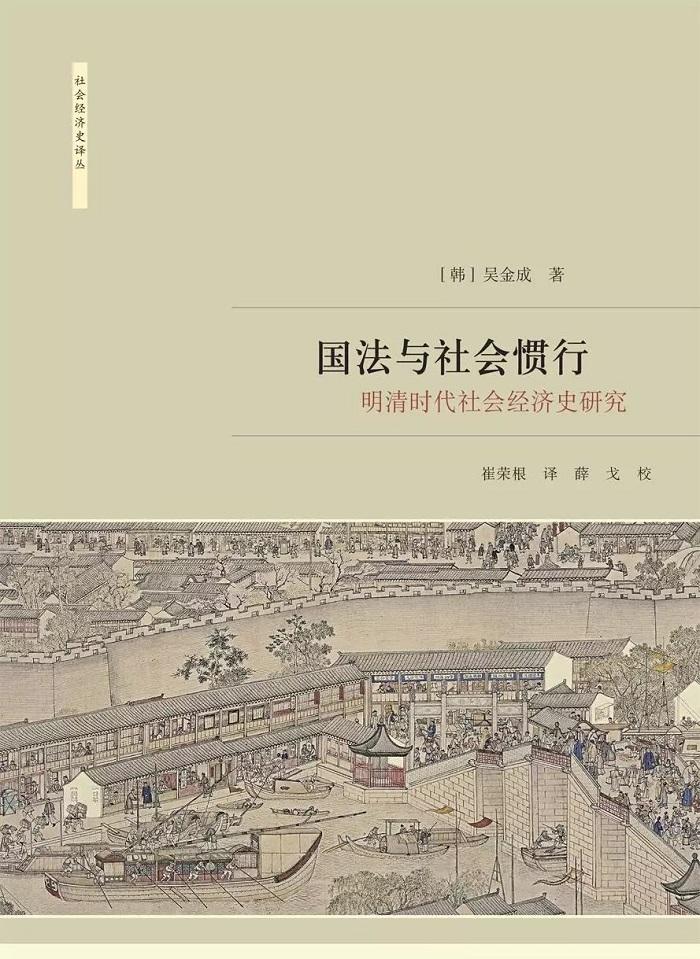
《国法与社会惯行: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韩]吴金成著,崔荣根译,薛戈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吴教授将著作定名为“国法与社会惯行”,似因他在研究中发现了明中叶以后的大量社会惯行与法律规定相背离的现象:国法规定限制士人优免,惯行却是士人优免泛滥;国法规定州县吏役供职年限为三五年,惯行却是州县吏役的数量庞大且世袭供职;国法规定鼓励儒学,惯行却是士庶沉于迷信。类似的现象不胜枚举,社会惯行与法律规定背向而行,置国法为具文。为此,本书试图厘清,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剧烈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绅士阶层以及围绕绅士周边的胥吏、商人、牙行、无赖等人群的各种功能。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吴教授使用了正史、政书、文集、方志等大量的史料,更是旁征博引了大量海内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包括中文、韩文、日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其所引用的文献足以媲美任何一套相关领域的文献目录书籍,对前人研究简明扼要地评述亦足以充当年轻学者研究的指导书。章节安排上,除了简要导论和结语,全书共三篇九章(含附论),每篇三章,分别讨论内容各异又彼此联系的三个主题——社会的动摇与重构、国家权力和绅士、都市和无赖,从不同角度论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化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在三篇内容中,第一篇“社会的动摇与重构”与后两篇略有不同,前者是后二篇的时代背景,由吴教授阅读大量研究后对明清社会经济变迁高屋建瓴式的论述及其早年研究的总结,后二篇则是爬梳史料所得的认知。对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大致情况,吴教授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明中叶里甲体制解体,绅士阶层填补了乡村地区的权力真空,经明晚期至清前期朝廷的反复努力,在绅士的配合下,建立新的赋役体制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二是从明中叶里甲制解体至清中叶,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持续向山区、落后地区和市镇迁徙,促进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吴教授对此着力最深,第一篇第二章、附论就此专门展开论述,内容论及长江中游地区耕地大规模开发,农业集约化经营,新作物全面推广,多种经营共同发展,农业中心由江南转移至长江中游。三是江南地区以纺织业为主导的手工业迅速发展,推动了全国性商业贸易的繁荣,商人、工匠、流民聚集,大规模市镇蓬勃发展,江南得以维持经济中心的地位。四是庶民的社会经济身份得到了极大提高,在阳明学“四民平等”的观念影响下,庶民阶层对政治和社会有了一定了认识,积极参与改变自身命运、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如民变、抗租等。
吴教授敏锐地意识到,明清帝国地域辽阔,各地环境差异甚大,即便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情况,具体变化并非完全不同步。故在本书的韩文版付梓前后,曾着力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探索前述诸多问题在江西地区的具体实践,并著成《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知识产业社2007年版,中译本亦于201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遥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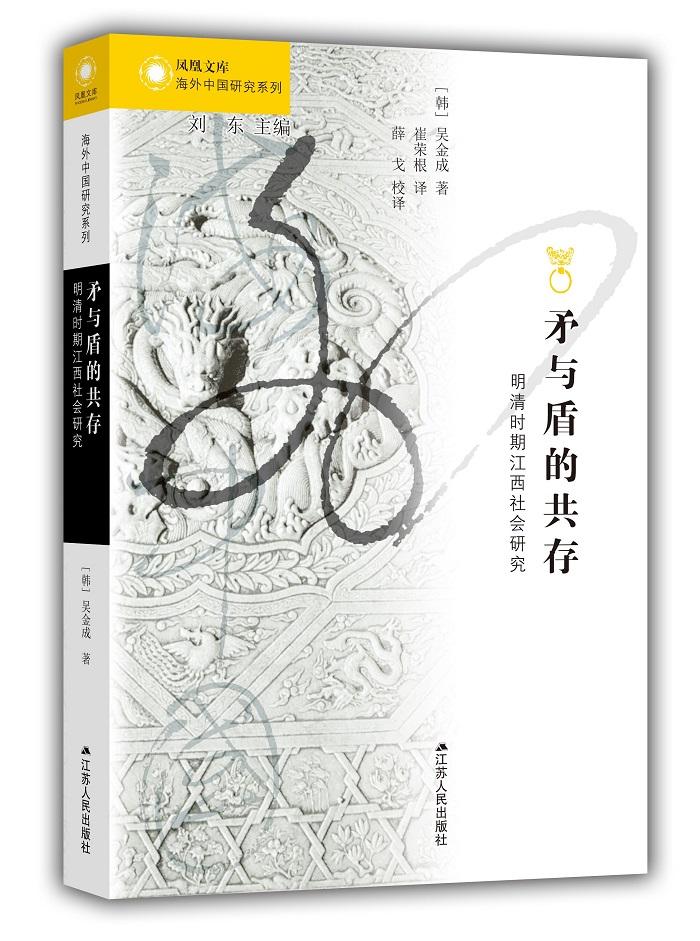
可以说,本书是吴教授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三十余年的精华所在,亦是老一辈韩国明清史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
乡村的绅士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个介于官府与民众之间的阶层,起着连接官府与民众的作用,海外学者称之为“地方精英”。多数时候,这一阶层上与官府争权,下与民众争利。随着明中叶变革的推进,一群被服儒雅的读书人与国家意识形态合拍,在乡村权力出现真空时成为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辅助,到清中后期竟是延续国家政权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绅士阶层。
吴教授所谓的“绅士”,是指以科举制、学校制、捐纳制为媒介出现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支配阶层,包括有过当官经历者(在职、致仕、休职的官僚和进士及第者)和未入仕的学位持有者(亦作士人,即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等官职渴望者)。绅士是地方精英的核心力量,亦是一些精英社会权威的来源。
士绅阶层的形成,既是国家制度使然,也是社会治理需要。明初,朝廷为笼络读书人和改变士风,将学校与科举合并,令生员及监生资格的获得者享有九品官员的特权,即具有优免徭役等诸多权力。一方面,这些特权享有者获得了经济利益,提升了社会地位,国家和民众亦将之视为士大夫的一员,另一方面,他们也体验和感悟着士大夫的自觉性和公意识,孜孜不倦地追逐功名,求不得时则定居乡村,谋取“保家身”的事业。明中叶以来,科举考试竞争愈加激烈,熟读圣贤书的生员、监生、举人与进士、官僚群体一样,因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和共同利益,具备了广泛的同类意识,发展为一个国家与民众共同认可的“独立的社会阶层”,被称作“绅衿”“绅士”或“士绅”。在儒教理念的影响下,绅士们或为探讨学问、或为科举入仕,结成各式的社团乃至联姻,维持彼此间深厚的纽带与协作关系,并制造舆论,传播“绅士公议”,强化阶层意识。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峻、里甲体制逐步瓦解,基层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国家需要实现赋税征收和维护社会秩序,促使具有与国家相同理念的绅士阶层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发挥了支配作用,是为国家行政的辅助组织。
在乡村地区,由于控制能力削弱,国家权力需要依靠绅士的社会支配能力来维持秩序,绅士则需要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巩固其支配力,从而形成了二者相互依存的结构。从公的角度而言,明中叶后绅士在乡村地区扮演了多种重要角色:绅士是国家统治乡村的辅佐,是乡村舆论对国家权力的代言人,担当了国家权力和乡村利益间以及地区间矛盾的调停者。他们作用体现在:一是维持社会秩序,确保乡约、保甲的运行,领导乡村防御,调解乡村大小纠纷,建设各类慈善组织,救济灾难、疾病中的难民;二是倡修水利设施,捐助道路津梁,为农业灌溉、商贸经济提供便利,尤其是地方公益建设方面,自提出建议、唤起舆论、向官府转达意愿,至凑集劳动力和资金、监督工程、调解官府各层级间不同意见,几乎都有绅士们的身影;三是教化乡里,通过乡约、书院、刊行善书及日用杂书,主导乡村舆论。
从私的层面来说,绅士们四处张罗、“武断乡曲”,亦是出自“保身家”的私心。绅士们凭借“绅士公议”,操弄舆论,沽名钓誉,挟持官府,勾结胥吏,垄断桥路,欺行霸市,干涉牙行,参与走私(私盐、外贸),控制市场,经营高利贷,更为可恶地是利用不断扩大的优免特权,不断兼并土地,而小民亦乐于将田地诡寄于绅士,沉重徭役则转移到了仍留在里甲中的平民,无力承担的平民只能逃亡他乡,或流窜山区,或聚集市镇,若丧家之犬,为国家政权的蠹坏埋下了难以根治的病患。
在历史实践中,绅士阶层的社会作用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明中后期,绅士们抓住时机填补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成为国家政权的辅助。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居庙堂之高”,结党营私,争夺政治权力,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处江湖之远”,侵吞赋税,掠夺经济利益,罔顾天下百姓福祉。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国之不国,与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脱不了干系。明清鼎革,满洲人的八旗军虽所向披靡,但稳定社会秩序离不开绅士阶层。在官府与绅士的配合下,各地汹涌的民变、抗租、反清势力相继平定,清朝的统治秩序日渐巩固。然而,满洲统治者不是安于紫禁城的昏君,任由绅士们为所欲为,而是用高压与怀柔并行的策略控制绅士,一边千方百计地打压以江南马首是瞻的士绅阶层,哭庙、奏销、曾静案,乃至革新赋役制度、皇帝屡下江南,无不是借机惩戒积重难返、自以为是的江南士人;一边对绅士施予小利,减免税金,设科劝学,开明史馆,安抚和激励江南绅士。原来“傲骨铮铮”的士绅转身化作摇尾乞怜的顺民,既继承了明代绅士担当地方公益的责任,亦能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支持朝廷平定叛乱,乃大清朝繁荣稳定的维护者。直到清末满洲政权摇摇欲坠,朝廷期许的各种新政没有财政保障,又废弃了上进的科举制度,绅士们最终走向了清廷的对立面。
城里的无赖
江南是两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虽然农业重心转移至两湖地区,但凭借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交通以及繁荣的文化产业,江南的经济中心地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得到了强化,并成长出大量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市镇,围绕在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周围,亦聚集了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群。
江南的城镇人口,除当地自然增长的外,外地流入的人口数量颇多,包括江南各地乡村迁入的流动人口,江西、安徽、福建、湖广等周边省份迁来的雇佣工人和流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大小商人及其家族。这些流动人口大部分没有编入所在城市的户籍,因而鲜有足够的史料论证其具体数额。如此众多的人口,或读书业举、或经商求富、或佣工作匠,没有固定职业的也大有人在,如牙人、讼师、脚夫、乞丐以及无赖,有些虽看似有服务性质的工作,却也流移不定,容易“失足”进入黑社会,成为不法分子。故以无赖为代表的无稳定职业者一向为有识之士忧心,被认为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在城市社会中,绅士扮演着与乡村类似的角色,商人的社会地位虽不及绅士,然其热衷公益,乐善好施,有“绅商”“儒商”之称。在光鲜亮丽的绅士、商人的背后,无赖同样扮演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角色。他们生活在社会背面,支配着“低下社会”(黑社会),解决绅士和商人不好明面出手的问题。打行是城市中依靠武力结盟的黑社会组织,打行里的无赖则是聚集城市无业人员的典型,他们的活动范围极广,为绅士、势豪之家充当爪牙,干预诉讼,勾结蠹吏,凡是有利可图之处便有他们的身影。歇家,是诸如牙人、白拉、讼师、窝访、帮闲等从事经济、法律事务的中间人统称,这些人倒卖信息、为虎作伥、欺善怕恶,虽然为解决贸易困难、日常纠纷提供了些许帮助,但需索无度,“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俨然是城市秩序扰乱者和社会矛盾的制造者。脚夫和乞丐,原本多是破产或走投无路的农民,在城里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受出身无赖的脚头、丐头威逼利诱,要么与打行联合,要么投靠势豪之家,才能获得一点艰难的生存空间。清代中叶,官府对城市加强了管理,无业游民的活动范围缩小,无赖中的一些人或改做工匠,或投身行伍,或没入官府;歇家中,有的化身为胥吏,有的捐纳得官衔,有的进学校成学霸。然而,不论他们进入哪个行业,无不是伺机滋扰生事以求渔利,渐渐地腐蚀着帝国的各行各业,是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逆功能”。
明面上,不务正业的无赖和不怀好意的歇家,是绅士们伸张正义、维护公议的对象,处于“人人喊打”的状态;实际上,绅士实是这些无赖、歇家的倚赖,因为无赖、歇家也明白,没有绅士作为后盾,他们的勾当万万得不到保障,只有与绅士分利,才有机会避开官府的弹压。不止如此,无赖时常与官府也有一定的往来,确切地说,是与胥吏串通,恶意勒索良善无势之民。更荒诞的是,在万历年间,当绅士与皇帝不合作时,明神宗竟派遣宦官担任矿税使,雇佣京城及矿脉所在之处的无赖,为了增加皇帝可用之材而大肆勒索、掠夺,引起包括绅士在内的全民反抗,难怪传统史家会认为明亡始于万历。
在前近代中国社会中,吴教授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四民社会,因为官员与士人同属绅士,乃社会的支配阶层,处于社会的顶端;乡村中小农和城里的市民(工商业从业者)则处于中间,与绅士对应的另一端则是无赖阶层,包括各色的无业游民和滋事渔利的歇家。在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明清帝国中,有许多国家权力难以到达的空白之地,绅士便是国家权力委以支配这些地区的社会阶层。但是,绅士的支配只在白天或者明面上行得通,而在夜间或暗地里则由无赖支配。实际上,自私的绅士与无耻的无赖又相互利用,勾结一体。如果说,未入仕的学位持有者与有过官职者具有共同的儒家理念,让他们具有了一套共享的“同类意识”,那么,目不识丁的打行、脚夫、乞丐等群体与舞文弄墨的讼师、牙行、窝访、胥吏等群体之间也存在的“同类意识”,它只有可能是共同的社会境遇和经济利益,即以不甚合法的手段获取生存资源,且这些手段不仅是国家权力试图管束的对象,也是绅士们乃至普通老百姓蔑视的对象。
再议国家与社会
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命题,而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因素当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运作的关系。数十年来,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纷争不断:自上而下地看,明清时期国家权力无处不在,基层社会在国家权力的严密控制之下;自下而上地看,基层社会有一套自己的运行机制,并未遵循国家意志,而是处于自治的状态;兼顾国家和社会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存在国家政权和乡族势力两套系统,二者“双轨并行”,共同维系社会的稳定;还有学者探寻一条相互调试的路径,认为“国家内在于社会”,即国家与社会相互糅合、相互妥协,经过国家的代理人(绅士)和具有包容性社会机制的媒介作用达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
本书的主题“国法与社会惯行”亦是一种明清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隐喻。吴教授从他发现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出发,即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政策与表达社会要求的惯行之间存在明显的背向而行,认为促发这一背向关系并不断扩大的始作俑者是历史上一向义正辞严示人的绅士阶层,并指出明中叶以来各种社会变革无不与绅士阶层密切相关。社会变革中的“顺功能”,是绅士们治国平天下的公意识使然,也是国家权力收缩的现实需要;社会变革中的“逆功能”,则是绅士们“保身家”的私心使然,也是商品经济活跃的必然要求。然而,历史实践中的绅士阶层并不像他们自绘地那般道貌岸然,更多的时候是先私心而后公意识,但欲壑岂有填满之日,绅士们又将牟利之手伸向了国法难以管控的城市黑社会,通过操控什五成群无赖谋取见不得人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的公意识不过是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利之后的权衡,国家权力与士绅阶层支配的社会之间关系,也是根据国家政权与士绅阶层的利益向背来决定。当国家政权与绅士阶层的利益一致时,或国家权力给予了绅士想要的私利时,国家与社会是合作的,国家可以通过绅士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哪怕是国法无法进入的黑社会;当国家政权与绅士阶层的利益相悖时,或国家权力无法满足绅士的私心时,国家与绅士支配的社会是撕裂的,乃至是对抗的。
因此,前近代中国关系国家社稷与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如何将绅士阶层纳入国家体制——的关键,在于统治集团与绅士阶层能否达成有效的共同利益,国家权力利用绅士阶层的支配力控制基层社会,绅士阶层利用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巩固经济利益和社会支配力。那么,传统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而是随着统治集团与绅士阶层的利益向背而变化。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