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看的勒古恩的第二本小说,第一本是《一无所有》。严格说来,这是第一本,因为《一无所有》我似乎并没有仔细读完,后面为了完成写课程论文的任务,最后的结局似乎被我囫囵吞掉了。但至少前半部分的设定和留下的深刻印象让我难以忘怀。
当我开始读《黑暗的左手》的时候,我预先有一种很强烈的期待。勒古恩的文字,从《一无所有》看来,兼有女性的细腻和幻想主题下的隐微而艰深的深邃思索。她的科幻作品,更像是一种文化科幻。
一个不想早睡的夜晚,我翻开了这部书。它的开头并没有特别吸引我。一种旅客般的视角描述了一场庆典。她想说什么?当一个又一个陌生而又充满奇异的词语占据了语句中本该由熟悉的母语负责的位置,一种奇怪的张力产生了。她没有直接为我们拉开这帘帷幕,而是让我们走近了,如同爱库曼的信使一般,如同金利·艾初次到访一般,疑惑、惊异于每一次冲击。这些陌生的信念、风俗,另一个民族和文化的自然的呼吸,吐息成冰原上的风暴,吹摇着我蒂固根深的习惯印象。虽然这样会抹消掉幻想的美感,但我真切地认同好的科幻作品是一场文化和伦理的社会实验这一观点。它像是一块镜片,当我将它与现实重叠时,才发现我所在的现实不是透明、赤裸裸的真实,而不过是另一块有色玻璃下的放映。
随着这场史诗的记录缓缓地爬行,勒古恩显露出了她的野心。相较之执着费墨于令人咂舌而眼花缭乱的超前绝妙的科幻硬设定,勒古恩更喜欢探讨文明延伸出的多样的可能性。她就像是一个套着科幻外壳的社科学者。甚至就像本书中的故事一样,她像是在借用笔端营造出的一个个虚拟世界作着文明的实验。
现在看来,他们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实验。——第七章 性问题
在这场“实验”中,勒古恩显刻意然将一些主题置于观测的焦点。例如性,政体,仪节,文化气质,宗教,生态环境。它们交织,相互牵绕着、或阻或引着这个星球蹒跚的脚步。
要给予一个整全大观是困难的。尤其在一个主线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中,意图传达其微妙的显征,更为不易。这种情节与信息量的不匹配却很好地通过一种复杂的叙事组织得到了消解。
接下来,我想结合几个感兴趣的主题和文章的特殊叙述谈一谈自己的理解与疑问。
社会文化与文化认同
文化的碰撞,是这本小说最大的主题。当我回顾时,我对书中对文化的描写产生了一些问题。
1. 什么时候,读者开始理解冬星的文化?
2. 什么时候,金利·艾开始成为精神冬星人?
这两个问题,可以视为一组对观的问题。当我思考我对冬星的文化的了解的过程时,我发现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差异寻找阶段;在此阶段,我用自身的文化作为不变的坐标系,主要注意的是冬星与我明显相异的文化特征,比如性,比如奇怪的历法和独特的生态环境。这些差异不一定是构成其文化特征最基础的底层因素,但却是最突出的。
第二个阶段:联系阶段;在此阶段,通过对差异性的分析,我渐渐将其与之前未曾注意到的文化特征相互联系,这些未曾被注意到的文化特征可能是第一阶段与我自身的文化特征相似的,但直到此时,其表面的相似才被摒弃,显露出其下异质的、与其真正的文化特征一脉相承的内涵。比如政体。
毫无疑问,我对冬星的理解是二手的,我透过艾的眼睛审视、体验这个星球。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读者不可能真正理解冬星。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理解,我想是需要更多的人类学社会学观察的。
文化的认同需要一个契机,这是一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代入。如果简单梳理金利·艾的旅程,大致可以被这样串联:
初到卡亥德,逐渐理解卡亥德
——被国王驱逐,否定自己对卡亥德的认识
——逃至欧格瑞恩受到礼遇,欣喜于与卡亥德不一样的文化
——认识到欧格瑞恩更深层的虚假,二次被文化排挤
——在与哈斯穿越冰原回到卡亥德的路程中重新认识卡亥德文化,并产生认同
初看之下,我会认为,在最后一段旅程中,金利·艾才真正作为一个冬星人生活,他不再居住在为特使刻意安排的处所,不再被温暖但虚假的炉火包围,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冬星人而活,触碰最真实的一面:寒冷、冰原、饥饿、孤寂、坦率、运气、生存。从某种意义上,金利·艾不仅重走了传说中的勇者之路,更是亲自创造了这个文化的奇迹。他完成了从一个文化的旁观者到创造者的身份转换。
但是,就像台阶的最后一步重要但需要前九十九步的铺垫一样,被卡亥德否定,对卡亥德文化的怀疑,是这段曲折旅程的必经之路。
4. 勒古恩想要传达的立场是什么?一种超越民族叙事、超越国别叙事、甚至超过文化叙事的共同体?
在本文中,有两对明显的立场对立,卡亥德与欧格瑞恩,冬星与爱库曼。但问题在于,冬星由谁代表?有没有一种文化可以被称为冬星自己的文化。从故事的走向来看,长久敌对的卡亥德与欧格瑞恩,在共同面对第三方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聚合在“冬星”这个名字之下。爱库曼在此,似乎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可能,一种可以摒弃对立政治的理由。这样的力量,无疑带给了卡亥德、欧格瑞恩足以扭转传统政治局面的可能。金利·艾本人万险而终成的结盟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我偶尔也会觉得,勒古恩想说的更多。爱库曼真的带来了改变吗?勒古恩用视角的切换讲述同一个事件,我看到,卡亥德的妥协并不来自于对爱库曼的选择,而是来自于恐惧,不得已,来自于对欧格瑞恩的胜利的曙光。而欧格瑞恩出于局势所逼更为明显。
就像金利·艾本人所说,这个星球上,真正理解,信任他,信任爱库曼的,从始至终,只有哈斯一人。
金利·艾没有理解过卡亥德,直到冰原之行,但从此,他也丢失了对母文化的认同,他对飞船上的同伴感到空前的陌生。
如果理解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只有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同时作为两个文明的承载者?如果在不抛弃本位文明的同时真正理解另一种文明?我认为勒古恩是否认这样的可能的。
当飞船和更多的同伴降落在这个星球,金利·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爱库曼代表的协调的文化统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有效地推行,超越民族的、文化的叙事统一体能够在磕磕绊绊中达成,勒古恩仿佛在犹豫。
5. 读者在阅读时代入的潜在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代入金利·艾?
这一问题乍看似乎并不是问题。
只是突然意识到,作为重要背景的爱库曼成了晦暗的设定,我们并没有直面对于冬星人来说的外星文明,但我们也没有完全代入金利·艾的立场。在爱库曼与冬星的接触中,我们是真正的第三立场。我们如此天然地代入金利·艾——这个似曾相识、甚为熟悉的代言人,以至于轻易地陷入了勒古恩安排的陷阱。我们必将被带领着反思这重身份。在最后的最后。我们跟随着金利·艾经过冰原之行,成了精神上的冬星人。却在我们真正开始认同这个星球、这个文化时,也跟随金利·艾失掉了我们虚假不稳定的立场。
一种合理的代入解释,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但是勒古恩也用频繁的视角转换,甚至在故事的最开头就提醒着我们不要轻易认同立场。
人物解读
限于篇幅和精力(我实在不擅长在通读完后做系统的回顾和感想),我只想记录对哈斯的一些疑问,不想做解答。
1. 哈斯的人生经历,是否如同第二章所讲的故事一样,同他的兄长克慕后被逐出,被流放?
2. 哈斯为什么会有与众不同的人类观?是否是因为他没有被任何一个群体真正的容纳,因此只能在最普遍的基础上寻求认同,就是人类。换言之,他被家族流放,被祖国流放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他接纳金利·艾的决定?
3. 哈斯为什么求死?
宗教
我非常喜欢勒古恩在此对宗教的探讨。她的一切描述都如此真实,充满了一种神秘而真实的异教色彩。旁观宗教仪式那一段写得极好。仿照圣经所写的宗教圣典也很值得玩味,其中的时间观、因果观无不精妙而与文化的特征互为印证。勒古恩对修辞、对隐喻的运用极为高妙,而这一切在对宗教的描写中尤为突出。
《一无所有》
在阅读中,我逐渐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期待。勒古恩独有的透着一股孤寂的文化观再现了。不仅如此,两本书的主角都担任着某种文化使者的角色特色,也都附有流亡者的色彩,金利·艾如此,哈斯如此,一无所有的主角也是如此,他们无不是主动或被动地被抛弃,在不同的文化之中穿梭、碰壁。勒古恩无疑喜欢在科幻背景下探讨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陌生的天幕下,文化的每一种侧面和影像,都变得模糊而陌生了。而文化的交触,就像高密度和低密度的水的接触。它们一点点渗流,那些突触像针一样互相刺探,却又由于次壁的悬差错过交锋。语言得不到交互,只能在空中悬浮。但一场颠倒在所难免,一旦达到极限,就开始颠鸾倒凤,掀起一场风浪。
最后
本意是想对书中的主题进行一点略微的探讨,却发现自己实在不适合在通读后进行一种系统的整理以及依据完善的整理进行讨论。勒古恩的文字在我心中掀起风浪,我却不能像她一样用文字记录下这风浪的分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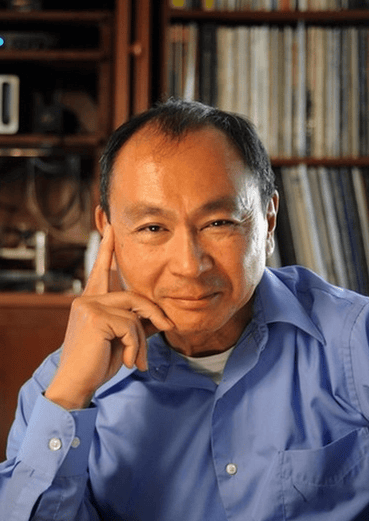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