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其他回答所说,由于其涉及范围之广大及显著的非系统性,想给新文化史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新文化史用来概括近三十年来自西方史学界生发的一股不可阻挡的史学潮流,或者说是一次史学风向的剧烈转折。而这一潮流,席卷了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在内的几乎所有史学门类,对西方历史学的生态产生了全方面的影响。
至于其根本特点,简单来说,如其名字一般,那就是将“文化”引入历史考察之中,既特别强调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又注重运用“文化”的概念去重新诠释历史,最后做到将社会与文化进行整合研究。充分汲取文化人类学等友邻学科的经验,着眼于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这都是新文化史比之于本次转折前的西方现代史学的特点。
什么是“文化”,即使在新文化史历史学家内部,从来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 @灰堡魔法师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可足参看。但与其纠结于文化的定义,不如找寻新文化史学者的共同特点,彼得·伯克的解释相当有说服力:
“文化史家们的共同点也许可以形容为对符号象征及其解释的一种关注。”——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
新文化史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不理解其发生的背景,则无法真正理解新文化史。
二十世纪中叶,历史学发生了一次急速的转向,这次转向奠定了当代历史学发展的基础。支配整个二十世纪之前的传统史学被扫进垃圾桶之中,无论是欧陆的年鉴学派,还是美国的克莱奥学派,新史学都尤其重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并倾向于借鉴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这种主张广泛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变化过程、结构的分析,乃至于用计量方法支配历史研究的主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费尔南·布罗代尔即是典型代表。
然而即使在布罗代尔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与《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巨著照耀一个时代的同时,比之社科浪潮,历史学内也不是万马齐喑。过于强调“总体史”与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崇拜,不仅在动摇着历史学本就岌岌可危的存在界限和理论架构,对“人”的忽视更令历史学界内惴惴不安。对计量与科学的过度推崇、不分场合地强调同质性、人的缺失、历史细节的忽视,这些都是史学社科化无法回避与回答的问题。“生命”缺位的历史学不仅在情感上激起了学界内部的批评,更多学者发现:
“许多社会史家转向文化的因素,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无法解释变化:例如,出生率的改变,虽然能够被计量,但其原因却更加难以捉摸。对诸如性别等文化因素非常突出的 新课题的兴趣,也在文化转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克里斯托弗·E.福思《文化史和新文化史》
出于对这一支配范式的反思,自布罗代尔告别《年鉴杂志》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年鉴学派自身内部开始呼唤“文化”,而这也发出了“新文化史”全面出现的先声。传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渐淡出主流,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为代表,在研究中注重个体的行为、个人心态、习俗、观念、符号等具有浓郁文化研究色彩的方法,成为年鉴学派的主流。只不过,此时引领潮流的法国历史学家并为自觉地提出“新文化史”这一概念,年鉴学派为其创制了一个新的名词——“心态史”。不过,伴随着新文化史的进一步发展,年鉴学派自身在八十年代还对“心态史”这一概念进行了反思。
“‘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雅克·勒高夫《新史学》
并非是只有年鉴学派意识到“文化”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海峡对岸,以E.P. 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发出了同样的呼声,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强调工人阶级的文化认同。正如彼得伯克所言,新文化史的出现来源于对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反思,而这一反思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界的共识:
“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 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 确切地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 一是卡尔· 马克思类型 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 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
与内在反思一再作为新文化史产生动力的,是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后现代浪潮将自身理论建设薄弱的历史学冲击得七零八落、岌岌可危,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历史学家都需要行动起来进行回应。后现代主义对文本和叙述的反思,瓦解了历史学界长期保有的追寻历史真实的信念,瓦解了宏大叙事的天然正当性,瓦解了传统的辉格主义的叙述模式。如果说英法史学界自身的反思还留有深深的“旧的新史学”残余,那后现代主义则促成历史学界进行了向“新文化史”的彻底转身。学者获得了充分的理由,去审视文本生成的过程及其中的文化因素。
新文化史的转变同时被看作是“人类学的转变”,“新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时常是可以同义转换的一组概念。没有人类学的外部给养,新文化史很难发展到今日的局面,甚至难以起步。新文化史使用文化概念去分析人类行为、符号等的核心方法,正是来源于人类学。没有文化分析,则无法实现新文化史意义上的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作为彼时对历史学影响最巨的人类学家,格尔兹不仅对文化作出了令历史学家深感信服的结论,其提出的“深描”方法,对历史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析,对新文化史研究来说更是不可或缺。凭借着文化人类学的帮助,新文化史学者拓展了对研究对象的诠释空间。从根本上来说,区分“新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并无意义,恰如著名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所说:
“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
大体来说,新文化史关注的对象有具备以下特点:
1.潜在的事件
新文化史既不同于传统史学,沦为历史大事的编年史,汲汲于事件的顺序编排及清晰过程;也不同于年鉴学派的“三时段论”,对历史事件嗤之以鼻而不加以理会。明显的历史事件,既包括政治事件、金戈铁马这样的军国大事,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容易被感知的事件。新文化史在向这些明显的历史事件投向关注的同时,注意这些事件背后渗透的文化观念,并且力图将其与明显发生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2.研究对象定义的时间与空间
不同于传统史学,习惯以固定时段、民族、国家、地缘空间等传统时间与空间范围定义研究对象,新文化史择取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故而这一时空界限充满了弹性,大至国家,小至家庭,并没有人为定义的严格界限。这种抛弃传统宏大叙事的国家时空序列,着眼于研究对象自身发展脉络的取向,有助于发现社会中众多独特现象的深层次意义。
3.个体作为叙述的中心
新文化史对五六十年代史学方法的反思,直接来源于旧的“新史学”中“人”的缺位,这一点在新文化史中自然受到格外重视。
在新文化史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再只是帝王将相,以及那些被认为对政治、经济结构产生显著影响的精英人士,同样也不走向另一极端,将历史看作是弱势群体的发声机器。在新文化史的研究过程中,人的平等性非常突出,任何个体都有被作为研究中心的可能。新文化史不再着意于集体、国家等组织等叙事组织,而是直面个体生命的行为与社会的互动,着眼于人之所于社会的复杂关系。
4.观念与社会的互动
承接于对个体行为以及对文化互动过程的关注,新文化史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心态与社会可能的互动过程。个人的思想既有着本身的能动性,又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外部的社会条件。个体的观念世界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的构造,而社会的互动又来自于个体之间的思想交流,新文化史深入考察个体的心态史,从而可以对诸多社会文化现象做出前所未有的深度诠释。
总的来说,新文化史不是对历史的开辟,而是对历史的深耕。新文化史更多的是一种研究取向或方法,而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单独存在史学领域。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或许也可以作为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社会史,但这一研究过程,已经被投射了新的光芒,这才是新文化史得以广泛扩张,成为西方当代历史学的一大主流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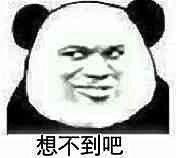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