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以为,写写嵇康的特立独行、多才多艺、反叛精神,再配上几个传奇小故事,也就齐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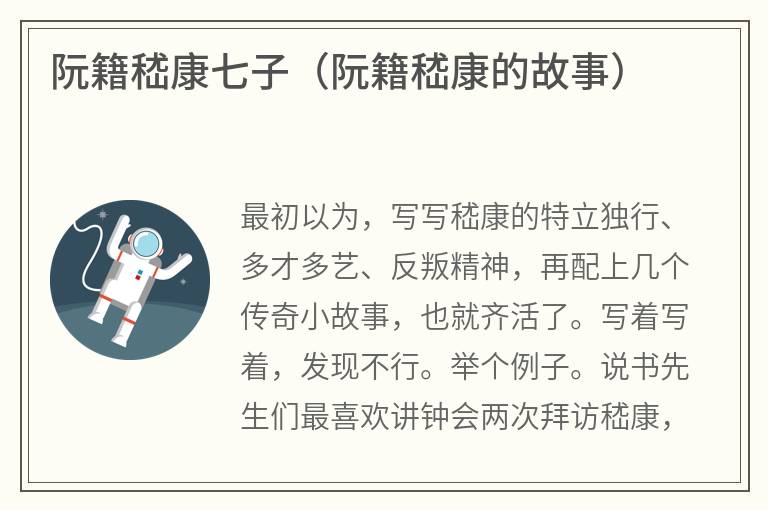
阮籍嵇康七子(阮籍嵇康的故事)
写着写着,发现不行。
举个例子。
说书先生们最喜欢讲钟会两次拜访嵇康,并把嵇康之死归结到钟会身上。
第一次见面(实际上没见到)。钟会写了一篇文章,想请嵇康看看,来到嵇康家门口儿,突然怯场了,就把文章往嵇康家院子里一丢,自己掉头跑了——就像是青涩少年写了封情书,又不好意思亲自送给心仪的姑娘,只好偷偷塞入人家课桌里似的。此处,说书先生们会把钟会定位为深受司马家宠爱的一个贵公子,让人感觉这家伙跟高衙内似的,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混子,附庸风雅写了篇狗屁文章,想请嵇康老师美言几句,以赢得名声。
但实际上,钟会不但辅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平定了毌丘俭、诸葛诞叛乱(淮南三叛的第二叛、第三叛),还与邓艾一道灭掉了蜀国,而且钟氏家族家学深厚,钟会本人更是当时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其才华绝不在嵇康之下。钟会的这篇文章叫《四本论》,探讨的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那么,为什么他根本没见到嵇康就跑了?其真实原因,恐怕说书先生们就说不清了。
第二次见面(这回见到了)。应该是在当了司隶校尉以后,钟会再次去见嵇康,此时钟会志得意满,肥马轻裘,自当是带了一大批帮忙、帮闲一道去的。嵇康正在打铁,钟会就带着一班手下跟旁边看着,嵇康头都不抬,只管打铁。就这么过了好一阵子,钟会觉得无趣,准备离去。嵇康突然朗声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随口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然后,扬长而去。回去之后,钟会就在司马昭面前大肆诋毁嵇康,导致嵇康最终被司马昭杀害。说书先生们认为,这件事儿,嵇康有点儿过分了,你不理钟会也就罢了,人家要走了,你何必搞那么一句,让人难堪呢?此时钟会已经是司马昭身边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得罪了他,你不是找死吗?因此,嵇康之死,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是这样吗?
我个人认为,这种解释,有点扯。前面我们讲过,阮籍老娘去世,阮籍不但不哭,还跟司马昭身边喝大酒吃肥肉。西晋三大孝子之一的何曾,指着阮籍的鼻子,对司马昭说,老大,您是以孝治天下的,阮籍这厮如此不孝,就算不弄死他,也应该流放到边地去啊!司马昭说,老何,你看我的面子,别追究他不行吗?
阮籍和嵇康都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阮籍,何曾弹劾,司马昭就护着;嵇康,钟会说点儿坏话,司马昭就杀了,老实说,理由不够硬,不能服人。
要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恐怕还要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入手。
魏晋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巨大的,我以为主要是两方力量,一是官宣,一是名士。名士有时与官宣是一致的,比如钟会;有时是分离的,比如嵇康,套用个时髦词儿,嵇康就是当时的民间意见领袖。
一般情况下,朝廷会给名士一定的生存空间,即使没有为我所用,但只要不是太出格儿,别总是瞎嘚嘚、讲怪话,朝廷也会允许你自生自灭。但是,如果你借着自己的名声对朝廷政策说三道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曹操诛杀孔融,曹丕因魏讽案诛杀数十人(一说数千人),就是这种情况。
到了司马家当权之后,司马懿诛杀了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王广(前面几位死于高平陵事变,王广死于淮南三叛的第一叛,王凌谋反案,王广是王凌的儿子)等一批名士;司马师诛杀了李丰、夏侯玄(李丰谋反案)等一批名士;而司马昭还没动刀呢。
我给名士提供的生存法则只有两条:
第一条,朝廷是对的;
第二条,如果朝廷错了,请参阅第一条。
想通了这一节,名士想活下去,司马昭也是给机会的。比如,竹林七贤的其他六贤,阮籍、阮咸、刘伶、向秀、山涛、王戎,都做了司马家的官,而且,山涛、王戎,都做到了三公。
只有嵇康,宁愿打铁,也不受招安,而且这家伙名声还特别大,是当时的超级大V,对几千名太学生(国家预备干部)而言,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一个人一张嘴一枝笔,就可以抗衡整个士大夫集团,他时不时发表一些与官宣严重背离的帖子,一发出来就十万加,实在是太讨厌了,这才是司马昭要弄死他的主要原因。钟会,不过是司马昭的小卒子而已,更何况,嵇康死于公元263年的冬天,那个时候,钟会正在蜀国搞谋反活动,怎么陷害嵇康?
我说嵇康难写,这些都不是主因,关键是这家伙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还真不少,不吃透消化他的那些个文章诗词,只流于表面地讲他的传奇生死,讲真,没什么意思。嵇康写了一大堆东西:
《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答难养生论》《明胆论》《太师箴》《释私论》《管蔡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等等等,光看这些个名字,就让人头大。
这些文章,一篇比一篇难懂。比嵇康早几百年的贾谊,写了《治安策》《过秦论》,都是千古名篇,哪有嵇康这么难懂!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清谈盛行。魏明帝曹叡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大才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有钱有闲有理想的青年才俊,最喜欢清谈,而他们清谈的内容,则是以“三玄”为底子,所谓三玄,就是《易经》《老子》《庄子》,都是出了名的难懂。
二是清谈与政治相结合。曹叡时期,对这些名嘴们进行了打压,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浮华案”,这些人受到了抑黜。曹叡死后,曹爽辅政,大量起用这些名嘴,何晏、夏侯玄等人都进入中枢,把他们的一身才华与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有意无意地,也把深奥的清谈带入了政治生活。
三是往往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曹爽、夏侯玄、何晏等人的政治实践,引起了以司马懿为首的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弹,一场高平陵事变,杀了一大批名嘴,又吓得一些名嘴郁郁而终(比如王弼),到了竹林七贤的时代,在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之下,自由说话更成为奢侈品,而嵇康这样的人,不说点什么肯定会憋死,但说的时候多少得有点伪装、讲点暗语,他的东西就越发难懂了。
但是,再难懂,也有人能读得懂。
举个例子。
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为仕途不顺,有点闹情绪,写了一首诗: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大概意思是,南山有田啊,一片荒芜,没有人照料;种豆一百亩啊,豆子全掉啦,就剩下豆茎;人生须行乐啊,何必非等到富贵!
当时有个人对此诗进行了解读:
南山是很高的地方,象征皇帝,而一片荒芜没有人照料,显然在攻击皇帝昏乱。一顷是一百亩,比喻文武百官,豆子本是很结实的东西,代表忠贞,应该放在仓库之中,却沦落到旷野,比喻杨恽被罢黜放逐。豆茎下垂,曲而不直,暗示政府官员,都是谄媚之徒。
汉宣帝刘病已看到杨恽的这首诗,极其反感,廷尉于是判处杨恽大逆无道,腰斩,妻子儿女放逐酒泉郡。
讲真,如果深入去挖嵇康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恐怕比杨恽的诗,还要让朝廷震怒,杨恽只是表达对个人际遇的不满,而嵇康则是对朝廷大政方针发起挑战,他还怎么活?
那么,他不说话不就安全了?
对,他不说话,肯定安全。但,他忍不住。
我们来看一下嵇康的基本情况。
嵇康,字叔夜,谯郡铚县(安徽省宿州市西南)人,出生于公元224年。
《晋书?嵇康传》载,嵇康的先祖本姓奚,是会稽上虞(浙江省上虞市)人。某代奚家人家为了躲避仇家,举家跑到铚县定居,因旁边有一座嵇山,于是改姓为嵇。另有一说,嵇家先人取会稽郡的“稽”,换旨为山,于是姓嵇。
嵇康的父亲嵇昭,在曹魏政权做到了治书侍御史,并承担过督办军粮的任务,官做得虽然不大,但应该说已经进入了曹操的视线,甚或有可能成为曹操(曹氏)的亲信。
嵇康出生不久,嵇昭就去世了,嵇康由母亲和兄长抚育成人。
嵇康的字是“叔夜”,这个“叔”字,透露出他排行老三。大哥姓名不可考,但应该至少大嵇康十余岁,已经承担了养家的重担。二哥嵇喜,字公穆,官做得平稳顺遂。
嵇喜以秀才身份从军,担任过司马、江夏太守、徐州刺史、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官职。
嵇康和嵇喜,早年间关系应该相当亲密,但后来可能闹掰了,不过,不是感情上的“掰”,而是性格上的“掰”,或者说是政治理念上的“掰”。
我们之前讲过,阮籍会玩儿“青白眼”,老娘去世,嵇喜来了,阮籍就翻白眼儿,籍康来了,阮籍就青眼有加。
嵇康还有一个好哥们儿叫吕安,《世说新语?简傲》载,吕安到嵇康家,正好嵇康不在,嵇喜出来迎接。吕安一言不发,就在嵇家大门上写了一个“凤”字,然后就走了。嵇喜一脸懵圈,搞不清这小子什么意思。
凤的繁体字是“鳳”,注意,鸟上面还有一小横,鳳字拆开,就是“凡鸟”,吕安的意思是,嵇喜,你就是一凡鸟,我懒得搭理你。呵呵。
阮籍母亲丧礼,嵇喜前往吊丧,吕安来家找嵇康,嵇喜热情接待,但是阮籍和吕安的态度并不友好,这就给我造成两个印象:第一,嵇喜是热衷于官场的俗人,而嵇康则是清高的君子;第二,兄弟两个关系很糟。
关于第一点,我想请问,嵇康不做司马家的官,是不是嵇喜也不应该做?如果做了,嵇喜就不是东西?如果不做,嵇喜何以养家?天下人都做得司马家的官,偏嵇喜做不得?……讲真,做嵇康这样的名士,成本太高,一般人是做不起的。
关键是第二点,我个人认为,嵇喜、嵇康兄弟的感情非常好,并非我们以为的那么不堪。
我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一个重要理由是,哥儿俩之间多有诗词互赠,尤其是嵇康,当嵇喜以秀才身份从军之后,嵇康写了十九首《兄秀才入军赠诗》,其对嵇喜的深厚感情,浓郁得化都化不开。我们看一下第十四首: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读如波)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注意最后一句,“郢人逝矣,谁与尽言”。也就是说,嵇康是把嵇喜视为“郢人”的。
典故郢人挥斤,出自《庄子?徐无鬼》。说是有个郢人,也就楚国人,在鼻尖上涂一层白灰,薄得跟苍蝇翅膀似的,然后,让石匠用斧子把那层白灰给“砍”去——不是刮去,是砍去。石匠的利斧舞动如风,就跟李小龙耍双截棍似的,一顿狂抡,白灰全部被斧子砍掉,干干净净儿的,但郢人的鼻子一点儿都没被刮破。后来,宋元君听说之后,就把石匠找来,让他表演。石匠拒绝,说,世人都以为我耍斧子很厉害,但不知道我那个拍档,鼻子上抹灰的郢人更厉害,我之所以能够把白灰砍下来而不伤他的鼻子,正是因为他有胆略,我才可以这么干,换个人,只要稍有畏惧之心,这个事儿都没法干。现在,我的拍档去世很久了,我不可能再表演了。
真还别说,我也见过类似“郢人挥斤”的事儿。有一年,我去海南旅游,观看泰国人妖表演。暖场节目相当惊艳,其中一个节目就颇有郢人挥斤的意思。两人表演,一个人站在舞台左侧,另一个站在舞台右侧,两人相距七八米左右,右侧的人手里拎着一条鞭子。
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有这么几句歌词: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执鞭者手里的鞭子,可不是这位牧羊姑娘打情骂俏的小皮鞭诶,而是类似于老北京一些练家子健身用的长皮鞭,很长,很粗,鞭梢略细,非常沉重,挥动时发出“呜呜”呼啸,目测得十来斤重,没把子力气根本抡不动。执鞭人不动,皮鞭就软塌塌躺在地上,执鞭人手臂爆起,那长鞭也豹起,“啪”地一声抽出去,真有无坚不催之感,倘若抽在人身上,用不了三两鞭,就得要了亲命。
舞台上,左边的人点着一根儿烟,叼在嘴上,执鞭者略作准备,手臂挥动,那长鞭如闪电击向叼烟人。叼烟人纹丝不动,眼尖的观众立即看出,他嘴上就剩了一个过滤嘴儿,香烟的其他部分,已经被长鞭击断。叼烟那个,就像是郢人,挥鞭那个,就像是石匠,我猜,叼烟的和挥鞭的,谁离开另一个,这节目都没法儿演了。
【这种鞭子】
郢人和石匠,有点像俞伯牙和钟子期,可谓知音难觅。
嵇康在诗中把嵇喜比喻为郢人,可见兄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甚至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是对得上话的。我的意思是,嵇康被后世尊为最牛的文化人之一,他的哥哥嵇喜,与他对得上话,水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只不过,嵇喜后来走了仕途,没有留下更多的文章罢了。
嵇喜出仕,嵇康大约是有些感慨,两人的关系破裂了,但是感情并没有破裂。
讲真,嵇喜大约是一个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兄弟俩心生龃龉,主要是嵇喜做了司马家的官,特别是,他竟然做到了宗正!
宗正是九卿之一,这个职务是干什么的?是掌管王室亲族事务的。两汉四百年,没有出现过担任宗正而不姓刘的,也就是说,掌管王室亲族事务,得由王室成员来承担。但是,嵇喜竟然成了曹魏政权的宗正,真是岂有此理!
查阅《三国志》,魏国有两个不姓曹的宗正,第一位是甄德,第二位就是嵇喜。甄德虽然不姓曹,但他本是魏文帝曹丕的郭皇后家的人,又被魏明帝曹叡过继给亲娘甄夫人家为后,袭了曹叡女儿平原公主的爵位。也就是说,这位甄德,与郭皇后、甄皇后,以及曹叡本人,都有那么点儿关系,当宗正,虽然也不合官制,好歹沾点儿亲带点儿故。但嵇喜则不同,他与曹魏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居然做了宗正,司马家也太欺负曹家了吧!
嵇康对此,大约也是心有怨气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下回再讲。
【图片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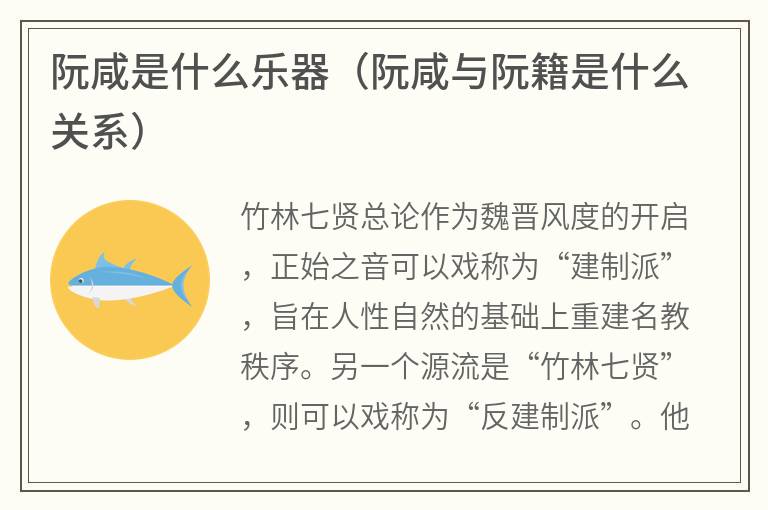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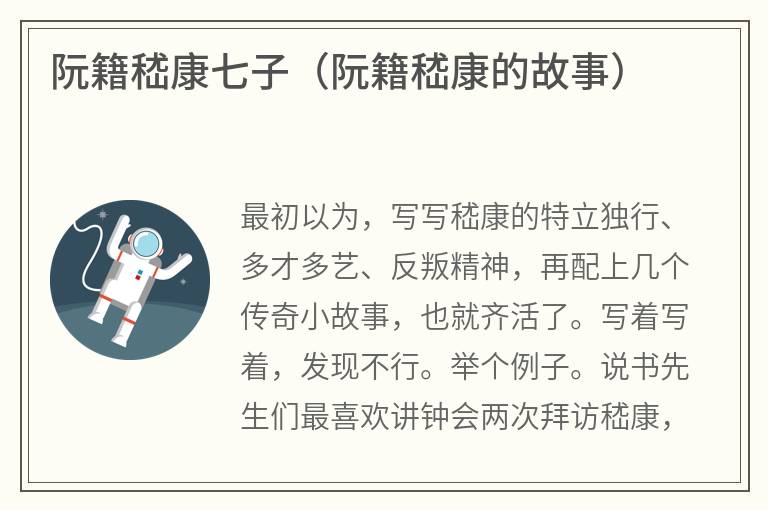
发表评论